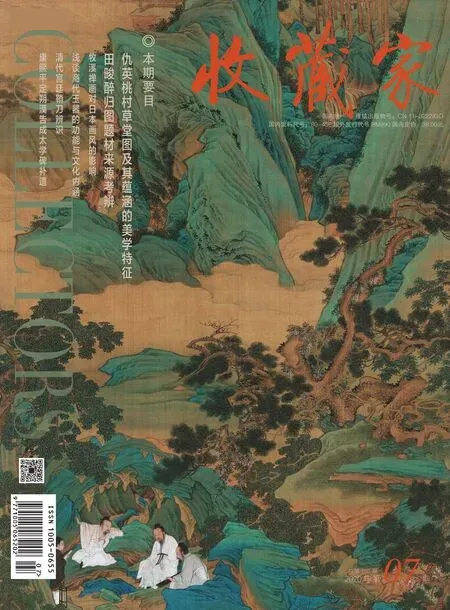滿城漢墓出土車馬器探析
□ 賈葉青
1968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保定市滿城縣的陵山上發掘了兩座漢代墓葬,經過對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銘文、造型、工藝的反復研究,最終確定墓主人是中山靖王劉勝及王后竇綰。其中一號墓為劉勝墓,二號墓為竇綰墓,兩墓均鑿山而成,規模宏大,共出土文物一萬多件,再現了西漢貴族“事死如事生”的喪葬習俗,被評選為“中國20 世紀100 項考古大發現”之一。在兩座墓葬的耳室和甬道中共發現了10 輛馬車,29 匹馬,還出土了精美的青銅車馬器2884 件,其數量之繁多、裝飾之華麗、工藝之精湛是極為少見的,這些器物反映出西漢手工業制作的高超水平,為研究漢代車馬制度和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一、滿城漢墓出土真車馬概況
西漢時期,“貴者乘車,賤者徒行”,車馬不僅是交通工具,也是王侯貴族身份的象征。《史記·平準書》中記載西漢初期,“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漢武帝時期,社會經濟迅速的恢復和發展起來,“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竟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這時馬車的普及率已經相當高了,且崇尚車輿裝飾華麗之風。滿城漢墓設置有車馬房,車馬房中隨葬車馬的情況,呈現出當時王公貴族乘堅策肥的奢侈生活。

圖1 劉勝墓墓室結構(選自《滿城漢墓發掘報告》)

圖2 竇綰墓墓室結構(選自《滿城漢墓發掘報告》)

圖3 錯金銀銅車軎

圖4 鎏金鑲嵌龍首形銅轅飾
劉勝墓共出土6 輛車,16 具馬骨架,并殉有狗和鹿。其中1 號車和2 號車放置于甬道,3 ~6 號車放置在南耳室,由于年代久遠,馬車木質結構已經腐朽,又因滲水淤積,一些金屬構件已被沖亂。根據遺跡推測,1 號車為1 馬駕馭的雙轅車,留有長、寬1 米左右的朱紅色漆皮,應為車廂上的殘跡,車具錯金銀,配有1 件銅弩機。《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記載:“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司馬貞索隱:“謂輕車,一馬車也”,所以這輛車應為比較輕便的軺車,可能是劉勝出行的導車或從車。2 號車制作最為講究,是單轅、4 匹馬駕馭的安車,并伴有11 具狗骨架和1具鹿骨架,車上放4 件鎏金承弓器和1 件弩機,車馬飾均錯金銀或鎏金,車轅飾為龍首形,蓋弓帽以花朵為裝飾,即“金華蚤”。《后漢書·輿服志》記載:“乘輿、金根、安車……龍首銜軛”“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虡文,畫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日王青蓋車”,所以這輛車應為劉勝使用的等級很高的王青蓋車。3 號車是單轅、4 匹馬駕馭的安車,車馬飾均鎏金裝飾。4 號車和5 號車均為2 馬駕馭的單轅車,周圍出土有承弓器、弩機、銅鏃,推測可能與出游或征戰有關。6 號車是雙轅車,車旁有3 具馬骨架,是僅次于2 號車的豪華馬車(圖1)。
竇綰墓北耳室共出土4 輛車,13 具馬骨架。同劉勝墓一樣,這些實用馬車的木質結構已經腐朽,因洞室常年被雨水侵灌,導致某些金屬車馬器位置移動。根據遺跡推測,1 號車是單轅、4 匹馬駕馭的安車,留有朱紅色帶花紋漆皮,應為車廂上的殘跡,出土車馬器以鎏金裝飾。2 號車也是單轅車,周圍有4 具馬骨架,其中一具屬小馬骨架,推測可能為4 號車的馭馬。兩輛車周圍均伴有一些散落的狗骨。3 號車是4馬駕馭的單轅車,另有1 副小馬牙床。車廂周圍散落28 個蓋弓帽,其分布呈圓形,《后漢書·輿服志》記載:“輿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體現了古人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意識形態。此外,3 號車車廂周圍有2 具弩機、一簇銅鏃,且銅鏃前鋒鈍圓,應是專為打獵而制作的,因此,有專家推測這輛車可能是狩獵用的獵車。4 號車是單轅小車,周圍散落的車馬器器形較小,且周圍沒有馬骨架,專家推測2 號車和3 號車周圍的兩匹小馬應該是4 號車的馭馬。《漢書·霍光傳》記載:“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游戲掖庭中”,三國魏人張晏注:“皇太后所駕游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可見竇綰墓的這輛小車可能就是漢代皇室貴族婦女駕游宮中的小馬車,也稱輦車,駕車的小馬稱為果下馬(圖2)。

圖5 鎏金鑲嵌銅承弓器

圖6 錯金銀銅較

圖7 錯金銀銅較(局部展開圖)

圖8 銀當盧

圖9 鎏金銀銅當盧
二、滿城漢墓出土車馬器概述
滿城漢墓出土了2884 件裝飾精美的金屬車器和馬飾,這些器件功能合理,材質多樣、裝飾豐富,蘊含著漢代的文化審美和精神內涵,體現了古人的設計智慧。
1.車器
車軎,《說文解字》:“軎,車軸端也”,其形狀一般呈長筒型,是套在車軸兩端用以括約和保護軸頭的器物,分為內外兩端,內端較粗接近輪轂,外端較細接近車軸外側。錯金銀銅車軎,長5.9 厘米,一端封口,一端折沿,軎身中段裝飾有一周寬帶凸弦紋,器表用錯金銀工藝裝飾出云雷紋,花紋對稱,精美細膩。上面插有銅轄,《說文解字》解釋:“轄……一曰轄,鍵也”,轄的一端的穿孔用來插銷釘起到制軎的功能,另一端穿孔用來系裝飾性的飛軨(圖3)。
車轅飾,安裝在車轅端頭的飾件,既是出于美觀的需要,又起到保護車轅的作用。鎏金鑲嵌龍首形銅轅飾,長20 厘米,作龍首形,長扁鼻前伸,雙目前視,雙齒緊閉,龍口銜管徑3.2 厘米的銎管,龍之雙角卷曲成環狀。器物通體鎏金,并鑲嵌綠松石和瑪瑙作為裝飾,形成了絢麗奢華的藝術效果。《尚書》中記載“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說文解字》中解釋龍為:“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 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在古人看來,龍是天上的馬,也是人登天升仙的神獸。把車轅做成龍頭的形狀,體現了人們對龍的崇拜,也有“神龍引車”的含義(圖4)。
承弓器,古代戰車上的裝配附件,主要為固定兵器弩機所用。成對組合的承弓器正好承托弓弩前端的雙淵部位,弩臂搭在車箱前欄,構成穩定的三角形結構用于穩定弓弩。鎏金鑲嵌銅承弓器,通長13.8 厘米,造型簡潔生動,作龍頭的形狀,龍的雙眼圓睜注視前方,龍角緊貼頭部向后伸展,龍口大張,口內吐出長頸高昂的獸首,獸首作昂起狀,頸部細長而彎曲。器物通體鎏金,龍頭和獸首用瑪瑙和綠松石鑲嵌點綴。整件器物以巧妙的構思和精湛的裝飾,體現出古代工匠豐富的想象力和審美意蘊(圖5)。
較,曲鉤形構件,安裝在車輿兩側屏板上、供乘車者憑倚的扶手。張衡在《西京賦》中寫到“戴翠帽,倚金較”,薛綜注:“翠羽為車蓋,黃金以飾較也”。車較,不僅是車輿上華美的裝飾品,也是車主人高貴身份的重要標志。錯金銀銅較,長21.7、寬0.8 厘米。通身以金絲銀絲相間錯出云雷紋,作對稱排列,顯得既協調又極富畫面感,且紋飾具有二方連續性,在視覺上又產生了緊湊感和韻律感。錯金銀是一項復合工藝,加工難度非常大。這件器物直徑只有0.8 毫米,古代工匠在這弧形面的方寸之間,以銅胎為紙,以金銀絲為墨,制作出了一幅靈動飄逸的美妙圖畫,甚為精彩(圖6、圖7)。
2.馬器
當盧,“盧”通顱,因系戴于馬額中央,所以稱為當盧。其不能遮擋馬的眼鼻,故大體只能在額頭與雙眼之間的T 字形空間懸掛,既有一定的美觀裝飾作用,也可以保護馬頭的要害部位。銀當盧,長26.8 厘米,整體作馬面形,頭面平直而偏長,耳短且上翹內卷,雙眼和嘴部作凸起的圓形,圓形中心有鏤空的長方形小孔,周緣裝飾連珠紋,設計有51 個小孔用以穿帶縛扎、系于馬頭。整體比例協調,具有純厚樸素自然的裝飾風格。鎏金銀銅當盧,長25.3 厘米,背面設計有三鈕,上為兩個平行豎鈕,下為一橫鈕。正面以鎏銀襯地,上刻鎏金紋飾加以渲染,作內外雙重輪廓線。內輪廓線的內圍以上下纏繞的流云紋為主體紋飾,其間有怪獸出沒,還逼真地勾描出一幅獵人打獵圖。獵人頭戴尖帽,高鼻、大眼、身穿對襟短衣,挽褲及膝,衣帽裝束與胡服類似。他正向右側回首持弓射箭,姿態矯捷。內外輪廓線間裝飾有身體蜷曲的蟠龍、昂首翹尾的朱雀、奔跑的野豬和神獸等動物造型,整體畫面布局勻稱,線條流暢、充滿生趣(圖8、圖9)。
銜鑣:銜,又稱“勒”,是橫勒在馬口中的器具。鑣,是與銜配合使用的馬具,安裝在馬口角的兩頰上。駕馬時,銜置于馬口中,用以制馭馬的行止。鑣貫于馬銜的兩環中,用以防止銜脫落。錯金銀銅銜鑣,鑣長25.3、銜長21.7 厘米。銅鑣略呈S 型,兩端似槳葉,裝飾波浪式花邊,中段有二橫穿孔,器身采用錯金銀工藝裝飾有流云紋,線條輕盈流暢,完美地展現出鑣的裝飾功能。銜作扭索狀,與鑣配套使用,分為兩節,每節中間以簡樸的繩索紋裝飾,兩端各有一圓環,兩節以內環相互套接,外環用以系轡貫鑣(圖10)。

圖10 錯金銀銅銜鑣

圖11 鎏金銅節約

圖12 鎏金花型銅蓋弓帽

圖13 鎏金銅傘柄箍
節約:用來裝飾和連結馬絡頭、轡帶的零件。滿城漢墓出土銅節約93 件,均采用鎏金工藝裝飾,彰顯了車主高貴的身份。直徑1.3 ~3.5 厘米,作球面形,球面鑄出熊的形象,熊雙目圓睜、四爪清晰,十分嬌憨可愛。背面設計科學,有兩平行鈕、四方形環鈕和井架型鈕三種通孔形式,可以保證皮條在交叉處穩定結節(圖11)。
三、滿城漢墓土車馬器的藝術特征
滿城漢墓的車馬器鑄造技藝精湛、紋飾精巧、造型栩栩如生,蘊含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及美學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漢青銅器的藝術特點。
1.精致實用的造型設計
《周易·系辭上》中提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東漢思想家王符在《潛夫論》中提出:“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說明實用性是古代造物設計的主要特點,即制器以精確實用為上。滿城漢墓的車馬器就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幾乎所有的車馬器都體現了“物以致用”的價值取向。鎏金銅蓋弓帽,管部凸出一棘爪,用于勾撐傘布,后端還有小銷孔,用于穿繩牽連蓋弓。由于車蓋并不是固定在車上不移動的,所以古人設計傘柄箍,方便車蓋裝卸,體現出“形式追隨功能”的設計思想(圖12、圖13)。
2.舒展動感的裝飾紋樣
西漢時期,手工業進一步發展,青銅器在制作工藝和裝飾紋樣方面取得了快速的發展。漢承楚風,繼承了楚文化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青銅器上的紋飾趨于舒展動感和簡潔輕快,彰顯了獨特的美感。比如圖8 的當盧,以形態生動的獵人、蟠龍、朱雀、野豬和云紋組成了一幅生動的圖案。蟠龍、野豬和朱雀穿梭于云紋之間,或駐足而立,或奔騰向前,野豬身上的鬢毛隨風飄起,朱雀昂首翹尾營造出輕盈欲飛的姿態,整體裝飾圖案極具動感韻律,展現出生命的活力,傳遞出奔放自由的浪漫氣質。
3.嫻熟精湛的裝飾技法
在漢代“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的觀念影響下,黃金和白銀在皇室貴族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范圍較為廣泛。滿城漢墓的車馬器,或鎏金銀、或錯金銀,或鑲嵌金銀寶珠,裝飾十分華麗。尤其是鎏金工藝,在漢代得到充分的發展,據《漢書·外戚傳》記載:“……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 昌) 黃金涂,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如上述的龍首形車轅飾、銅承弓器、蓋弓帽等均為鎏金工藝裝飾,使得器表華美,炫麗奪目,顯示出墓主身份的高貴、生活的奢華。而圖3 車軎、圖6 銅較和圖9 銜鑣則是采用錯金銀工藝裝飾,紋飾基本遍布器物全身,繁簡結合的恰到好處,顯示出西漢工匠精湛嫻熟的裝飾技法。
滿城漢墓出土的不同類型的馬車,驗證了史書中關于劉勝“喜游玩,好享樂”的記載,而那些精美的車馬器又為研究西漢高等級貴族的車輿制度提供了實物資料。這些車馬器以實用的造型、豐富的紋飾、精細的做工,體現出漢代人豐富的審美意識和漢代工匠高超的技藝水平,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是我國古代高超科技水平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