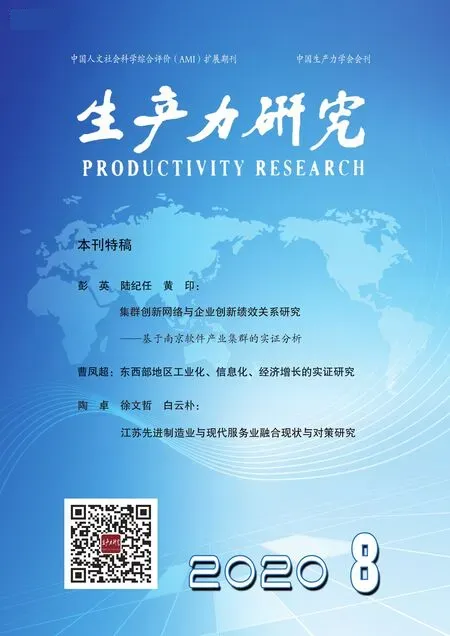集群創新網絡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研究
——基于南京軟件產業集群的實證分析
彭 英,陸紀任,黃 印
(1.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03;2.南京郵電大學國際電聯電信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江蘇南京 210003;3.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蘇州市分公司,江蘇南京 215004)
一、引言
軟件產業集群是推動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先導性力量,在奠基智能產業和信息技術的同時,也促進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軟件產業化水平提高。然而,當前軟件產業集群內各主體間關系存在薄弱且不穩定的問題。同時,集群內企業的創新績效被嚴重忽視,制約了軟件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是軟件產業集群內部尚未構建有效的創新網絡,行為主體創新績效低下。本文基于現有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以南京軟件產業集群為例,實地走訪中國(南京)軟件谷、江蘇軟件園、徐莊軟件園等園區,對園區內企業進行問卷調查,并實證檢驗問卷數據,助力完善集群企業創新網絡,從而推動整個軟件產業集群升級發展。
二、理論與假設
(一)創新網絡關系特征與企業創新績效
創新網絡關系特征包括網絡關系強度和網絡關系穩定性,是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重要因素[1]。“創新”最早由Schumpeter(1912)提出,他認為判定創新與否的標準為是否產生了新的價值,并且創新主體必須為企業。通常以創新投入、專利權數、著作數、勞動產出等作為衡量指標。網絡關系強度代表著創新企業與集群內其他主體間聯系的頻繁程度,關系強弱不同的企業可獲得不同程度的信息與資源[2]。任勝鋼等(201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所處網絡規模、關系強度、開放性與企業創新存在顯著正相關;于森(2014)[3]發現關系強度對企業創新能力和績效有正向影響。李志剛等(2007)實證分析驗證了網絡穩定性、網絡密度、網絡中心度等變量顯著的正向作用于企業創新績效;張悅等(2016)[4]通過Meta 方法對68 個獨立樣本進行實證研究,表明網絡穩定性顯著正向作用于企業創新績效。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a:網絡關系強度與集群內企業的創新績效正相關;
假設H1b:網絡穩定性與集群內企業的創新績效正相關。
(二)創新網絡結構特征與企業創新績效
創新網絡結構實質是網絡內主體間的聯系方式,創新主體通過網絡結構影響網絡內其他主體的創新行為,從而影響整個集群的效率[5]。網絡密度和結構洞是學界常用的網絡結構指標。研究對象與網絡內其他企業直接聯系,而其他企業間無直接聯系,則該企業就處于結構洞位置[6-7]。通過對流動信息的有效控制,結構洞企業可以實現對雙方企業的控制,最大化提升自身創新績效[8]。再者,結構洞企業能有效減少企業與其他企業間的冗余聯系,進而有更多資源用于提高創新績效[9-10]。網絡密度是描述網絡內部主體間聯系的密集程度。高密度網絡高效促進企業間合作、信任,可以更好實現網絡內企業知識、信息的交流[11]。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a:網絡結構洞與集群內企業的創新績效正相關;
假設H2b:網絡密度與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正相關。
(三)創新環境與企業創新績效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2008)將政府政策、社會文化、設施等作為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因素。李衛國(2009)將創新環境劃分為社會資本、文化、政策等。蓋文啟(2010)指出區域環境的硬環境包括設施環境、區域位置等,軟環境包括政策、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Davis(2015)等學者進一步認為集群氛圍環境與集群的創新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3a:要素環境與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正相關;
假設H3b:社會文化環境與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正相關;
假設H3c:集群政策環境與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正相關;
假設H3d:集群氛圍環境與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正相關。
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收集
本研究通過兩階段來優化問卷設計。第一階段:歸納總結前人的理論假設、研究成果,確認需要測量的變量;選取學界給出的測量指標來量化變量;編制測量題項形成預調查問卷。第二階段:實地走訪南京軟件產業園區企業,征詢相關工作人員的建議,對預調查問卷進行修訂,形成最終問卷。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68 份,最終回收有效問卷202 份,回收率為75.37%。

圖1 假設模型
(二)變量測量
自變量為網絡關系特征、網絡結構特征和創新環境。網絡關系特征包括網絡關系強度(RS)和網絡關系穩定性(RF),主要借鑒Uzzi(2010)、吳曉冰(2009)等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網絡結構特征包括結構洞(RH)和網絡密度(ND),參照Hagedoom 和Roijakkers(2006)、王海花和謝富紀(2012)等研究成果;創新環境包括集群氛圍環境(AE)、社會文化環境(SE)、要素環境(EE)和集群政策環境(PE),借鑒Brenner 和Weigelt(2001)、劉磊磊(2004)和胡恩華(2007)等學者的相關量表。因變量為企業創新績效(IP),主要借鑒Ritter 和Gemunden(2004)、Bell(2005)等的量表,從企業創新產出、企業專利或著作權數和企業創新機構數三個方面來測量。控制變量為企業根植性(ET)與企業規模(ES),前者用企業運營年數來測量,后者以目標企業的員工數量和年銷售收入兩個指標測量。采用Likert 五級量表進行量化測量。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通過SPSS 21.0 進行數據處理,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每個變量均值都大于3,標準值較小,體現樣本間指標差別較小,說明南京軟件產業集群創新網絡已具備一定基礎,選擇軟件產業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
(二)信效度分析
常用克朗巴哈系數來度量樣本數據是否可信,從表2 可看出,除網絡關系強度外,其他變量的α值均大于0.80,問卷數據的可靠性良好。效度分析用來判斷設計題項的合理性,對網絡關系強度等9個變量進行KMO 值與Bartlett 球形度檢驗,可發現,現有變量的KMO 值最小為0.599,滿足大于0.5的要求,且p 值為0.000,小于0.01,通過了顯著水平為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本研究的量表設計合理,適合因子分析。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N=202)

表2 信效度分析
(三)回歸分析
首先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從表3、表4 可看出,VIF(方差膨脹因子)小于10,排除多重共線性問題;由F(方差檢驗量)可發現模型中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此外,調整后的R2趨于1遞增,可見模型的擬合效果隨著自變量的加入變得更優。

表3 回歸分析結果2(N=202)

表4 回歸分析結果2(N=202)
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1)集群創新網絡關系強度與集群內企業的創新績效間關系不顯著(P>0.05),即假設H1a 不成立;另一方面,雖然網絡穩定性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是顯著的(P<0.01),但這種影響是消極的(β<0),所以假設H1b 也不成立。究其原因,在集群創新網絡形成初期,關系的過度嵌入使得網絡內企業刻意保護集群內部合作,忽略了更為優質的外部資源;而網絡內企業各種往來關系潛移默化使各方面趨同,長此以往抑制集群內企業創新。(2)創新網絡的密度和結構洞均對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P<0.05),假設H2a 與假設H2b 都得到了驗證。(3)社會文化環境、集群政策環境和集群氛圍環境與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β>0,P<0.05),假設H3b、H3c、H3d 均得到了驗證;要素環境對集群內企業創新績效沒有顯著影響(P>0.05),假設H3a不成立。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以南京軟件產業集群企業為調查樣本,實證研究了集群創新網絡中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結論如下:集群創新網絡關系特征的關系強度維度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并不顯著,而關系穩定性維度與企業創新績效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軟件產業集群創新網絡結構與企業創新績效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并且主要通過企業所處網絡的結構洞和網絡密度表現出來;集群創新環境部分正向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
根據結論,提出以下對策建議:第一,創新網絡形成初期,企業間合作關系的過度嵌入使企業產生行為惰性,進而失去可能優越的外部創新資源。因此企業要在謀求網絡關系穩定的同時,防止關系僵化,以更好吸收先進知識,突破創新瓶頸。第二,創新網絡中,企業處于結構洞位置,網絡密度越大,企業的創新績效越優。因此企業可調整自身所處網絡的節點位置,以獲取精煉、合理的資源,進而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第三,目前南京軟件產業集群仍處于上升期,所處區域的創新環境時刻變化,難以合理適應,企業的創新能力與創新績效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企業要對集群氛圍環境充分利用,依靠自身資源稟賦提升創新績效。與此同時,還要根據外部要素環境適時調整創新策略,以突破創新邊界,獲得最優創新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