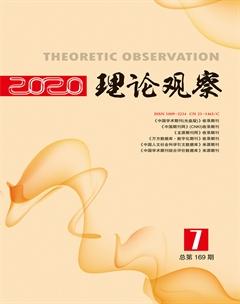社會流動與中國農(nóng)村政治穩(wěn)定的內(nèi)在邏輯
陶富林
關(guān)鍵詞:農(nóng)村;政治穩(wěn)定;社會流動
中圖分類號:D42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0)07 — 0084 — 03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到農(nóng)村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鐘擺”角色,既可以成為穩(wěn)定的根源也可以成為革命的根源〔1〕p89。近年來農(nóng)民生活條件不斷改善、農(nóng)村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政治格局總體穩(wěn)定。但面對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區(qū)與深水區(qū)這個社會轉(zhuǎn)型的巨大難題,社會總體穩(wěn)定的格局會不會受到新的沖擊?如何繼續(xù)維持農(nóng)村政治的相對穩(wěn)定狀態(tài)?如何更好地處理改革、穩(wěn)定、發(fā)展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學界對這一現(xiàn)象的解釋視角要么強調(diào)國家宏觀政策與體制〔2〕;要么突出了農(nóng)民政治行動與政治心理的主觀因素〔3〕;要么把客觀的經(jīng)濟指標擺在解釋農(nóng)村政治穩(wěn)定原因的首要位置,而忽視農(nóng)村社會的現(xiàn)實性變動條件〔4〕,都未能很好地解釋我國農(nóng)村社會長期保持穩(wěn)定的原因。基于此,筆者認為從亨廷頓從社會流動的視角出發(fā)將農(nóng)村放在整個社會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中分析不僅符合社會動態(tài)發(fā)展的特征,也符合我國社會各階層間流動的事實,可以更好地闡釋社會流動與中國農(nóng)村政治穩(wěn)定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
一、亨廷頓的社會流動理論
(一)社會流動的政治內(nèi)涵
亨廷頓用三個公式概括了社會流動的政治內(nèi)涵:社會動員/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頹喪、社會頹喪/流動機會=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動亂〔5〕p3。在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為落后的農(nóng)村地區(qū),當社會動員不能滿足人們的社會欲望的時候,社會矛盾就會被激發(fā),農(nóng)民只能通過超負荷的政治參與排解內(nèi)心的社會頹喪感,但政治參與一旦超過政治制度化水平承載的范圍,就會引發(fā)農(nóng)村地區(qū)的政治動亂。基于此,亨廷頓認為社會流動是排解社會頹喪感、治愈政治動亂的最佳途徑。社會流動為農(nóng)民提供的增收渠道和經(jīng)濟效益可以有效替代政治參與所獲得政治補償,使得政治參與回歸制度化所能承受的水平和農(nóng)村政治相對穩(wěn)定局面的實現(xiàn)。
(二)社會流動的表現(xiàn)形式
亨廷頓把社會流動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表現(xiàn)形式〔6〕p234,橫向流動是指農(nóng)村人口從鄉(xiāng)村地區(qū)流向城市地區(qū)實現(xiàn)都市化的過程,通俗的來說就是農(nóng)民的居住地由農(nóng)村轉(zhuǎn)移城市,生產(chǎn)方式由農(nóng)業(yè)轉(zhuǎn)向非農(nóng)業(yè)。縱向流動是指原本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原有的職業(yè),流動到更好的工作崗位上使得收入水平得到提升。本文中所論述的社會流動主要是指中國農(nóng)民在現(xiàn)代化的浪潮中通過國家提供的橫向流動機會,實現(xiàn)由農(nóng)村向城市的地域轉(zhuǎn)移,改變原有的居住場所、生產(chǎn)方式、職業(yè)身份和以及經(jīng)濟狀況的過程。
(三)橫向流動面臨的淤塞
亨廷頓洞察到農(nóng)民通過社會流動改變自身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同時也會面臨一些淤塞〔7〕p128。一是橫向流動到城市的農(nóng)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隨著社會階層結(jié)構(gòu)的代際更替,第一代流動者的子女在城市環(huán)境下長大融入城市的精神需求比父輩更強烈,新的“相對剝奪感”由此產(chǎn)生,會對社會穩(wěn)定造成新的沖擊。二是社會流動會造成農(nóng)民群體間的收入分化加大,農(nóng)村內(nèi)部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分層導致經(jīng)濟利益的分化與沖突。第三,社會流動會改變離鄉(xiāng)進城務(wù)工人員對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化與價值觀鄉(xiāng)村的認知,形成新一輪的鄉(xiāng)村認同危機。
? ? ? 二、社會流動與中國農(nóng)村政治穩(wěn)定的內(nèi)在邏輯
(一)利益分化:社會流動欲求激發(fā)
傳統(tǒng)小農(nóng)經(jīng)濟體制下的農(nóng)民被嚴格地束縛在其所居住地域的土地上,那種先賦性、繼承性和不可更改性的農(nóng)民固化階級身份和農(nóng)村封閉的層級結(jié)構(gòu)造成了農(nóng)村幾乎沒有任何社會流動的機會的“與世隔絕”狀態(tài)。隨著市場經(jīng)濟興起,社會結(jié)構(gòu)開始發(fā)生轉(zhuǎn)型,利益主體分化趨勢日益顯著。農(nóng)村傳統(tǒng)保守的觀念被打破,民眾內(nèi)心不再滿足過去那種自給自足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對物質(zhì)生活的渴求被激發(fā)。但農(nóng)村的發(fā)展速度遠比不上農(nóng)民這種對社會渴求欲望增長的速度,這就形成了現(xiàn)狀與欲望之間的落差。再加上城市工業(yè)化的發(fā)展進一步拉開了城鄉(xiāng)差距,貧富差距使得農(nóng)民的社會挫折感和相對剝奪感更加強烈,社會流動的訴求和呼聲日益強烈。
(二)經(jīng)濟滿足:農(nóng)民的社會受挫感降低
自20世界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城鄉(xiāng)二元分割體制逐漸打破,農(nóng)民重新獲得在鄉(xiāng)際間和城鄉(xiāng)間自由遷徙的權(quán)利。農(nóng)村生產(chǎn)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不僅激發(fā)了農(nóng)村生產(chǎn)活力,還大大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為農(nóng)村政治穩(wěn)定奠定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chǔ)。除此之外,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還大大釋放了農(nóng)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而這一點剛好迎合了城市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勞動力需求。農(nóng)民從農(nóng)村流向城市不僅打破了過去單一的農(nóng)業(yè)收入格局,在加上市場經(jīng)濟在本質(zhì)上接受個人的努力和能力,農(nóng)民在物質(zhì)基礎(chǔ)上獲得極大的滿足感,實現(xiàn)收入增長的同時社會受挫感也大大降低。農(nóng)民在城市發(fā)展中貢獻的力量也極大地推動城市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fā)展,大大推進了我國城市化的發(fā)展進程。
(三)觀念轉(zhuǎn)變:制度化水平與政治參與相對平衡
社會流動的實現(xiàn)不僅改善了基層民眾物質(zhì)生活水平,還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們對政治制度的認知。過去基層民眾往往把不滿情緒的原因歸為制度政策,認為只有通過上訪、群體性事件、訴訟等政治參與的方式來才能維護自身利益,但政治參與一旦超出了制度化載體所能容納的范圍必然導致政治不穩(wěn)定發(fā)生。隨著社會流動的實現(xiàn),農(nóng)民越來越多將主要的精力轉(zhuǎn)移到謀求經(jīng)濟收入上。“錢能解決一切的思想”逐步占據(jù)了鄉(xiāng)村主流,民眾的政治參與動機逐漸下降。另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shè)與基層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同步進行,促使民眾政治心態(tài)逐步發(fā)生改變。再加上社會流動的過程本身就是基層民眾增加對社會和制度本身認同的過程,經(jīng)濟收益大大緩解了民眾對政治的不滿情緒,民眾借助政治渠道爭取權(quán)利的這種觀念逐漸被物質(zhì)層面的經(jīng)濟滿足所取代,從而使得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回歸到相對平衡的狀態(tài)。
三、社會流動理論對農(nóng)村維穩(wěn)工作的現(xiàn)實啟發(fā)
(一)農(nóng)民回流:農(nóng)村穩(wěn)定的主攻方向
亨廷頓的社會流動理論更多的是從“平流”和“上流”的角度來探討社會流動與政治穩(wěn)定之間的關(guān)系。面對科技賦能的大背景和生產(chǎn)智能化的大趨勢,人工智在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運用使得工廠和企業(yè)給農(nóng)民提供的崗位明顯減少是農(nóng)民選擇回流返鄉(xiāng)的重要原因。另外,隨著國家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大力實施,鄉(xiāng)村集體經(jīng)濟的發(fā)展,勞動力就地轉(zhuǎn)移機會日益增多,為農(nóng)民“回流”返鄉(xiāng)置業(yè)提供了重要保障。農(nóng)民回流對農(nóng)村穩(wěn)定的帶來的挑戰(zhàn)有:一是基于過去鄉(xiāng)村土地承租和流轉(zhuǎn)制度的不完善,有可能會引起農(nóng)民和留守農(nóng)民之間的土地矛盾與糾紛,從而對政治穩(wěn)定的構(gòu)成潛在威脅。二是在返鄉(xiāng)農(nóng)民這一龐大的群體中并不排除一些在城市中賺得了較為豐厚的經(jīng)濟收入,回鄉(xiāng)后覺得自己財大氣粗,甚至會聚集鄉(xiāng)村混混打牌賭博、打架鬧事等破壞鄉(xiāng)村秩序的行為,這也是農(nóng)民回流對鄉(xiāng)村穩(wěn)定一大威脅。針對農(nóng)民“回流”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基層政府應該及時進行政策的調(diào)整與監(jiān)督,積極推動落實農(nóng)村勞動力就地轉(zhuǎn)移,實現(xiàn)農(nóng)村內(nèi)部就業(yè)系統(tǒng)的有效循環(huán),幫助返鄉(xiāng)農(nóng)民實現(xiàn)鄉(xiāng)村融合,吸納返鄉(xiāng)農(nóng)民積極投身于鄉(xiāng)村振興的實踐。
(二)村民參與:農(nóng)村穩(wěn)定的內(nèi)生動力
村民自治存在兩難,一是難在監(jiān)管,二是難在參與,尤其是隨著農(nóng)民經(jīng)濟條件的改善,民眾政治參與的動力明顯不足,鄉(xiāng)村發(fā)展面臨嚴重的“人才危機”。如何實現(xiàn)新時代背景下農(nóng)民政治參與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再平衡,是亨廷頓提出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平衡帶給我們的現(xiàn)實沖擊。亨廷頓認為只有將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維持在相對平衡狀態(tài),社會才會呈現(xiàn)相對穩(wěn)定狀態(tài),過高或者過低都不行。反觀農(nóng)村70年的發(fā)展歷程,一方面農(nóng)村的變化驗證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實踐,另一方面我們也即將面臨新一輪的鄉(xiāng)村政治參與危機,當前我們的農(nóng)村并不是政治參與超過制度化的水平,而是村民自主參與小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水平。亨廷頓提出應該通過鄉(xiāng)村動員或“綠色起義”的途徑重建政治穩(wěn)定, 所謂綠色起義就是指通過擴大政治參與的方式引導農(nóng)民參與政治生活, 用制度化的體制進行疏導才能保持政治穩(wěn)定的長久態(tài)勢〔8〕p86。政府應積極拓展自下而上的階層流動渠道,消除階層之間的隔閡,實現(xiàn)基層民眾政治參與重新適應當前基層政治體制的需求,這是維持政治穩(wěn)定的關(guān)鍵所在。
(三)社會融合:農(nóng)村穩(wěn)定的價值所在
從柏拉圖提出的勞動分工論到哈耶克倡導的權(quán)力至上的自由主義,再到羅爾斯奉行的平等分享權(quán)利同時承擔義務(wù),我們可以看出從古至今社會差異無處不在,更何況是生活在當前這個人生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錢生錢的速度的時代,何談消除差異?亨廷頓提出政黨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很好地扮演了社會政治壓力疏導者的角色,在社會差異的中間地帶正是黨和政府大展身手的舞臺,本著尊重差異、正義約束的執(zhí)政、施政理念實現(xiàn)社會兜底政策再分配的公平與正義,讓人民真正感受差異背后的正義,這是實現(xiàn)政治穩(wěn)定的重要保障。十九大明確提出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槿嗣駥γ篮蒙畹南蛲桶l(fā)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就是要把“人”放在首位。不論是在推進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還是面對新一輪的農(nóng)民“回流”潮,實現(xiàn)穩(wěn)定的關(guān)鍵都在于“人心”,也正好驗證了那句“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冷酷無情,社會規(guī)則也不是類似于馬拉松式的淘汰機制,而應該是一種建立在社會流動基礎(chǔ)之上、有利于促進社會良性循環(huán)的新陳代謝機制,最終實現(xiàn)人與人、地區(qū)與地區(qū)、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這才是追求政治與社會穩(wěn)定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參 考 文 獻〕
〔1〕〔5〕〔6〕〔7〕〔8〕亨廷頓.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9.
〔2〕徐勇.論中國農(nóng)村“鄉(xiāng)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穩(wěn)定與完善〔J〕.社會科學研究,1997,(05).
〔3〕肖唐鏢.從農(nóng)民心態(tài)看農(nóng)村政治穩(wěn)定狀況〔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05).
〔4〕黨國印.當前農(nóng)村社會穩(wěn)定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1997,(03).
〔責任編輯:孫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