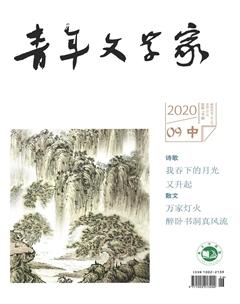虛妄之欲:從拉康的欲望理論看《連環套》中霓喜的悲劇性
任祥欣
摘? 要:張愛玲的《連環套》描寫了霓喜的姘居生涯,上演了一出連環套式的女性悲劇。從拉康的欲望理論來看,霓喜的“欲望”實則是被“攻擊者認同”所異化的對于權力的渴望,而她的悲劇性在于她僅能追求欲望的短暫性補償,卻無法獲得一種穩定長久的“要求”機制,因此陷入了虛無之虛無的輪回,這對心理活動日趨復雜細密的現代社會有著思考與警醒價值。
關鍵詞:《連環套》;霓喜;悲劇性;欲望理論;認知錯位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6-0-02
張愛玲的《連環套》描寫了霓喜與一系列男人的姘居生涯,上演了一出連環套式的女性悲劇。但霓喜的悲劇性并不能直接地歸于社會環境、女性地位以及所謂的命運,正如張愛玲分析道: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1]。這一缺陷是拉康語境下,“偽主體對本體論意義上的缺失之物永不可能實現的欲求”[2],是霓喜的“理想自我”同他者眼中“霓喜”的錯位。本文運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批評,通過對《連環套》中敘事者與霓喜兩種視角的文本細讀,為霓喜的悲劇性提供了一個拉康式的解讀。
一、視角分歧間的“需要”與“欲望”
《連環套》文本的開端時間是賽姆生太太(即霓喜)六十歲開外時,大抵與作者寫作時期處在一個年代,隨后便整體閃回到五十多年前,從霓喜被鄉下養母賣到印度人雅赫雅的綢緞店起,先后與幾個男人姘居以及偷情,最后終于自己不再年輕,不足以吸引男人時,才大夢初醒,明白了男人的靠不住,決定要靠孩子。小說自此被腰斬。
從文本的敘述中可以發現存在兩層視角:一層是外敘述者“我”的視角,而“我”的視角是接近于全知敘述,是比較客觀的他者的視角,代表他者眼中的霓喜,能作評價,幫讀者厘清霓喜的話哪句是真的,哪句是謊言;另一層是霓喜的視角,霓喜眼中的自己是童年養尊處優,有著傳奇性的邂逅等等的,但這些都被“我”識破,并不留情面地告訴讀者——都是假的、杜撰的,還用嘲諷的口吻說,霓喜的話“原是靠不住的居多,可是她信口編的謊距離事實太遠了,說不定遠兜遠轉”,“偶爾也會迎頭撞上了事實”。不過霓喜那些“靠不住的話”“信口編的謊”卻暴露了霓喜欲望的蹤跡。
在拉康的視閾中,“欲望”往往構成主體生存的內在動力。這里的“欲望”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講的“力比多”,因為“力比多”不過是對“具體的缺失對象”的生物性的“需要”,一旦獲得對象,則得到滿足。而從“需要”到“欲望”中間有一個“要求”的環節,來實現從具象需要到非具象欲望的轉變。“要求”有兩個指向:一是需要的對象,二是向其發出要求的他者——一個不在場的在場。“他者”可以是小時候的鏡像、父母或者玩伴的目光等小他者,也可是人進入語言的“象征域”中由語言構建起來的大寫的他者。拉康悲觀的宣布“欲望”就是不可能實現的他人之要。[2]
“欲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很顯然霓喜那些“信口編的謊”只是她的“需要”,因為那些珍珠粉、錢、傳奇故事都是非意象的,她真正的“欲望”還在他處,需要我們回到文本中尋找答案。
二、“攻擊者認同”下的權力幻想
霓喜的第一段婚姻,按照敘述人“我”的說法,霓喜是被雅赫雅跟養母討價還價后用一百二十元買的,但霓喜還添了一段與雅赫雅在河上早已一見傾心,雅赫雅發財后將她贖回的浪漫傳奇,不過敘述人“我”給這一傳奇作了“多半是她杜撰”的宣判。這不禁讓人想起福樓拜筆下那個幻想著騎士浪漫愛情的愛瑪,她的悲劇是由于情感欲望的匱乏。不過霓喜明顯區別于愛瑪,霓喜的出發點更加現實,比起為愛獻身她更需要的是愛情帶來的利益。也有文章認為霓喜的悲劇在于屈從了女性的命運,被迫“只能將婚姻作為籌碼換取生活保障”。[3] 可是霓喜并沒有一心專注于“生活的保障”中,不然她不會一氣之下離開赫雅自己卻連一點體己都沒能攢下,不會在與第二個男人竇堯芳姘居時還給崔玉銘花錢、偷情,在堯芳死后不愿回鄉下,也不甘給崔玉銘做小,負氣離開。
敘述人“我”的聲音分析過,霓喜所需要的是“一點零用錢與自尊心”。自尊,符合“欲望”的非具體性,但既然她要的是自尊,為何還要宣揚自己是雅赫雅“一百二十塊錢買的”?像張愛玲說的“相安無事”,白頭偕老,豈不是能夠獲得一種更長遠,更讓能獲得自尊的選擇?在筆者看來霓喜的“欲望”真正指向的是那種在兩性間甚至是同周圍人的關系中的支配感,不同于通常女性主義話語中的女性權利,而是讓別人聽從于她、順著她來的一種世俗的權力。
且看霓喜的幼年時期,她作為被繼母販賣的蛋家妹,從小就遭受非人的調教與凌虐。這段回憶被霓喜形容為“兇殘的古典”“貧窮與磨折”“禁忌”。在賣給雅赫雅時,霓喜還被羞辱性地“驗貨”,毫無權力所言。繼母還得意夸耀道,“若不是我三天兩天打著,也調理不出這么個斯斯文文上畫兒的姑娘”“換了個無法無天的”,“怕不磕磴得你七零八落的”。按照拉康的話語,霓喜此時處在想象秩序的“鏡像階段”,人會在“小他者”的凝視或反應中誤認自我,并將這初印象作為“潛意識”烙印在自己的一生中。可是霓喜并沒成為繼母訓練出的那種人,一個有趣的對照是,當霓喜后來真就無法無天地把綢緞店給砸了個雞飛蛋打。可見,“他者”對于自我的建構并不是簡單的傳教式的,而是存在一套復雜的機制。
弗洛伊德提出過一種認同過程被稱為“攻擊者認同”。這種認同模式常發生在“創傷性情境”中,是“對恐懼及無能感的一種防御”,被害者常會通過模仿所懼怕著的事物來解決自己充滿焦慮的窘境。[4]霓喜被視為“禁忌”的早年經歷便是如此,面對那任人宰割的艱難處境,只有通過認同這一他者的侵凌性行為,才能逃避那夢魘般的記憶,這種支配與被支配實質上就是一種權力關系。由于象征域的復雜性,霓喜對于權力的欲望并不是簡單地通過侵凌來實現的,而是由許多委婉的方式補償獲得的。故霓喜渴望的并不是那種傳奇邂逅,而是以此來想象自己憑借魅力誘導了雅赫雅心甘情愿地贖她回去;調戲藥店伙計崔玉銘并跟他偷情,也是因顧客與店員、老板娘與伙計的關系中的優勢地位;與第三位丈夫湯姆生,一是湯姆生屈服于她那種“悍然的美”,再就是她能憑借湯姆生加入英國國籍,獲得更高的地位。
甚至,霓喜每次被拋棄時都死守孩子,并非都是出于母性的本能,也是出于對權力的欲望。在霓喜被雅赫雅驅逐時,她摟住孩子,“要孩子來證明這中間已經隔了十二年了”,以擋住自己喪失權力的恐怖;霓喜的大女兒“是被霓喜責打慣了的”,鄙薄母親那一套,而“傾向天主教”。可見,孩子不僅是獲取權力的籌碼,更是她權力存在的證明,是她能夠掌握與控制的欲望客體。然而,當霓喜對孩子進行權力的侵凌時,在孩子身上也發生了“攻擊者認同”,只不過產生了一種“反向認同”。這也是“連環套”的一層意蘊。
三、無法抵達的虛妄悲劇
拉康認為,欲望是無法抵達的。誠然,每個人都有無法達成的欲望,但不是每個欲望的不可達成都是悲劇性的。霓喜的悲劇性在于她僅能追求欲望的短暫性補償,卻無法獲得一種穩定長久的要求機制。原因主要有兩點:
首先,近代香港駁雜的城市化環境塑造出獨特的城市文化,這為霓喜欲望的短暫性補償提供了可能。[5]姘居關系便是這種獨特城市文化的一種。這也為女性提供了一種解放自我、追求欲望的可能。在鄉下嚴密的宗法氛圍下,就不存在這種機會。所以當堯芳死后,竇家人來爭奪家產時,霓喜才記起那是“無情的地方”,不會讓霓喜放肆,頓時放棄了回鄉爭斗的念頭,凈身出戶。社會環境的變遷使得霓喜有了諸如傳奇遭遇、一夫一妻等幻想,姘居中的霓喜看似寄人籬下,可權力的種子時刻都在萌動中。
但近代香港的這種城市文化是很不穩定的,且姘居關系是以男性主導,男方一旦出現變故,如堯芳的離世、湯姆生的結婚,霓喜的幻想就立刻化為泡沫。這涉及第二個原因——霓喜始終個人無法認清自己在權力關系中所處的位置。
霓喜自恃美麗、精明,足以誘惑男人為她效力,在想象中自己是居于權力的主導一方。可事實是,在她那想象中有限的權力,全部是男人賦予她的,這是霓喜的“理想自我”同他者眼中“霓喜”的錯位,由此陷入了悖論:欲望的滿足實則是虛無中的虛無。直到結尾,霓喜尷尬地發現發利斯看中的是她大女兒而非她時,才似乎醒悟,“知道她是老了”,仿佛有點什么東西“破碎了”。于是,霓喜的后半生把欲望的對象瞄準了自己的孩子。她以為在母親-兒女這對權力關系中,能夠占據主導的地位,殊不知從大女兒開始就蒙下反叛的種子。
霓喜的欲望悲劇是因不穩定的城市文化和自我認知錯位造成的無法擺脫的困境,她終生的忙碌只是虛無,正如連環套一樣,環環相扣,無盡輪回著,無法走出。
四、總結
心理分析,尤其是女性心理的分析是貫穿張愛玲小說創作的一條線索,也是張愛玲一直被人們討論、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從自甘沉淪的葛薇龍到缺乏性啟蒙的愫細,再從于調情中謀生的白流蘇到于壓抑中毀滅的曹七巧,都為現代文學中的人性描寫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連環套》更是將筆觸伸入到不常被人關注的姘居關系中。從拉康的“欲望”角度,發現了霓喜對權力的虛妄追求,為其悲劇性的成因發現了一種新的可能,這在心理活動愈趨復雜和細密的現代社會,有值得人思考與警醒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張愛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北京,2009.
[2]張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一一拉康哲學映像》[M].商務印書館:北京,2008:299-318.
[3]周娟.漂若浮萍,韌如勁草——淺析張愛玲《連環套》中霓喜的人物形象[J].成都師范學院學報,2014,30(06):79-82.
[4]麥克威廉姆斯 編 鐘慧 譯.《精神分析案例解析》[M].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北京,2004:107-118.
[5]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第二版)[M].北京大學:北京,2013:259.
[6]張愛玲.《郁金香》[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北京,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