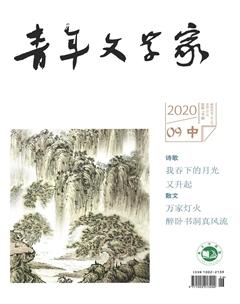“書如其人”之吾觀
摘? 要:在書法藝術上,宋代蘇軾曾指出“凡書,象其為人。”以“君子”、“小人”論書,有著時代與個人遭際的特定背景。作為一個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其論書不免摻入道德與政治的因素,因此東坡生平三次遭貶。當然他所提出的“書如其人”的命題十分深刻而重大,它承襲了許慎的“書者,如也”的觀點;也深化了楊雄的“書為心畫”的觀念,從宏觀上進一步揭示了書法藝術與創作主體的本質聯系,并啟導后世對這一命題不斷的探討。
關鍵詞:書如其人;生平三貶
作者簡介:郭剛(1978.12-),男,漢,甘肅省隴西縣人,本科,隴西縣文峰中學副高,研究方向:書法理論與技法。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6-0-03
提到“書如其人”,人們就會想到蘇軾,那么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蘇軾其人。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其父蘇洵、弟弟蘇轍皆以文學名世,世稱“三蘇”;嘉祐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學識淵博,喜獎勵后進,其文明白暢達。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蘇軾還擅長行、楷書,取法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并上溯晉宋諸名家,而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黃庭堅在《山谷集》里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蘇軾性格生性豁達,為人坦率認真,他用自己的詩詞表達著他對人生的感悟和對社會的態度。在他的性格中,既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的婉約;既有“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時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窘迫;既有“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瀔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頓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絕唱。一方面,學識高,見識廣,品味與境界也就高,也就不把書法繪畫當成一個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在蘇軾眼里,作文寫字繪畫,只不過都是表情達意的東西而已,只求自然天成。只因如此,蘇軾“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問君何若寫吾真,君言好之聊自適”。“凡物之可喜,是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透露出作為士大夫文人的蘇軾把書與畫作為表達自己感情的載體,追求自我性情的抒發。另一方面,他對前人也很欣賞。他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總體評價時說,“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意思是,他認為杜甫的詩、韓愈的文、顏真卿的書法、吳道子的繪畫至善至美,能達到他們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為止了。他的一生雖是豪放豁達,但仕途多舛,起伏跌宕,數起數落。
一、蘇軾命運多舛、生平三貶
第一次是1080年因“烏臺詩案”入獄起,蘇軾開始了他的第一輪人生低谷。入獄100余天,差點丟了性命。后來還是因為趙匡胤曾經說過不殺賢士這樣的話,以及家人與朋友的積極營救,蘇東坡這才逃過一劫。 因為蘇軾自從進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對由王安石領頭的‘新法一派,再加上當時的他在文壇上地位很高,他的詩詞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是很大的,這也就間接阻撓了‘新法的推廣,引起了變法派對他的強烈不滿,他的政治對手將他所有詩詞收集起來,成為在朝堂上攻擊他的理由和借口。他們指控蘇軾寫詩文訕謗朝政、反對新法、指斥皇帝,要求處置蘇軾。這就引起了皇帝的不滿之后被貶。
第二次是被貶惠州,正是因為與蘇軾的為人有關,至新黨勢力倒臺,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等人上臺,蘇軾被召回重用時,蘇軾又看不慣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再次反對新黨。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隨后被外調,外放。至新黨再次上臺,又再遭貶官。但是這一次蘇軾可以說是很無辜的,守舊派的領導人物當時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變法派抓住機會一度成為朝廷上的主導力量,守舊派因此被變法派大肆打壓,蘇軾也因為一貫所站的立場,再加上當時的他是元祐黨人的領袖,被變法派全面打壓,也再次被貶。但被貶后的蘇軾心里面也怡然自得,到惠州時值深秋,蘇軾看見驛站邊的樹木依然翠綠欲滴,便問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樹,小吏回答是荔枝樹,蘇學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嶺南”,原來蘇軾本人生平酷愛甜食。在別人眼中的嶺南煙瘴之地在蘇軾眼中卻是洞天福地,同時心滿意足地賦詩一首:“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
第三次是被貶儋州,這次被貶的原因比上次更簡單,新派雖然已經在朝堂上占了上風,但是為了將舊派徹底壓的再無出頭之日,新派對舊派進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規模的打擊,所有的舊派人員被貶了一遍之后,為了以防萬一又再一次被貶遠,蘇軾也在其中。1097往海南;謫居海南儋州,是蘇軾生命中最艱難的歲月。那個時候海南島還是一個蠻荒之地,是朝廷流放那些嚴重的、死不改悔的罪臣的首選場地。到了那里,真乃天高皇帝遠,你造不了反,發點兒牢騷也沒有人聽得見的。家破人亡的蘇軾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準備。“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
只有經歷了這些風浪的洗禮,才會有充滿激情和跌宕起伏的詩文、書法及書論,或悲憤,或平和,或喜悅。這些情感隨著人生波動而通過他的詩文反映出來,也通過他的書法體現了出來,更是通過透徹精細的書論體現出來。
二、蘇軾書論之吾觀
1、蘇軾歷經人生磨難,論書重人品與學養
蘇氏論書,看重的是書家的人品,因為書法不只是“藝”,而更是書法家的“德”,重視書家的品德修養,是中國古代書法批評的一個優良傳統,就整體來說,后者自然是根本。當人品作為書法評品的基點后,這方面的議論成了書論的一個重要內容與特色。“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書唐氏六家書后》)論書強調書家的品德修養,也是儒家“君子立身務求其本,本立而道生”這一正統觀念的引發,同時也因為書法與人心的內在聯系,比起其他技藝方面有更直接的一面,即所謂“書為心畫”。在宋代文人重道德、尚氣節的意識愈加強烈。在蘇氏之前,歐陽修對此早就有所涉及:“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公書雖不佳,后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于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筆說·世人作肥字說》)正所謂“敬其人益愛其書”。“斯人(按:指顏真卿)忠義出于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也。”(《集古錄跋尾》)提出了書法形態與書家為人有著必然聯系的看法,這里雖只論及顏氏一人。然蘇氏則進而作出“書如其人”的論斷:“凡書像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書唐氏六家書后》)蘇氏從相貌著眼,認定歐陽詢的書法形態與其為人相像,未免臆斷,然而明確提出“書如其人”的重要命題,這在書論史上還屬首次。其實際內涵,則是“君子、小人”之說:“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勢不回之。”(《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書唐氏六家書后》)
其所說書作的“峭峙不回之勢”,則當與錢氏的性格、氣質一致,因為人的性格、氣質會影響其審美取向。
“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則君子、小人必見于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為人而已,凜乎若見其消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見其為人邪正之粗云。”(《題魯公帖》)
蘇氏以“君子”、“小人”論書,有著時代與個人遭際的特定背景,但并沒有將書法與人品完全相提并論。蘇氏論書亦極重書家的學養。“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妙。”(《東坡集》)“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
大抵學養深厚,其書作格調高雅,內涵豐富,意境超遠。蘇氏本人即是很好的例證。
“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耳。”(黃庭堅《山谷集》)
“(東坡草書)縱橫斜直,雖率意而成,無不如意……蓋其才德文章溢而為此,”(倪瓚《云林集》)事實上,只是從書作的審美,可以看出書家的性格;從書作的格調,可以看出書家的學養;從書作的情趣,可以看出書家的才氣。清人劉熙載便總結說:“書者,如也。如其才,如其學,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藝概·書概》)這就是對“書如其人”更近于實際的闡釋。至元、明之際,有些人將此走向極端,認為“人品即書品”,拋開藝術賞評的客觀標準,把書法批評變成道德評判,從而因人廢書,這就遠遠背離了蘇氏的本意。
2、蘇軾才情豁達豪放,論及書法追求新意
在書法領域,蘇軾孜孜以求的則是“新意”。“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孫莘老墨妙亭詩》)“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書唐氏六家書后》)“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于?墨之外矣。”(《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書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后》)前二則論及顏、柳二家之所以成大家,皆由其能創出新的意態。第三則言智永雖欲葆王氏家法,然其書亦自有意態。最后一則雖是論畫,當與論書相通,即要在前人的法度與豪放的風格中,創出全新的意態,進而寄寓精妙的理趣。再看蘇氏的夫子自道:
“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塊也。” (《評草書》)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石蒼舒醉墨堂》)
前一則講自己總的藝術追求。正所謂“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這一提法帶有強烈的“個性”意識,即不襲古人的面目,而要創出帶有鮮明個性特色的意態。“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我于黔安(按:即黃庭堅)亦云。”(《跋山谷草書》)可見蘇氏對個性風格的推重。縱觀宋代幾位代表性書家,無不是以自己迥異于前人,個性獨具的筆墨意態光耀書壇,從而開拓了書壇一代新風,使宋代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自己獨特的地位。通觀《黃州寒食詩帖》《赤壁賦》等眾多代表性書作,我們可以體悟到,蘇軾正是借助創出全新的筆墨形態,從容地抒發著“這種整個人生空漠之感,這種對整個存在、宇宙、人生、社會的懷疑、厭倦、無所希冀、無所寄托的深沉喟嘆”。(李澤厚《美的歷程·蘇軾的意義》)
后一則講實踐這一藝術追求的途徑。所謂“意造本無法”,即以己意作書而不拘于前人的成法。馬宗霍說:“東坡自謂‘我書意造本無法,實則本之平原以樹其骨,酌之少師以發其姿,參之北海以峻其勢。”(《書林藻鑒》)這就是對各家法度的融匯與化解,達到“于萬法中求無法”。而蘇氏更以己意驅使之,從而逐漸形成適于表現已意的新法。正如清馮班所說:“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鈍吟書要》)這“本領”,也就是創出自己的新法。要使自己的新意自然而又充分地表現出來,就要率意而書,不在筆墨形態上刻意經營,即所謂“點畫信手煩推求”。
3、蘇軾書藝精湛,“尚意”書風逐漸形成
蘇軾在論述涉及“尚意”書風,不再考慮“助人倫,成教化”的政治功用,也不再奢談什么“書道玄妙”、“書通大道”的社會現象。而非常注重書法的“意態”、“意趣”、“意韻”,在他們心目中,書法不再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只是文人的一種雅好而已。看看蘇氏的說法:
“筆墨之跡,托于有形,有形則有弊。茍至于無,而自樂于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于博弈也。”(《題筆陣圖》)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余韻,于靜中自是一樂事。”(《記與君漠論書》)
“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游。”(《石蒼舒醉墨堂》)
就是說,學書、作書只是為了寓心適意,忘憂自樂,以求得精神的解脫。這一觀念的形成,還有承于其師、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的首倡。“蘇子美嘗言:明窗凈幾,筆觀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余晚歲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余。”(《試筆·學書為樂》)
“自此已后,只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試筆·學真草書》)正因為是文人寓意樂心的手段,其意興方能自然、率意地流露于筆墨間,這正是尚意書法的出發點。
“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書唐氏六家書后》)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跋懷素帖》)
“近日米蒂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于世也。”(《論沈遼、米蒂書》)這些是蘇氏評定各家書法優劣的標準及著眼點,它們涵義相近,均指蘊含創作主體精神意緒的筆墨體現。“意態”偏重外部形態,“意趣”指形態中的趣味,“意韻”指形態中的雋永,而后二者皆寓于“意態”之中,并借“意態”來體現。蘇氏在評價智永書法時說,其“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句中“新意”與“變態”對舉,可知蘇氏著眼的“態”乃是“意”的直接體現。清康有為說:“故有宋之世,蘇、米大變唐風,專主意態,此開新黨也。”(《廣藝舟雙輯》),可知“意態”這一概念更接近于梁嫩所說的“宋尚意”之“意”的本意。“意態”的籠統說法就是“筆意”,其形成的總體內涵就是“意境”。宋人崇尚的“意態”,其實是擺脫唐法、足以體現宋代文人精神意蘊而又有獨特個性風格的筆墨形態。宋代尚意書法所以成就卓越,這與書法家具有深湛的學養有著重大關系。其代表人物如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皆是著名的學者與文學巨匠,他們廣博的學識成為其書法創作的深厚底蘊。
參考文獻:
[1]王世征 歷代書論名篇解析 文物出版社 2012年5月.
[2]劉玉才、許樹安、陰法魯 中國古代文化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3]李澤厚 美的歷程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