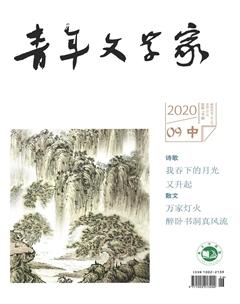以《情人》談杜拉斯的文化跨越
摘? 要:20世紀90年代,杜拉斯這個獨特的女性寫作者開始進入中國女性作家們的視野。東西方文化混合交錯的成長背景,使得杜拉斯的創作中總是帶有一種激烈的在東、西方文化上的內在沖突。她的書寫既體現著西方文化中對肉欲的歡娛、“隨意的性”的追求,又有著對東、西文化交錯的身份焦慮。
關鍵詞:杜拉斯;欲望書寫;流散;文化混合
作者簡介:陳琢,女,漢族,湖北黃石人,伊犁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6--02
自傳體小說《情人》這部作品的發表,使瑪格麗特·杜拉斯榮獲了法國龔古爾文學獎。作為一個被遺棄在印度支那殖民地這片土地上的法蘭西后裔,作家身份上的矛盾、家庭的重重變故激發著她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和想要向既定命運抗爭的強大欲望,也展現出跨越文化的生命力。
一、被肯定的欲望:追求肉體的歡娛
(一)“隨意的性”
在現代社會文明中,關于性愛的話語主要兩類:浪漫性話語、隨意性話語。浪漫性話語:愛是婚姻的實質,也是性愛活動唯一合法的理由。這一類浪漫性話語,在性文化更佳保守、壓抑和嚴肅的東方文化中體現更甚。另一種性愛話語是:隨意的性。“隨意的性”是指把性和性愛的歡娛本身作為追求的目標,更具動物天性地將性視為個人化的行為,而不看中世俗首肯的伴侶關系。隨意的性話語,一方面與二十世紀西方一系列婦女解放運動和女性經濟地位的改變有關,另一方面,與杜拉斯在矛盾交雜的東、西方文化中生長起來的叛逆天性有關:以打破貞操的方式打破命運的束縛。《情人》中十五歲的少女“我”,在欲念的牽引下一次次隨著那個中國情人去到人聲鼎沸的中國人生活區,進到那個充滿曖昧情調的、拉著純潔百葉窗的房間。在每一段性愛描寫中,少女“我”從來不是被動的,而是和“他”一樣“處在肉欲的狂熱”中,她被自然的野性指引,自愿而主動地奉獻自己的身體。顯然,“我”已將性愛比做一門技藝。性愛話語的嚴肅性、封閉性和私密性因此而被消解。當“貞操”不再是傳統東方文化中女性命運轉折的致命關鍵點,女性的幸福歸屬也從“是否處女”中被解救了出來。
(二)“無愛的性”
《情人》對性的“浪漫話語”的消解使我們發現,在西方文化中(以法國女性屬性為代表),性的意義是多元的。當性不再是“愛情”必然的結局時,性的意義便可以是“無愛的”。杜拉斯肯定了無愛的性,亦是為女性自身賦權。在《情人》中,我與中國情人之間的性不是買賣的要求,也不是愛情華麗的副歌。這里的性只是性:沒有是非,只是純粹的快樂。和而不同的是,西方女性的生理成熟往往比東方女性早8-10年。東方女性對自身生理欲望的自覺意識多在二十五歲以后(多數在成婚以后),而西方女性往往在十三、四歲便會呈現出生理上的成熟與完備:生理欲望也更早地自然萌動。作為流淌著法蘭西血液的西方后裔,即使在保守、傳統和性意識封閉的東方土地上,杜拉斯自身的生理成熟期顯然比東方女性更早。作家也因此在《情人》中將少女“我”對性愛的渴望描寫成為一種不容蔑視的、理直氣壯的美麗和純潔的力量。除了女性與男性之間的愛,杜拉斯諸多作品中都涉及到了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之間的精神之愛。如《情人》、《烏發碧眼》、《恒河女子》。“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決定了他的社會特征和異性戀的欲望”觀點已經被很多后現代性學理論家認為是一種在性別認可上的文化霸權。《情人》中的“我”,就是一個跟著感覺走的“酷兒”。正如波伏娃所言:“女人之間的愛是沉思的,撫摸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對方,而是通過她逐漸再創造自我”。
二、東、西方的成長經歷:混合的身份
(一)童年經驗理論
弗洛伊德人格理論中曾指出:人的童年經歷或者說是早期經驗會對他的一生構成影響深刻的潛意識。而杜拉斯在印度支那生活的童年經歷也成為她的作品中深刻的文化潛意識。無論是文字排版中對法語規范語法的刻意背棄,還是其作品語音語調中綿長無盡地帶著傷感音調的韻律,都使得杜拉斯文學作品中彌漫著一股濃郁絕望的欲望硝煙的味道。在1987年創作的《物質生活》中,杜拉斯就曾經提到她的故鄉是水鄉、是湖和湍流、是平原上充滿了泥土的味道的故鄉。童年在印度生長的杜拉斯,雖然具有法蘭西民族的膚色和血統,但是她心靈上真正的歸屬是東方文明中的印度,是一塊被熱帶季風常光顧的熱土。
(二)印度生活的凸透鏡
雖然杜拉斯的生命旅程經歷了東、西文化的混合,但是在她文學創作中起到最決定性作用的,是在法屬印度生活的那一段童年時光。杜拉斯畢竟是一個具有合法法國國籍、純正法國血統的西方人,無論在印度生活時她的家庭有多么貧窮和艱難,她和自己的家人也一直在不知不覺中享受著作為殖民地國家公民的優越感。在《情人》的開篇中作者寫到,即使在搭乘公交車時,司機也會把所有前排座椅空出來給具有殖民者身份的“我”們去坐。印度支那聯盟包括老撾、柬埔寨、東京、安南、交趾支那五個地區,其中東京、交趾支那、安南三個地區成為了法屬印度支那。杜拉斯的童年便是在西貢、河內、金邊這些地區度過。《情人》中不斷被強化的“我”哥哥的粗暴、“我”母親的瘋狂混亂、“我”的無病呻吟都反映了印度支那地區法國白人真實的生活狀態。杜拉斯的作品像是一副凸透鏡,以真實貼近的角度描繪了一個充滿著黑暗與貧困、滿目瘡痍的支那土地上的法國白人生長圖。印度支那地區的自然風景:《情人》中一次次被提到的湄公河、塞納河、印度恒河,以及熱帶地區特有的陽光與季風,都被作家一一汲取進了自己的文學世界。
(三)流散身份中的邊緣文化
“流散”這一詞,在阿什克洛夫特的《后殖民關鍵詞研究》中被定義為“人們從他們的家鄉自愿地或被迫地遷移——是殖民過程中的一個中心歷史事實”。二戰后,大量要求重返宗主國的原被殖民者和由經濟、文化等帶來的殖民主義之外的原因,導致了世界范圍內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些多元文化中的“流散者”在東方、及交雜的文化環境中反而擁有了一個更加廣闊的視角,因為對世界文化的改造與傳承產生了更大的主動性。杜拉斯與印度支那地區不是神交,她和家人一起“像越南人一樣講越南語、和越南孩子一起玩游戲”。在《杜拉斯的領地》中,杜拉斯甚至強調自己是越南人。這樣一來,文化層面上的杜拉斯就處于一種“無家”的流散狀態,她的心靈就會充滿焦慮與矛盾。事實上,當今世界人口正是經歷著越界大流動:移民、難民、流散社群、留學者,這些人處于不同文化之間感受到文化邊界的不穩定狀態。一方面,杜拉斯在《情人》中想要創造一個“欲望正義”的白人情人形象;而另一方面,她的越南性又使她作品中不斷表露著東方文化的真實。
三、“征服那個中國情人”——身份焦慮的投射
(一)中國情人性格上的“軟弱無力”
《情人》中,那個中國男人本是帥氣的巨商之子,但是在“我”的面前卻是這樣羸弱、被動。十五歲的、貧窮的“我”被杜拉斯塑造成了一個勇敢的、強悍的“男權”形象。在“我”對那個中國情人的情欲征服背后,其實也是一種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欲望征服。盡管那個中國情人已經在法國留學過,并且風流倜儻、家財萬貫。但是在貧窮的白人女學生面前,他依然有一種令人震動的“自卑”:第一次搭訕少女時,他由于膽怯整個人的聲音和手指都在顫抖著。此時的中國情人,雖然是生理上的男人,但是在文化特征上顯然已經被塑造成了具有東方文明色彩的“女人”。少女“我”更像一個剛毅勇敢的“男人”。那個中國男情人的身體那樣單薄,他的性格像殖民地的本地女人一樣嬌柔,他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地哭。中國情人像一個羸弱的怨女,在“我”面前哭訴:從文化層面上看,東方文明此時是被弱化、丑化的。如果說,杜拉斯在《情人》中為少女“我”所賦予的這份自信是代表了一種西方文化的自信與強勢的話,那個脆弱的中國情人形象無疑被當成了“低劣的、奴性的”東方文明的代表。男女關系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性愛關系,在創作者的潛意識里,特別是像杜拉斯這樣的作家,她們是在復雜的東西文化雜糅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文學作品中的男女關系體現出東、西方之間經濟地位和種族身份之間的較量。而中國情人軟弱無力的形象則無疑透露了作家在殖民時期的文化態度:西方文明正在強暴東方文明。
(二)中國情人的形象與法國社會的集體想象
殖民時期歐洲人對東方人的想象是否真的符合現實呢?“他們酷愛抽大煙和一夫多妻”是當時歐洲人對東方人極具代表性的集體想象。在《情人》中,少女總是很清楚自己與中國情人這份愛情最終的結局。值得注意的是,對“我”表露出無限深情的那個中國情人,卻沒有違抗父親的命令:他害怕失去父親財富的繼承權。于是作品中她的中國情人總是哭。在人物形象上,少女的情人也沒有男性符號的胡須、肌肉,而總是被描繪為瘦弱的、“經不起使人受苦的力量”、只有生殖器是旺盛的。對于當時的世界局勢,處于殖民者的西方國家一種集體自信的心理狀態,也在杜拉斯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明確的反映。
結語:
總之,“人總是生活在文化之中”,而作家生命經歷中的文化交融會更加深刻地體現在文學創作的深處,成為其作品深刻的文化內涵。瑪格麗特·杜拉斯的眾多作品,無疑都是20世紀里東西文明交融的代表產物。在那段世界局勢風云詭譎的時空里,杜拉斯以其獨特的文學語言發聲,將交融的生命欲望展現得淋漓盡致。
參考文獻:
[1]瓦里爾. 這就是杜拉斯 盧思社譯. 作家出版社,2010.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3]瑪格麗特·杜拉斯. 情人王道乾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4]弗洛伊德著. 夢的解析 賴其萬譯. 九州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