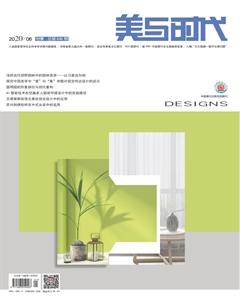圓明園的形象缺位與現代重構


摘? 要:長期以來,圓明園的形象缺位,造成了國人的審美經驗生成受阻,并最終影響了國人對圓明園價值的體認與傳承。圓明園形象缺位與現代重構研究立足新時代語境,嘗試探討新時代背景下圓明園形象的重構問題,找尋圓明園與其世界影響、歷史價值不夠匹配的根由,讓圓明園重現輝煌。
關鍵詞:圓明園;形象缺位;現代重構
有人認為,圓明園有兩個生命:一是作為皇家園林代表了中國園林最高成就和世界園林藝術的人類文化景觀;二是作為中華民族苦難與屈辱的見證、對中國和世界人民都有警示意義的歷史文化景觀。也許,這只是圓明園生命中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歷史階段:輝煌與滄桑(二者大致以1860年為界)。滄桑巨變造成了圓明園形象的缺位,這使得圓明園所蘊含的豐厚歷史文化能量長期得不到有效釋放。所以,繼輝煌與滄桑之后,“重生”同樣是圓明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謂“重生”,即形象缺位后,國人對圓明園形象的重構。這里,我們區別于長期以來學術界爭鳴不休的“重建”,而選擇“重構”,意在表明,圓明園的“重生”不僅表現在地面建筑的恢復、園林植被的配置、山形水系的修復,更重要以及更深層的“重生”,應該包括內在技藝與藝術精神以及文化之脈的傳承傳播。與單一的靜態景觀修復與重建相比,這種重構因為歷史場景的再現、歷史畫面的填充以及藝術技藝的審美化,大大增加了感知代入感而使得圓明園更具鮮活生命氣息。
1860年“大劫難”以來,圓明園的形象基本處于缺位狀態(公眾對圓明園的價值認知普遍不足,與其歷史地位、世界影響等實際影響力嚴重不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比較直觀的外表形象的缺位,比如地面建筑、橋涵、路面等園林基本構成要素的缺失;二是用以填補圓明園畫面感的人文歷史史實、場景場面、人物故事的缺位。前者源于1860年以來圓明園所遭受到的各種破壞,后者則很大程度上源于圓明園研究脈絡體系的不完整以及圓明園史實社會化普及力度的不夠。二個原因共同造成了普羅大眾對圓明園審美經驗的生成受阻,認為圓明園就是一堆大石頭而沒什么東西可看,最終影響了國人對圓明園價值的體認與傳承。
一、形象缺位下圓明園功能與價值的轉變
(一)遺址時期
1860年,英法聯軍所放大火對以木質建筑結構為主的圓明園是毀滅性的。除蓬島瑤臺、正覺寺等因為河水阻隔沒有被焚以外,圓明園幾乎全部被大火淹沒。損毀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在之后的歲月里,圓明園又遭遇多重破壞。比較嚴重的有這幾次:一次是對圓明園木料的破壞。據史料記載,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大臣倉皇西逃,趁火打劫者將圓明園內的建筑梁柱、木橋樁等鋸斷拉走,園內的大小樹木也被砍伐殆盡。據回憶,當時清河鎮上木材堆積如山,圓明園里只剩下山石湖泉了。一次是對圓明園石料的破壞。中華民國初年,圓明園成了北洋軍閥取之不盡的材料廠,據記載,徐世昌、王懷慶等人均有拆毀圓明園石料的行為,軍人押車每日10余大車拉運園中的石料。后來,園內的地面方磚、屋瓦、石條、木樁、木釘、銅管等也陸續被大車拉走,這一拉就是二十余年。除“火劫”“木劫”“石劫”外,圓明園遭受的第四次劫難是“土劫”。自宣統末年始,旗人們便在園內的宮殿舊址上修建房屋。20世紀40年代起,園外周邊農戶便陸續在圓明園內平山填湖,種植莊稼,萬園之園變成片片稻田而蛙聲一片,讓人感慨萬千。后來,住戶成片后還出現了管理單位,有些單位也相繼占據圓明園進行作業。這一時期,不僅圓明園的文物、建筑、收藏等損毀嚴重,作為園林基本要素的山、水、植被等也遭到嚴重破壞,導致圓明園喪失了作為園林的基本功能和價值,圓明園遺址于裊裊炊煙之中若隱若現。
(二)遺址公園時期
1976年11月,圓明園管理處成立,結束了圓明園將近一個世紀的荒蕪狀態。1981年,40余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議開辟圓明園遺址公園,并正式提出了“圓明園遺址公園”概念。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確定了“圓明園遺址公園”的名稱,并劃定了公園規劃范圍。1988年,圓明園作為公園正式向社會開放,成為了百姓休閑游憩的公共文化活動場所。
經過四十余年的保護與發展,圓明園遺址公園一步步完成了搬遷園內住戶、修筑圍墻、加強管理等三部曲(遷出去、圍起來、管起來),作為公園的功能基本實現。除了滿足游人休閑、游憩的公共文化服務功能外,作為遺址公園,圓明園還承擔著愛國主義教育職責。以中小學生為主的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目前已經成為圓明園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圓明園接待中小學生入少先隊、入共青團、成人禮等活動達千余場。圓明園南門附近的“不能忘記”,時刻警示青少年銘記“落后就要挨打”教訓,從小立志,胸懷家國而心系天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積極貢獻力量。
這是圓明園地面形象遭到損毀以后承擔起的新職能,貫穿圓明遺址公園發展工作的始終,但卻不是全部。因為從根本上講,圓明園是遺址,每一片瓦礫里都閃耀著文化的光輝。所以,我們需要在圓明園滄桑中銘記歷史,也需要在圓明園輝煌中尋找文化自信,更需要正視圓明園的形象缺位問題,力爭在形象重構中有效連接起三百年王朝文化、三千年傳統文化與五千年中華文明,進而點燃中華文化復興的星星之火。
關于圓明園形象的重構,國人的思考與討論從未停止。作為重要遺址,圓明園到底是保持原貌還是予以整修,或者復建?如果復建,復建的比例是多少?以什么時期的圓明園為復建依據等問題接踵而至。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始,有關圓明園形象重構問題的討論此起彼伏。比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幾種聲音:提倡原樣不動地保留廢墟的廢墟派、主張部分整修的整修派、立足園林自然生態環境營造的園林環境派等。
二、學界圍繞圓明園形象重構的幾種聲音
主張保留圓明園廢墟的學者認為,文物的價值不在于遺存本身,而在于它的見證價值、教育價值。圓明園遺址見證了近代中國由強而弱的歷史,保存遺址,有利于激發國人愛國情懷和啟發世界人民對于人類創造的輝煌文化的珍視。所以,應將文物遺址的歷史原初性放在文物保護的首要位置,并提出“廢墟也是一種美”“美是不可重復的”等美學觀點作為論證依據,得出“圓明園的輝煌是一次性的”“圓明園的美是無法重復的”等結論,進而推出圓明園作為中華民族國恥的永恒紀念碑也是無法被修復的。廢墟派認為,借助廢墟、遺址,觀賞者反而可以發思古之幽情、興懷古之審美想象。
與強調廢墟美的觀點不同,另一部分學者主張對圓明園山形水系在整體保護的前提下予以整修,同時對于部分景觀予以小范圍修復。他們認為這不僅有利于繼承中華民族寶貴的造園傳統,對于提高遺址公園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也大有裨益。與廢墟論者對圓明園滄桑史的強調不同,整修論者將圓明園150年的造園史與1860年后150余年的圓明園滄桑史統一于圓明園整體歷史之中,認為兩段歷史同等重要。從前150年歷史(1707-1860)中我們看到了清朝國力的強盛和盛世文化的繁興,圓明園代表了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又一高峰期杰作和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結晶。而后150年歷史(1860-今)則見證了近代中國在民族復興過程中所遭受的屈辱與磨難,二者共同見證了中華民族的興衰歷史。整修論者看到了圓明園整修的巨大意義,他們將圓明園重現輝煌視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象征。
進入新千年后,隨著圓明園東部游覽區的整修完整,有些學者注意到東部景區在整修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他們認為最明顯的問題是缺乏生態意識,未充分意識到植被、環境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圓明園里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在說話,每棵樹、每根草都會說話,所以要重視園內植被、植物景觀與遺址之間的關系問題。運用先進的生態理念保護生物的多樣性,尤其是鳥禽類,實現人與歷史、自然的和諧統一。
持續的論爭反映了國人對圓明園遺址的重視。廢墟論者一直強調的歷史原真性,原真性是文物與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原則。但對于這個“真”到底是以何時的“真實”為依據,學界卻鮮有共識。與廢墟論者強調文物的歷史見證功能不同,整修論者更加看重文化傳承,他們珍視隱藏在圓明園遺址中的文化基因符碼,并試圖通過部分恢復來獲取符碼信息,進而解鎖圓明園作為五千年中華文明積淀的價值所在。在講好中國故事、注重文化傳承的21世紀,整修論者的主張仍值得我們深思,思考圓明園的內在價值,以及圓明園價值與圓明園遺址價值如何統一等問題。至于自然生態環境論者則體現了我國人民文物保護意識與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雙崛起,這與古代中國人所倡導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謀而合,體現了中國人追求主客一體的精神實質。但是,由園林遺址轉變為生態濕地,邁出的步子顯得稍大了些。
文化、文物是時代的見證者,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離開了時代的文物是不鮮活的,沒有文物的時代是蒼白的。所以,文化需要代代傳承。作為圓明園人,我們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傳承好文化基因,讓中華五千年文明在中華大地上源遠流長。
三、新時代關于圓明園形象重構的幾點思考
眾聲喧嘩中,圓明園走過了快速發展的40年,成功地完成了遷出駐園住戶、駐園單位,圍起圍墻和管理起來的三大工作,初步整修后基本具備了公園要素并正式對外開放,作為滿足公眾休閑游憩的公園功能基本實現。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將圓明園列入全國100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幾十年的發展實踐表明,圓明園近40年的山形水系及橋涵、路段整修以及部分景點的考古發掘與清整,讓圓明園魅力指數不斷提升,聚起了更多人氣。2018年,圓明園游客人數超過一千萬人次,游客的滿意度表明,圓明園的基本整修還是十分必要的。
自從進入新世紀,談整修變色的年代基本終結,人們開始以更加理性、客觀的眼光來理解和看待圓明園問題。他們不再糾結于圓明園整修復建的比例,不再執著于建筑景觀的整體復原,而是著重強調圓明園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傳播中的獨特價值。因為他們堅信,隨著3D打印等技術的普及,圓明園3D復原是指日可待的,但圓明園所蘊含的豐厚藝術、文化、歷史價值卻有待于我們挖掘與呈現。這需要用一個個的歷史畫面、歷史人物、歷史故事、歷史事件來串聯起那段歷史,營構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歷史畫面,在活靈活現的歷史代入感中讓國人感受圓明園藝術乃至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精髓。與靜態建筑景觀相比,這種歷史復原顯得更加鮮活而有趣。總之,我們看到了國人在圓明園形象重構問題上的和解,與他人和解,最重要的是與每個人心中那個莊嚴雄偉的圓明園形象實現了和解。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圓明園理應發揮在傳承中華文化、凝聚中國力量、發揚民族精神方面的獨特作用,早日與其世界影響、歷史背景及其文化價值實現統一與協調。
作者簡介:李營營,博士,北京市海淀區圓明園管理處。研究方向:園林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