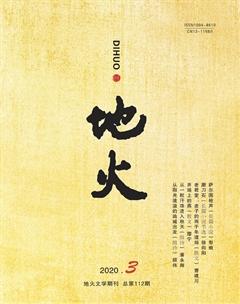老君堂:老子的兩千年道場
曹建川
我的主題在老君堂。
但是,半道上還是繞不開橫亙在路中央的一尊高達(dá)36.6米的鍍金觀音。以這個(gè)高度,我沒法撇開我的目光。何況觀音正慈眉善目地垂視著茫茫蒼生,還有眼前的我。
車剛一停下,一個(gè)中年男人從左手邊的南山寺快步而出。他面相疲憊,滿面塵灰,頭發(fā)凌亂,言語倒是還善,臉上表現(xiàn)出幾分與泥土很協(xié)調(diào)的笑容。
他問:“是燒香還是拜佛?”
我不想搭理他,只是喏喏:“隨便轉(zhuǎn)轉(zhuǎn)。”
我立馬捕捉到他臉上的九分失望,還有一分憤懣。
我直面大佛,用手機(jī)為佛存念時(shí),他立馬進(jìn)行講解。他很懂得搶抓商機(jī),說:“大佛建成已經(jīng)20多年了,高36.6米,因?yàn)槟呖唛_鑿始于公元366年。還有呢,這佛是金身,光使用金箔就花費(fèi)了140多萬呢。”
我說:“我來過很多次了,你不用講解了。”
他彎腰看看車牌,知道是七里鎮(zhèn)人,這才換過一種表情,待見于我,說:“你們是七里鎮(zhèn)的?”
我點(diǎn)點(diǎn)頭,說:“聽口音你不是本地人,來自哪里,皈依了么?”
他說:“我家也在七里鎮(zhèn),在武威廟村,是移民過來的,都30多年了。”
我說:“你比我還敦煌。你原先在武威哪里?”
他說:“在古浪。就是去蘭州要翻越的最高山峰烏鞘嶺那里,家就在烏鞘嶺最頂端。”
他豎起一根手指,往天空上戳,似乎能戳住他曾經(jīng)的家。他說:“沒水,沒法活,投親靠友,來敦煌了。”
我說:“你是居士?”
他說:“不是。姐姐是,姐姐在這寺里4年了,和姐夫兩個(gè)人。姐夫回去了,我來陪陪她。”
我說:“哦。我是來找老子的,記得你們寺里邊,有老子的介紹,我進(jìn)寺里去看看。”
有了交流,他似乎爽快了一些,指引我們進(jìn)廟。廟叫“南山寺”,與大佛正對一條中軸線。寺外一堵朱紅色圍墻,墻上有碩大的黃色的隸書大字:
梵界凈土
南山寶寺
這時(shí),這個(gè)中年男人的姐姐現(xiàn)身了,攏著團(tuán)花圖案的短襖,頭上罩著一條藍(lán)色毛巾,快人快語,也善言善語,趕緊招呼,叫我們進(jìn)去。得,一進(jìn)去就看見釋迦牟尼佛正襟危坐,滿臉莊嚴(yán)。磕頭是必要的,燃香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我誤將幾十塊零錢塞進(jìn)了功德箱。當(dāng)我點(diǎn)燃香后,老人依然善言善語提醒道:“放點(diǎn)香火錢。”
我說:“零錢全都放進(jìn)箱子里,不一樣嗎?”
中年男人趕緊補(bǔ)充道:“香火錢是香火錢,我們收的,放進(jìn)功德箱就跟我們無關(guān),是公司老板的。我們打不開,你看,兩把鎖,得兩把鑰匙打開。”
我恍然大悟,趕緊對后到的俠女說:“香火錢別放進(jìn)功德箱啊。”
我看見那姐弟,不好意思地笑開了。那笑,也似乎坦蕩。
以前我真不拜佛,也不燒香。我自認(rèn)為我能主宰自己的命運(yùn)。但現(xiàn)在,不了,也許時(shí)間這把殺豬刀真能改變很多堅(jiān)硬如鐵的東西。比如思想。比如認(rèn)真。還比如自己的頭發(fā),皺紋,腰身和骨頭。在時(shí)間面前,人沒有一棵樹有韌性,也沒有一顆石子那么頑強(qiáng)。人的脆弱,不堪一擊。在時(shí)間里,我們都是過往的塵灰。
老人招呼我們進(jìn)她的屋子。那份真誠和熱情無法拒絕。
寺廟旁側(cè)一個(gè)側(cè)院兒。院子很小。一個(gè)尺子拐,正面是兩間房屋,側(cè)邊是一間。我們進(jìn)了大的一間,剛一掀門簾,一股很溫暖的氣流夾雜著一股食物的餿氣撲面而來。我穩(wěn)了穩(wěn)嗅覺,遲疑了片刻,才抬腿進(jìn)去。屋子里一只爐子正紅亮亮地閃爍著煤炭被燃燒后的熱能。一張三斗桌,桌面上一塊菜板,菜板上有新切的紅蘿卜和青椒丁,估計(jì)正準(zhǔn)備做一頓面條的雜醬。桌子上還立放著一臺(tái)不到20寸的平板電視,用鑲有花邊的紗布罩著。一張低矮的小餐桌,上面擠滿瓶瓶罐罐,油鹽醬醋。
我們的交談一直很溫暖。
得知她姓俞。她的口音重,我問了幾次,她說出一個(gè)名字。我哦了一聲。她說皈依佛門30多年,不識(shí)字,卻背得《大悲咒》《波羅蜜多心經(jīng)》《彌陀經(jīng)》《凈土文》等。問她不識(shí)字是如何念誦的。她說聽師父朗誦,照著學(xué),天長日久也就會(huì)了。我叫她背誦一下《心經(jīng)》,這經(jīng)書我是非常熟悉的。她雙手合十,口吐蓮花,噼噼啪啪,滾瓜溜熟。
俞居士說,每天要背誦一遍經(jīng),這是功課,還有三萬句“南無阿彌陀佛”。
她十分有成就感,面相慈祥,安靜,笑容如花,這些都是佛滋養(yǎng)出來的。問她年紀(jì),她自豪地說,都七十有一了。再問家人,她說孩子四個(gè),一男三女,都在敦煌城做生意,大的孫子都18歲了。滿是心無掛礙的閑散和自在滿足。
我說:“你在這里一個(gè)人,待得住么?”
俞居士說:“待得住,老伴待不住,下山去了。”
我說:“莊稼還種么?”
俞居士說:“早就不種莊稼了。之前種棉花,現(xiàn)在棉花也不種了,沒收入。”
我說:“土地呢,沒流轉(zhuǎn)出去租給別人種么?”
俞居士說:“誰種啊,誰都沒種呢,誰都不種了,嘿嘿。”
我說:“撂荒了。”
俞居士說:“撂荒了。”
其實(shí),我的心深深地被刺痛了。天地開洪荒以來,大地給人類呈現(xiàn)的就是糧食、瓜果和蔬菜。這些糧食、瓜果和蔬菜,是人類生存繁衍必需的生活元素。而且,作為農(nóng)民,他們代代以來把土地視為命根子,寧愿斷子絕孫也不愿喪失對土地的擁有。多少王朝刀槍劍戟血雨腥風(fēng),最主要的就是爭土地奪地盤。可是現(xiàn)在,農(nóng)民們對土地的表情是如此地輕描淡寫和不以為然,甚至不屑一顧。我知道他們這種對血液基因的改變不僅僅是城市化商業(yè)化的誘惑,讓他們做出徹底改變的是多種因素。也許最重要的一條是,播下的是種子,收獲的是失望。
對俞居士這樣逐水而生的移民來說,他們對土地對耕種的感情應(yīng)該高過對《心經(jīng)》的依賴。然后,他們還是決絕而愉快地做出了舍棄。
俞居士的弟弟在身后補(bǔ)充了一句,說:“他們兩個(gè)人都有工資,一個(gè)月1500,兩個(gè)人3000,加上香火錢,還不比種田地強(qiáng)多了啊。”
我沒有回應(yīng)他。這不是一個(gè)多么復(fù)雜的計(jì)算和對比。我是想這是一個(gè)隱喻,我不能再解釋什么。再解釋就多余了,因?yàn)槲覀兠總€(gè)人的生命都只是區(qū)區(qū)幾十年,誰能預(yù)見未來之來呢。也許,未來的生命體真不需要糧食和蔬菜,只要充電就足夠了。
我走出小院兒,回到正院兒,尋找關(guān)于老子的解釋。
我要找尋老子。
很多人都確信,老子騎著青牛一路西來,最后到了三危山,并在此坐化入仙的。
我們都知道,老子過函谷關(guān),被關(guān)令尹喜擋著道。
先看看這個(gè)尹喜。這個(gè)周朝的天水人也非常人,有這樣記載:關(guān)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nèi)學(xué)星宿,服精華,隱德仁行,時(shí)人莫知。老子西游,先見紫氣東來,知真人當(dāng)過,后回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
也就是說,學(xué)富千車的老子都知道學(xué)富百車的尹喜也不可小視。
尹喜官拜周朝大夫,看不慣王朝衰敗,別官而去,做了函谷關(guān)的小關(guān)令。
他為何獨(dú)獨(dú)要做一個(gè)小關(guān)令呢,因?yàn)樗蠚鈻|來,掐算必有大人物過關(guān),于是他在這里邂逅了老子。這是一次奠定歷史高峰的驚鴻一遇。
可以說,尹喜擋道,為中華文明堵住了一座道德高山,截住了一條思想的巨河。倆人惺惺相惜,坐在長滿青草的山坡歌以詠志,而面對朝廷衰敗又報(bào)國無門,滿腹才華,也只能是滿腹牢騷。
哀怨之處,尹喜說,老師您干脆將想要說的話寫下來吧,我給您存著,留給后人。
老子想想,也是,寫就寫吧。于是狼毫小楷,上下兩章,五千字,擲筆于地,大笑幾聲,望西而去,再無所終。
對尹喜的功勞,歷史上有如下兩句為證:
華章九篇入《百子》
經(jīng)文五千頌《道德》
這就足夠了。尹喜功莫大焉,老子很偉大,老子的偉大之所在,更在于尹喜的智慧。要不是他,中國的孔子拜師將無門,中國的莊子學(xué)之將無師,中國的哲學(xué)還迷失于蒙昧的歷史長河。也有人說,自老子的《道德經(jīng)》始,中國才躋身世界思想的高峰。似乎怎么歌頌老子都不為過。
他配。
關(guān)于老子,生是傳奇,死也是傳奇。
據(jù)說,老子是彭祖的后裔,在商朝陽甲年,公神化氣,老子寄胎于玄妙王之女理氏腹中,胎孕81年才出生。一生下這孩子就白眉白發(fā)白胡子。因此,他母親給取名叫“老子”,意思是一生下來就老了。是啊,都81歲了,怎么會(huì)不老呢。現(xiàn)在的人的壽命能匹敵他在娘胎里的時(shí)間就很不容易了。
其實(shí)他的父親彭祖,也是一個(gè)神傳人物。據(jù)說是上古五帝中顓頊的玄孫。他經(jīng)歷了堯舜、夏商諸朝,到殷商末紂王時(shí),已767歲,相傳他活了800多歲,是世上最懂養(yǎng)生之道、活得最長的人。對,他就是最早的養(yǎng)生專家,其在世之久,令他之后的人類鞭長莫及。
關(guān)于老子的死,有人說也是坐化升仙。
這很符合老子的思想,也符合現(xiàn)代科學(xué)對生命的解釋,人都是一股氣,來時(shí)聚,去世散。我們看不見這股氣,但可以看見火葬場高煙囪上的那股裊裊青煙,那股青煙是否就是所謂的“氣”呢。也許是。
有這樣一段傳說,因?yàn)閷?shí)在太久遠(yuǎn),太玄幻,所以縹緲,只能歸為傳說。
傳說是這樣的:這個(gè)姓李名聃的老子很長壽,101歲仙逝。加上娘胎里的81歲,就有182歲。死了,鄰里皆來吊唁。老人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念老子順民之性、隨民之情、與世無爭、柔慈待人的大德大恩,皆悲不自抑。念他的好,念他的恩德,悲戚戚,不忍失去。這時(shí)老聃好友秦佚來了,居然不跪不拜,拱手致意,哭號(hào)三聲即止。轉(zhuǎn)身欲去時(shí),鄰人攔住了他。
問:“你是老子好友嗎?”
秦佚說:“當(dāng)然。”
鄰人說:“你既為老子好友,怎么如此薄情少禮,怎么能夠這樣呢。”
秦佚卻說:“有何不可?”
鄰人憤怒了,大聲責(zé)問道:“你其理何在?”
秦佚笑著說:“老聃早有言在先,生亦不喜,死亦不悲,你們聽說過嗎?”
眾人無言。
秦佚又道:“還有,老聃出生時(shí),是由無至有,聚氣而成,順時(shí)而來,合自然之理,這值得高興嗎?”
又道:“今日老聃去了,由有歸無,散氣而滅,順時(shí)而去,也符合自然之理,值得悲傷嗎?”
秦佚最后說:“生而喜者,是以為不當(dāng)喜而喜也;死而悲者,是以為不當(dāng)悲而悲也。這是背自然違天理,不合符道的。既然不合于道,還算得上老聃好友嗎?既然是老聃好友,就要遵其言而動(dòng)、順于道而行。”
又說:“我既為老聃之友,故能以理化情,故不悲。”
一番“道論”,讓老子的鄰居啞口無言。
由此,我也想到莫高窟有一尊佛的涅槃圖,佛涅槃了,他的眾弟子表情各異,有的悲切,有的沉默,有的嚎啕,有的微笑。當(dāng)然,解釋是這樣的,只有哭相的弟子是沒有得道的,還是最初級(jí)階段的,而那些表情如常甚至微笑的弟子,才是參悟透了生死的高徒。這個(gè)跟秦佚的“道論”異曲同工。
老子的“道”,指的是宇宙本體,萬物根源,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不可言說的,不能明釋的,只可意會(huì)不能言傳。正所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在此,我并不想陷入對于“道”的求解之中。我想求證的是,老子是否真實(shí)坐化于三危。
從一些典籍里也可查證到蛛絲馬跡。比如在《道藏·尹喜傳》《水經(jīng)注》等書中可以看出,老子西行主要活動(dòng)在渭河中上游一帶,除了伯陽柏林觀、講經(jīng)臺(tái)等地之外,他們還去過秦州區(qū)的老君臺(tái)、玉泉觀、崆峒山、敦煌等地。
對,有敦煌二字,這很重要。雖然大多數(shù)論證依然是:
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shí),莫知其所終。
我在大院兒里看見門背后有一塊牌子,有這樣的文字記錄:
甘肅省社會(huì)科學(xué)聯(lián)合會(huì)前副主席,副研究員、學(xué)者王顯鳳老先生專門研究老子30多年,多次去過老子誕生地和函谷關(guān),甘肅臨洮和敦煌三危山實(shí)地考證,對老子西行等諸多問題有了自己獨(dú)特的見解,并大膽認(rèn)定老子西行終點(diǎn)站是敦煌,仙逝地也是三危山。
因?yàn)橥趵舷壬_認(rèn)老子西行的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春秋末年,中原戰(zhàn)火頻繁,日益劇烈,老子辭官回鄉(xiāng),講學(xué)傳道,失去了必要的社會(huì)安定環(huán)境。
其二,老子想親身會(huì)見釋迦牟尼,但到敦煌時(shí),年事已高,體力不支,青牛已疲,時(shí)距天竺遙遠(yuǎn),心有余但力不足了。
其三,老子發(fā)現(xiàn)三危山是個(gè)理想的好地方,既無草木走獸,也無人煙,僻靜異常,安全無比。
認(rèn)定仙逝于三危山證據(jù)確鑿:
證據(jù)一:先有老君堂,后有莫高窟。老君堂的道人在山上發(fā)現(xiàn)的漢磚,證明老君堂在魏晉之前早已有之。北魏和尚在山上所看見的佛光,實(shí)為老君堂發(fā)出的紫氣。這種紫氣,同函谷關(guān)令伊喜看到的那種,伴隨老子西行而“紫氣東來”的情景是一樣的。
證據(jù)二:關(guān)于老君堂的演變,可能經(jīng)過三個(gè)階段。先秦時(shí)期,弟子們?yōu)橄墒庞诖说氐睦献樱钇鸩菖铮宰骷漓腱`堂。西漢初年,推崇黃老之學(xué),遂正式興建磚木結(jié)構(gòu)的老子紀(jì)念堂。唐宋時(shí)期,唐皇武后,封老子為太上老君,遂又重建,并改名為老君堂,以至于今。老君堂,不被命名為某某道觀,又正是一個(gè)物證,證明老君堂就是老子廟。
還有證據(jù)三、證據(jù)四、證據(jù)五,我覺得都比較扯淡,就不羅列了。
但不管怎么說,我覺得老子也是終老在三危山的。
要問原因,那就是我希望我和老子很近。這個(gè)理由,超過一萬個(gè)推測。
對于這樣的論證,我寧愿選擇相信。因?yàn)椋U谖业哪_下,三危正在我的心中。我不知道為什么一個(gè)“佛”的寺廟里卻理直氣壯地懸掛著關(guān)于“道”的追問。看來,佛和道,都是溫柔的,善良的,不唯我獨(dú)尊,也不排斥異己。彼此都是行德勸善,又何須有我無你,有你無他呢。
我仿佛聽到聲音——
佛說,我慈悲為懷。
道說,我無為,我逍遙,我自在。
站在寺門,往前看,是金光閃閃的觀音大佛,四面的山像巨掌一般半握,或者更像是一朵盛開的蓮。那些山峰就是蓮花瓣。觀音就站立在如蓮的手心中,一站就是20年。我再回過頭去,看見寺廟大門柱上的對聯(lián),我想到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
金身觀自在果修羅漢悟三乘
寶相現(xiàn)如來回證菩提空五蘊(yùn)
出了南山寺,就看見了半山腰的老君堂。
老君堂似乎早就等在那里,并看見我在南山寺里逗留。但我深知,老子不會(huì)為怪,因?yàn)樗抢献樱@就是足夠的理由。
去老君堂,得從觀音旁側(cè)的小道而進(jìn)。
記得夏天,我和一位朋友相約來過三危山。那次來得就比較晚,遠(yuǎn)見夕陽西下了,我們才從七里鎮(zhèn)出發(fā)。敦煌的夏天太陽遲遲不下山,似乎格外留戀佳期遲到的戀人。眼見晚上10點(diǎn)了,天還是亮堂著的,內(nèi)地人來了很不習(xí)慣,老是抬頭看天,以為天出了問題。其實(shí),沙漠里夏夜才是充滿情趣的。你只有跟沙漠里的夏夜緊密相融,才會(huì)發(fā)現(xiàn)那份美麗。哪怕我的文字再充滿魅力,都會(huì)大打折扣。
朋友是從內(nèi)地來的,準(zhǔn)確點(diǎn)說是從長江南岸來的。她奔敦煌而來,也奔我而來。我默默地像一株駱駝刺般生長在沙漠里,可是總有外邊的人慕名而來。這不是夸耀,這點(diǎn)夸耀不能讓我生出一點(diǎn)光輝。安靜地生長,那才是偉大的力量。
我往往被迫破戒安靜。
這個(gè)朋友會(huì)寫詩,愛攝影,更愛獨(dú)自行走。這些要素?cái)n于一個(gè)年輕女子是非常要命的。我的想法一直就是,人不要愛好太多,哪怕對待事物,也就那么一兩種足矣,更何況這些是支撐自己生命的元素呢。
我不太好直言,但我禮貌地接待了她,并像一個(gè)老朋友似的,跟她上了鳴沙山,去了陽關(guān)玉門關(guān),還有魔鬼城。這是敦煌主要的幾個(gè)景點(diǎn),再無他趣。但她是熱烈的,面對所有的大漠風(fēng)景,一粒沙,一棵胡楊,一座城池。當(dāng)然還有我。這有點(diǎn)要命。
她說:“你真幸福,在這樣的地方生長,本身就像詩歌一樣。”
我嘿嘿兩聲,無言以對。因?yàn)榇蠖鄶?shù)詩歌是用悲情和眼淚譜寫的。
驅(qū)車上山。一上山,就領(lǐng)略了三危山的氣度。沙漠里白天酷熱,晨昏陰涼。假若思想和肉體足夠敏感,就能感覺到三危內(nèi)在的氣場,博大而深厚。那種能量所散發(fā)出的氣息,在三危的天空形成了一個(gè)氣罩,外在的地理的物理的意念的紛擾很難對沖這種能量和氣場。這種能量和氣場,是三危的本體,是三危的魂魄,是三危思想光芒。這種東西,可意會(huì)不可言傳。它存在,它就在那里;但你看不見,摸不著。
但它確實(shí)存在。
在三危之外,我們是三危的附著物。在三危之里,我們又成了大山的一部分。但分明,我們或者我,已經(jīng)深刻地融入了這座大山,這個(gè)氣場,這個(gè)道場。我能感覺到,三危的氣息緊緊裹挾了我。
我給朋友說我的感覺,她笑笑。她的笑意味深長。
也許,她還在三危之外,或者感知并不明確。
山有山的氣場,水有水的氣場。山水的氣場構(gòu)成大自然的氣場,而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所以人不要硬性地抵抗或者反抗自然,或者改造自然,那是很可笑的思維和行動(dòng)。天人合一,自然而然,和諧共生和相互依存,這才是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人與大山大河的關(guān)系。說白了,也是自己與自己內(nèi)在的關(guān)系。
但,很久以來,我們都違背了這種關(guān)系。
現(xiàn)在,人們正在復(fù)蘇,正在覺醒,正在試圖重新打量這種關(guān)系。
這是一個(gè)很好的開端。也但愿這種開端會(huì)締結(jié)一個(gè)良好的果。
果是對因的回應(yīng)和照見。
前幾天,辦公室的樊兄說了兩件事,令我思考。
之一:他說他有一個(gè)四川朋友,資產(chǎn)豐厚,可以花費(fèi)四五百萬去德國學(xué)琴,因此小提琴拉得已有相當(dāng)級(jí)別。但他還有一愛好,就是拉弓射箭。他專門射殺野地里的牛,以此取樂。突然間,得了怪病,萬藥難救,生死不得,到幾乎要自殺的地步。樊支招,去問問佛。此朋友轉(zhuǎn)身去問佛,佛說你作惡太多,要想活命,就如何如何云云。此人也果真立地成佛,每天抄寫一遍《心經(jīng)》雷打不動(dòng),惡疾竟然不治而愈。
之二:說某某辦公室人員突然暴斃,暴斃不得,偏癱,失去了語言和行走功能;又一同事,暴斃不得,也偏癱,語言還在,行走不得。終究其因,乃執(zhí)念太深,恨太深,自己找不到氣孔,最后自己將自己撐爆了。
色就是空。萬物皆存在,又萬物皆空。
人只是現(xiàn)實(shí)大地的一次行走,比如敦煌大地,從有漢文字記載以來,在這片大地上走過了三苗人,走過了烏孫人,走過了匈奴和突厥人,我們都看不見他們的背影了,但他們確實(shí)走過。我們呢,也必須將這樣“走過”,連一個(gè)背影也不會(huì)存在,最后只能以一個(gè)名詞出現(xiàn),那就是“華夏人”。我們將在歷史長河中隱退掉姓氏,隱退掉姓名,隱退掉性別,至于思想和想法,成功和失敗,那將是很可笑的附著物,連一粒塵埃都算不上。
在天地之間,色就是空,空就是色。
執(zhí)念于一人一物一事,都是自找麻煩和嚴(yán)重?zé)o趣。
這當(dāng)然是很高級(jí)別的認(rèn)知。這不是每個(gè)人都能認(rèn)知的。有些執(zhí)念太深的人,就是魚死網(wǎng)破也認(rèn)知不到。
認(rèn)知,決定萬事萬物的狀態(tài)。
于是,我想到了三危山中的老子。想到老子所建立的宏闊的思想道場。
老君堂坐臥在三危山的中部。
從觀音大佛像后邊的公路就望得見老君堂高高在上。但他還不是三危山的最高峰。最高峰還在它的身后,視野里最遠(yuǎn)的突兀處,才是三危的頂點(diǎn)。但三危的萬丈光芒并不在三危山的頂點(diǎn),這有可能跟老子的哲學(xué)思想同出一轍,且我逍遙看萬事,何必爭當(dāng)獨(dú)光芒啊。所以說,老君堂的至高處不在高,而在于奇妙。
這一點(diǎn),是我多次在老君堂門前幾千年的城磚上坐臥呆思之后獲得的。
從老君堂的角度展開視覺,我分明看見中山環(huán)繞處,宛若一朵蓮花盛開。四周的山峰做了花瓣。而花蕊之處,老子的道場并沒有獨(dú)占,而是讓給了那座現(xiàn)代版的金身大佛。大佛做了花蕊的花柱。老子從來不會(huì)將美好的東西占為己有,他也從來不占。天地萬物都在他的眼下,都在他的“道”里,萬變不離其道。這才是高妙之所在。
雄視四野,萬峰蒼莽。天宇之下,三危巍然。
很多年前的斯時(shí)斯刻,老君曾在此與西天佛祖坐而論道。他們講述的是宏闊的大道,是為人類開辟思想的疆場,為人類乃至萬物生長尋找根據(jù),甚至為國家的治理建立規(guī)則和準(zhǔn)繩。他們相談甚歡。兩顆智慧的頭顱產(chǎn)生了核爆,那思想的火花照耀了三危的群峰,照耀了西部的天空,也照耀了人類的天空。
那是人類開蒙的洪鐘大呂。
那智慧的能量綿延千年,三千年,乃至后續(xù)萬年。
眼下的老君堂獨(dú)倚在半山腰,精致,小巧。當(dāng)然我們并不得見漢代的老君堂,唐宋的老君堂,清朝的老君堂。每一個(gè)時(shí)期,老君堂都有自己獨(dú)到的模樣和氣質(zhì)。我們見到的僅是在不久的幾十年之前或者百年之前被巨大的無神論者蕩平之后,在上世紀(jì)80年代重新修建的老君堂。也聽說,在蕩平之前的老君堂,香火旺盛。可以想象,老子從西漢以來的面相早已灰飛煙滅,而此時(shí)此刻端坐在廟堂之內(nèi)的老子,我總覺得太新,太艷,也太人間煙火氣。
在老子的眉目間,我真看不出乾坤大氣。
當(dāng)然,看不見是必然的。我們將太多的東西進(jìn)行了切割,最終剩下的是一無所有。
孤小的廟宇,坐東向西,紫氣是否繼續(xù)東來,我無力感知。
面向西天,那是中華民族根魂所系的方向。西天有極樂,西天有真經(jīng)。這也是中華民族老祖宗們行走的軌跡,由西而東,當(dāng)游牧的或者農(nóng)耕的腳步抵達(dá)海邊的時(shí)候,他們停下了前行的腳步,海岸線,成了一道天塹,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紅線,于是,一個(gè)民族抑制住了龐大的慣性,踩住剎車,在長江黃河流域,在能生長稻黍的土地上,耕種生息。但他們魂魄里總有一種聲音在呼喚,從西天而來。
于是,向西,成了一個(gè)民族的精神窗口。
玄奘等一大批虔誠的精神斗士,九死一生向西天取經(jīng)。
張騫鑿空西域,目的和方向都是向西。
霍去病等一大批將士的長矛,所指向西。
唐詩將邊塞的邊界拓展之處,也是向西。
還有史書里很多的逃亡,也是向西尋找茍且和安詳。
可見,西向,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倉儲(chǔ)和安魂溫床。大海的濤聲阻擋了一個(gè)民族太多的想象。當(dāng)宋朝的兒皇帝從崖山一跳,漢民族已經(jīng)魂歸大海。所以,大海是漢民族心中一道悲痛的閃電,欲說還休。當(dāng)一個(gè)偉大詩人發(fā)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吶喊后,很多人開始重新審視埋葬了自己根脈的大海,并看見了大洋的彼岸。隨之,一個(gè)民族開始齊聲吶喊“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雖然濤聲依舊,但都止步于岸。
頭枕西天,是中華民族的慣性。
千年前的絲綢之路,是文化慣性和經(jīng)濟(jì)慣性的必然。
“一帶一路”,是新的西顧。在慣性里,也注入了不一樣的倔強(qiáng)。
千年之前的老子在三危坐而論道的時(shí)候,估計(jì)早看透了這一切,萬物生長百花開,那都在他的掐算之內(nèi)。我看見老君堂左右的聯(lián)語:
混沌初開道在先天之上
乾坤既定人居太極之中
我推開廟門,木門嘲哳,落下一些流沙。
顯然香火不盛。香爐依在,香也在。還有打火機(jī)。我必須燃香一炷以示尊敬。這是中華民族最內(nèi)在最本質(zhì)的精神之源。誰若無視,那將是誰的短視。誰若視而不見,那將是故意遮蔽自己思想的根脈,截?cái)嘧约旱难芎土飨颉N也荒堋?/p>
當(dāng)香煙繚繞,我抬眼看見老子,老子也笑著看見了我。
猛然一頓。我發(fā)覺鶴發(fā)童顏的老子,很具體的表情給人以親近感。他旁邊還有釋迦牟尼和孔子的塑像。他們都是同一時(shí)代的星辰,離開他們,人類依然混沌,世界初元未開。他們共同為人類指點(diǎn)迷津和認(rèn)知世界的方法途徑。他們神性的義務(wù)和擔(dān)承,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千年之后今人的理解。即便千年之后,我們在熟練地掌握了科學(xué)指導(dǎo)下的蒸汽機(jī)和互聯(lián)網(wǎng)之后,我們依然是他們的學(xué)生。我們依然在他們宛若汪洋的思想大海里,笨拙地狗刨。
當(dāng)然,我也驚嘆距今不遠(yuǎn)的構(gòu)思者,他們大膽而又科學(xué),將人類三座大山并列在此,旨意明確,寓意深刻,余味深長。儒、釋、道,乃中華民族的內(nèi)心歸向,也是漢文化最主要的精神骨骼和行走拐杖。在傳統(tǒng)的和樸素的意識(shí)里,儒釋道是最契合以農(nóng)耕傳家這個(gè)民族的精神脈搏。且三教和諧共生,相互滋長,互為光輝。這是很難得的。
老君堂附近還有一古塔遺址,塔原名為慈氏塔,據(jù)考證為宋代所建,為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古塔之一,1981年已搬遷至莫高窟保存。
老君堂東邊的山頂,高高聳立著一間青磚古屋,這就是渾元古洞,據(jù)說是道家祖師打坐練功,朝拜天地的地方。北坡后的小山頭上還有幾座泥塔,飽經(jīng)滄桑,與老君堂相依相伴。老君堂附近還曾出土了漢代天馬磚、龍鳳磚等珍貴文物,現(xiàn)存市博物館和莫高窟陳列中心。由此可以推演在西漢時(shí),三危山已經(jīng)修建了很多寺廟,香火裊裊,歷史悠久。
也可以說自西漢以來,也就是張騫鑿空西域之后,漢文化從東往西而來,西方的佛文化自西向東而去,當(dāng)敦煌還沒有大而盛的時(shí)候,三危山這個(gè)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diǎn),代替敦煌做了宗教的和藝術(shù)的道場。這是肯定的。
假若還需要求證,那就是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莫高窟洞窟文化的開創(chuàng)者樂僔和尚,行游西天至三危,在三危山上看見對岸佛光萬丈,因而靈光閃現(xiàn),掘洞為窟,以佛為魂,開始了宕泉河岸一千多年的宛若繁花。那是偶然,也是必然。
老子是公元前570年生人。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是華夏奴隸制興盛的終點(diǎn),也正是封建社會(huì)發(fā)軔的起點(diǎn)。那時(shí)候農(nóng)耕文明已經(jīng)相當(dāng)成熟,鐵器被廣泛使用,對土地的改革正在被一些城邦國家拿上桌面。對生產(chǎn)資料的再分配將激發(fā)生產(chǎn)力的迅猛推進(jìn)。生產(chǎn)力的快速推進(jìn)將激發(fā)人類思想大解放,文化大探索,宗教大聯(lián)歡。
所以,中國的本土宗教儒和道,與西來的釋迦牟尼友好握手,再經(jīng)過多年的融合演化,儒釋道親密如一家,成為中華民族內(nèi)在最親切的情感密碼。自老子、孔子和釋迦牟尼之后,歷經(jīng)數(shù)百年的演繹,佛教開始在東方的土地上盛如蓮開。當(dāng)樂僔云游到三危的時(shí)候,他先拜謁了三危山中的老子。不,那時(shí)候老子早已化作紫氣升天,留下的只有這座老君堂。
老君堂雖然孤小,但它罡氣滿身,自主乾坤。
樂僔對老子跪拜之后,坐在堂前的石凳上,攏了攏滿是補(bǔ)丁的佛袍,捏了捏打了血泡的雙腳,讓三危清涼的風(fēng)吸干額上的汗滴,歇息之間打量著三危之雄奇。斯時(shí),他有很多想法,雖然他西去取經(jīng)志堅(jiān)如鐵。他感覺到了三危的能量和某種不可逆轉(zhuǎn)的引力正在作用于他。也許,關(guān)于三危,關(guān)于敦煌,一個(gè)新時(shí)代正在怦然而至。
突然之間,他看見了三危群峰,夕陽西下幾時(shí)回之際,佛光萬丈。
這正是樂僔尋找的佛光盛景。于是,他目光一沉,看見了三危對岸流沙崖畔。
大道原非秘只因本性迷
本來無掛礙何須苦尋覓
這一照見,敦煌在樂僔的目光里便熠熠生輝。
這一照見,敦煌向世界露出了佛的容顏。
這一照見,兩千多年來西部的流沙輝映出了人類思想的金光。
時(shí)至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大膽而奢侈地展開聯(lián)想,就那一瞬間,樂僔內(nèi)心如大海般的澎湃和巨浪般的呼嘯,是多么令人激越。雖然,歷史拒絕過度的解讀和場景化再現(xiàn),但每一次上到三危,盤坐于老君堂前的青磚之上時(shí),我都不能抑制自己已經(jīng)被嚴(yán)重抑制的人間情感。遐想和抒情,是我此時(shí)此刻最佳的容顏。
假若將時(shí)間和空間這樣的條塊拆解掉,時(shí)間對折,空間重疊,我愿意神清目秀地看著老子,也欣慰地看著樂僔。我會(huì)暴以長歌,那種我無法想象的長調(diào),為人類里如同老子、孔子、釋迦牟尼,還有樂僔們,致以虔誠和祝福。除此之外,我拒絕其他表情。我的表情只順應(yīng)歷史里的那些光明的東西,透徹的東西。光明不是光芒,光芒往往是智性的麻痹和屏障,我會(huì)對過于光芒的東西緊閉雙眼。
在三危山上,老子、孔子、釋迦牟尼,還有樂僔,他們是最透徹通達(dá)的靈魂。他們值得我三叩九揖,五體投地。但在公元2018年的夏天,距離他們兩千多年之后的此時(shí)此刻,我這個(gè)臟污的漢人,膝蓋已經(jīng)生銹,已經(jīng)對圣賢失去彎折的記憶了。我努力地,努力地想折下我的膝蓋,居然已經(jīng)做不到彎折。
我的淚水長流啊,淚水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