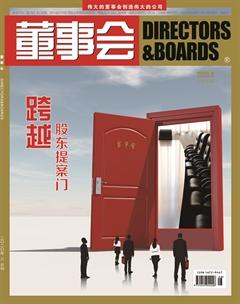識別“重大性”遠離刑事風險
張睿開 吳勁松
信息披露工作日益重要。今年3月新《證券法》實施,大幅提高了資本市場違法犯罪成本。6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三條法律條文與信息披露有關,提高了量刑標準、細化了犯罪情形。7月,證監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修訂稿)》(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沿用了“違反本辦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
《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與上市公司息息相關。“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企業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或者對依法應當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規定披露,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犯罪主體,最高刑期10年。《刑法》多次提到“重要”。遠離證券刑事風險,在信息披露中識別“重大性”成為關鍵所在。重大性包括三個層次:1.重大事實,指既存的可以影響證券價格的客觀事實;2.重大變化,指既存事實、狀況所發生的可以影響證券價格的重大改變;3.重大信息,是包括重大事實、重大變化在內的可以影響證券價格的重要情況。

我國立法中的重大性標準采取了“兩元”標準,即對于不同的信息披露階段采用不同的信息披露標準。在證券發行階段,證監會要求“凡是對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均應在招股說明書中披露”,此處突出了“投資者決策標準”。典型體現在《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1號——招股說明書》,規定“本準則的規定是對招股說明書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論本準則是否有明確規定,凡對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均應披露”。按照“投資者決策標準”,法律要求一律從理性投資者的角度出發來考慮重大性,如果一項信息對于投資者的決策確有重要意義,那么該信息就是重大的。
對于上市公司的持續性信息披露義務,立法以“證券價格標準”作為判斷“重大性”的主要標準,同時詳細列舉了屬于重大性事項的各種情形。新《證券法》將“信息披露”作為獨立一章,“重大事件”體現在第八十條和八十一條。《證券法》第八十條要求披露對股票交易價格有影響的信息為“發生可能對上市公司、股票在國務院批準的其他全國性證券交易場所交易的公司的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投資者尚未得知時,公司應當立即將有關該重大事件的情況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證券交易場所報送臨時報告,并予公告,說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狀態和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并列舉了11種主要情形;第八十一條要求披露對公司債券交易價格有影響的信息與之類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修訂稿)》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細化和延伸,分別規定了21種情形和21+8種情形。
我國關于“重大性”的規定,采用概括式和列舉式的立法方式,賦予了證監會補充認定重大信息的權力,但這種權力的行使沒有明確的指引,導致認定的任意性大。我們認為,信息披露中的“重大性”應以“投資者決策標準”為原則,而“證券價格標準”是判斷“投資決策標準”的輔助和參考因素。除了立法上所作的具體列舉外,應當參考會計準則和獨立審計準則的相關“重要性”標準,對信息披露的要求作出具體的判斷。如審計實務中常用來判斷重要性水平的一些參考數值:稅前凈利潤的5%-10%(凈利潤較小時用10%,較大時用5%);資產總額的0.5%-1%;凈資產的1%;營業收入的0.5%-1%,在信息披露規則中未予明確的情況可以作為輔助的判斷標準。關于無法量化的“重大性”,主要依據上市公司董事會自身作出的定性判斷,如關于《證券法》第八十條第六款“公司生產經營的外部條件發生的重大變化”,一旦公司作出了這種判斷,并有意無意通過公司官網、微信公眾號、接受媒體采訪等形式為公眾所知曉,則必須履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
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證監會向公安機關移送財務造假涉嫌犯罪案件6起。當前,立法司法行政機關重拳打擊證券犯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要求上市公司制定信息披露事務管理制度,該制度應當包括信息披露事務管理部門及其負責人在信息披露中的職責。“信息披露義務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管應認真研讀《刑法》《證券法》有關條文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修訂稿)》,加強信息披露警示教育,董事長、總經理、董事會秘書、財務負責人以及信息披露事務管理部門(董事會辦公室、證券事務部等)應充分認識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履職風險,依法合規、勤勉開展業務,遠離證券刑事風險。其中,董秘負責組織和協調公司信息披露事務,更應該做信息披露事務的專家,并在具體工作中從嚴要求,如履薄冰盡心盡責:這既是對公司、董監高等信息披露義務人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