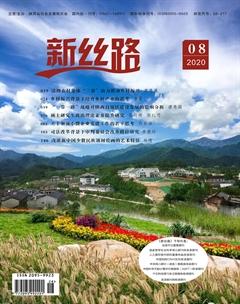論“三美論”在唐詩英譯中的先進性和局限性
劉錚
摘 要:唐代是我國詩歌發展的鼎盛時期,在該時期涌現出的詩作名篇無疑是我國寶貴的文學遺產,傳承和發揚唐詩的意蘊亦是我國譯者的不懈追求。許淵沖先生作為我國格律詩體派代表人物,他提出的“三美論”為中國古典詩歌英譯提供了規范化的理論支持和鑒賞尺度。本文以許淵沖先生英譯本為實例,分析“三美論”在其唐詩英譯中的指導作用,并對該理論局限之處試探性地提出修正意見。
關鍵詞:三美論;唐詩英譯;許淵沖
一、許淵沖“三美論”的繼承和發展
“三美論”的雛形源于魯迅對于漢語特點的理解,他在《自文字至文章》中提到:“誦習一字,當識形音義三: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許淵沖先生基于多年的翻譯實踐經驗,并融合了自身對翻譯的理解,將魯迅先生這一文學理論發展為翻譯理論。他在《文學與翻譯》中寫到:“我把魯迅的‘三美說應用到翻譯上來,就成了譯詩的“三美”論。這就是說,譯詩要和原詩一樣能感動讀者的心,這是意美;要和原詩一樣有悅耳的韻律,這是音美;還要盡可能保持原詩的形式,這是形美。”[2]許淵沖先生曾談道:“在三美之中,意美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音美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形美是更次要的,是第三位的。我們要在傳達原文意美的前提下,盡可能傳達原文的音美;還要在傳達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盡可能傳達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齊備。”[3]
由此可見,許淵沖先生的“三美論”,以“意”、“音”、“形”的統一,力求構建詩歌譯作之美,使譯入語讀者領略中國詩歌魅力。“三美”翻譯理論的提出,為詩歌翻譯樹立了更為具體的標準和原則,促進了文藝美學派理論的發展。
二、“三美論”再現唐詩英譯之美
唐詩是唐代儒克文人之智慧佳作,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唐詩意象豐富,形式規范,韻律考究,在為華夏子孫帶來聯覺美、視覺美、聽覺美的體驗的同時,這種“帶著鐐銬的舞蹈”[4]也為唐詩譯者造成了困難,雖不少名家參與其中,卻鮮有成功之作。許淵沖先生憑借深厚的文學功底,將“三美論”貫徹于唐詩譯本字里行間,力求傳達唐詩自有的情感和韻味,其唐詩譯本不乏傳世經典。本部分將以許淵沖先生的唐詩英譯為例,從“三美論”的角度鑒賞譯詩美感再現。
1.意美再現
唐詩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意境之美,古人常借物抒懷、寓情于景,通過煉字和意象勾勒出詩歌獨特的意境美,許淵沖先生認為“意美”是“三美論”中的提綱挈領的一環,是實現“音美”和“形美”的充要條件。只有譯者對原詩詞心領神會,才能在譯文中傳遞心靈的震撼。下面我們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英譯為例,賞析許淵沖先生實現意美再現的手法。
原詩: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譯文:
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
For River Town veiled in green willows and red flowers.
His lessening sail is lost in the boundless blue sky,
Where I see but the endless River rolling by.
這是唐代詩人李白為好友孟浩然而作的一首送別詩,詩中寄寓了詩人與友人在江夏的依依惜別之情,要將原詩的意境之美以譯文形式表現出來實屬不易,許淵沖先生在此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從傳意上看,許淵沖先生的譯法巧妙得當,如在譯頷聯時,不落窠臼地使用“unveiled”這一動詞將花開似錦的陽春三月描繪成一幅映入讀者眼簾的畫卷,同時將煙花一詞處理為“green willows and red flowers”,因為“煙花”一詞形容柳絮如煙、鮮花似錦的春景,指艷麗的春景,但因譯入語讀者文化差異和地理差異很難對這一意象產生共鳴,用“green”和“red”兩個形容詞定語對原意象加以補充修飾更能為讀者傳遞視覺體驗;在處理頸聯譯文時,許淵沖先生并沒有使用“lonely”表現“孤帆影只”之感,匠心獨具地將“lessen”這一動詞轉化為現在分詞,極力地烘托出友人乘一葉扁舟由大到小,漸行漸遠的意境,展現出譯者文學積淀之深厚;尾聯的處理也甚是巧妙,用“endless”和“rolling by”前置和后置定語相結合的方法將長江之水奔流天際之景刻畫得惟妙惟肖,同時反襯出頸聯中的“lessening sail”的渺小,與上一聯前后呼應,韻味無窮。
2.音美重塑
唐詩音韻和諧,格律嚴謹,抑揚頓挫之間,展現韻律之美,但也為其英譯增添了極大地難度,因為漢語和英語屬不同語系,發音體系也有很大差異,在譯作保留原詩意義的過程中,很難兼顧音律。許淵沖先生作為我國譯界格律詩體派代表人物,將“音美”納入其“三美論”中,主張保留原詩音韻。正如他所說:“以詩體譯詩好比把蘭陵美酒換成了白蘭地,雖然酒味不同,但多少還是酒; 以散體譯詩就好像把酒換成了白開水......。”本部分以《登鸛雀樓》為例展現許淵沖先生這一思想。
原詩: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譯文:
The sun beyond the mountains gl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can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登鸛雀樓》是盛唐詩人王之渙的一首五言絕句,此詩雖然只有二十字,卻以千鈞巨椽,繪下北國河山的磅礴氣勢和壯麗景象,氣勢磅礴、意境深遠,千百年來一直激勵著中華民族昂揚向上。原詩押(iou)韻,“流”和“目”二字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而許淵沖先生譯文采用aabb式,具有英國古詩特征,符合譯入語讀者閱讀習慣,頗具韻致,寥寥數字,在韻律層面上卻做到了極致。譯文中“glows”和“flows”,“sight”和“height”押尾韻;譯詩首聯中“mountains”和“glows”與頷聯的“seawards”和“flows”尾音均為輔音[s],頸聯中的“grander”和“greater”開頭和尾音均一致,分別為[g]和[r],尾聯“sight”和“height”尾音均為[t],從而實現了行內或隔行輔音韻和頭韻的統一;不僅如此,首聯中的“sun”、“mountains”,頷聯中的“yellow”、“flows”,頸聯中的“can”、“grander”,尾聯中的“climbing”和“height”構成行內韻或行內元韻。由此可見,許淵沖先生不僅用譯詩再現了唐詩音律之美,甚至通過再創造的形式在格律層面超越了原詩,將原詩都沒有達到的韻律效果,以符合譯入語的語言表現形式呈現了出來。
3.形美對應
許淵沖認為詩詞翻譯的形美,主要是譯詩在句子長短、對仗等方面再現原詩的形美。中國詩詞注重對偶,而“形美”便是對偶的特點之一。因此在唐詩翻譯中要盡可能做到與原詩形式相仿,對仗整齊。以許淵沖先生譯李白的《夜下征虜亭》為例進行說明:
原詩:
船下廣陵去,月明征虜亭。
山花如繡頰,江火似流螢。
譯文:
My boat sails down to River Tower,
The towers bright in the moonlight.
The flowers blow like cheeks aglow,
And lanterns beam as fireflies gleam.
從行數和分節來看,原詩是五言絕句,譯文行數與原詩一致,除第一句有九個音節外,其余每句八個音節;從對仗來看,頸聯和尾聯部分中譯詩與原詩一樣,形式統一,對仗工整。原作中“山花”對“江火”,“繡頰”對“流螢”,為避免重復使用了不同的比喻詞“如”和“似”。在譯作之中“flowers”對“lanterns”,“blow”對“beam”,“cheeks aglow”對“fireflies gleam”,比喻詞同樣采用了對應的“like”和“as”。許淵沖先生以英譯本實現詩歌對仗之美,達到了“形美感目”的效果,實屬難得。
三、“三美論”難掩唐詩英譯之瑕
“三美論”在唐詩英譯過程中的先進性已經不言自明,但其自身暗含的局限性任然無法忽視。“三美論”中的“三美”的重要性并非鼎足三分,“意美”、“音美”、“形美”的分量依次漸弱,因形傷意,因意生議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此外,“三美論”的最高標準“三美齊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對譯者自身雙語文學修養要求極高,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焚膏繼晷的鉆研很難將“三美論”付諸實踐。許淵沖先生作為“三美論”的踐行者,雖留下無數傳世譯本,著作等身,但因“三美論”自身局限性和理想化的特點,也很難使其所有作品白璧無瑕。下面以實例進一步分析,并試探性地提出改進策略。
1.因形傷意
唐詩的格律體系完備,其中近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甚為嚴格,不僅每句字數限定,平仄有別,韻腳一致,還要講求上下對仗,詞性對應。因此,在翻譯格律詩中,被音韻格律束縛,稍不注意就會出現敗筆,以至于減弱原詩的韻味。以許淵沖先生所譯《江雪》為例。
原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譯文: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in a boat,lo!
Fishing on river clad in snow.
《江雪》是唐代詩人柳宗元于永州創作的一首五言絕句。全詩構思獨特,語言簡潔凝練,意蘊豐富。許淵沖先生譯詩每行字數基本相等,音節數基本相同,以四部抑揚格替代原詩格律,雖不與原詩音似,卻傳遞了原詩的音美。前兩聯譯詩與原文達成了形式功能上的一致,原詩以“千山”對“萬徑”,“鳥”對“人”,“飛絕”對“蹤滅”,名詞與動詞相對應,靜態與動態相結合;譯詩以介詞短語“from hill to hill”對“from path to path”,以名詞短語“no bird in flight”對“no man in sight”,而且除“bird”和“man”之外,其余所有單詞字數相同,不拘泥于原文的表層形式,既譯出了原詩的內容,又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可見許淵沖先生極力做到了原詩的“形美”。美中不足的是許淵沖先生對于“形美”的堅守,無意之間可能在煉字層面減弱了原詩的“意美”。“hill”在英文中的定義為山丘,而非詩歌意象中的山巒或山脈,將“千山”中的“山”譯為“hill”不容易引起譯入語讀者,身處群山之間的孤寂落寞之感。張廷琛、魏博思在《一百叢書》的唐詩一百首,將前兩聯譯為“Over a thousand mountains the winging birds have disappeared.Throughout ten thousand paths,no trace of humankind.”[5]雖然從“千山”這一意象的傳遞層面更為準確,但行文繁瑣,亦無韻律可言,算不上好的譯作。如果單純將許譯原詩首聯中的“hill”改為“mountain”,則無法做到與頷聯中的“path”做到字數一致,削弱了譯詩的“形美”。所以筆者認為不妨將“hill”改譯為“peak”,這樣一來既能做到譯詩字數統一,又能體現千山層巒疊嶂之感,以“意美”引起讀者的聯覺;不僅能使前兩聯詩行內實現了頭韻,而且行間也實現了這一效果,以“音美”豐富了譯詩格律,更好地做到了“意”“音”“形”三美的統一,從而使讀者更能體現詩人孤身與天地之間的惆悵與寂寥之情。
2.因意生議
“意象”一詞,最早出現于劉勰的《文心雕論·神思》“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近,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唐詩中的意象不僅是審美客體的現實生活中景物、事物與場景的表象,更是賦予了詩人主觀審美思想和情感的意韻。因中西方文學中的意象存在較大差異,唐詩英譯過度直譯可能會對譯入語讀者產生費解,對作意象的使用存有異議。以許譯詩人李白的《長干行》和李商隱的《無題》為例:
原文:
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
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譯文:
My forehead barely covered by my hair,
Outdoors I plucked and played with flowers fair.
On hobby horse he came upon the scene,
Around the well we played with mumes still green.
《長干行》因為整首詩通過各種意象的描寫來體現出女子對丈夫的思念之情,前四句詩文主要表現了女子與丈夫年孩童時代嬉戲玩耍,天真無邪的和諧場景。許淵沖先生譯文前四句詩韻腳整齊,處理得當,但在最后一句“青梅”這一意象的處理可能仍有改進的空間。許淵沖先生將其音譯為“mume”,指代盛產于中國長江流域的水果,在意象所指的客體含義層面譯得十分準確,但作為譯入語的讀者很難因象悟意。筆者認為如果將“mume”改譯為“plum”可能效果更佳,因“plum”是西方通用的意象,除了本義“梅子”之外,還有“稱心之物”之意,更能令讀者想象出孩童時代嬉戲玩鬧,兩小無猜的美好畫面,也為下文二人喜結連理做了鋪墊,補充了原譯的“意美”。這種處理方式也使“play”和“plum”形成了頭韻,與第二句的“plucked”和“played”音韻上相互呼應,豐富了“音美”。
四、結語
結合以上唐詩英譯案例可以見得,許淵沖先生提倡的“三美論”對我國唐詩翻譯與鑒賞提供了理論支撐,對唐詩譯者具有良好的指導意義和啟迪作用。但“意”、“音”、“形”三美齊備終究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很難在實踐中達到“三美”和諧統一,因此將“三美論”奉為圭臬的譯者,需要有精益求精,功不唐捐的態度才可能臻于完美。許淵沖先生作為“三美論”的踐行者,對其經典之作數次刪繁就簡,字斟句酌才達登堂入室之境,以身體力行照亮東方譯界的“北極光”。
參考文獻:
[1]許淵沖.翻譯的藝術[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7:95
[2]許淵沖.文學與翻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77
[3]許淵沖.“毛澤東詩詞”譯文研究[J].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報,1979(1):39
[4]呂叔湘.中詩英譯比錄序(再版)[M].上海:中華書局,2002:1-16
[5]張廷琛.一百叢書[M].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