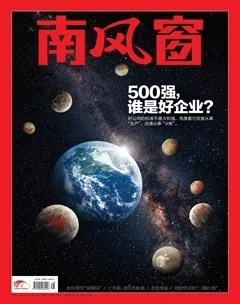警惕“內卷化”
趙義
最近,清北碩士和博士應聘浙江余杭街道辦崗位的新聞引起熱議。清北名校的人才和街道辦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巨大的反差,讓人們不得不追問這是不是意味著什么。
這種反差的觀感是不是合理,暫且不論。有一個評論引起了記者的關注,大意是說,名校碩博生競爭街道辦的崗位,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至少部分說明,曾經活力無限、龐大無比的“市場”,是否在不斷塌縮之中,內卷化不可避免。
請注意“內卷化”這個詞。這個概念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涉及的議題非常廣泛。這個觀點有個隱含的意思,是說這些名校碩博生在街道辦一定是做價值含量不高、與本來對清北的期待不匹配,從而嚴重浪費人才資源的事情。(事實上并不是如此,這里不展開。)
與之相關的是人們常說的“內卷化效應”,即長期從事一項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層面,沒有任何變化和改觀。比如,在分析形式主義對基層工作的危害時,人們就注意到,在鋪天蓋地的形式化考核驗收、督查檢查的壓力下,許多基層干部被迫陷入重“痕”不重“績”的材料主義、痕跡主義,工作上就陷入一種簡單層次上的自我重復,進而處于自我懈怠、消極應付的狀態,“年終盤點卻乏善可陳、兩手空空”。
從學術源頭上看,這實際上是“內卷化”概念的泛化應用。用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馬衛紅的話說,只要社會發展或者組織變遷中存在結構僵化或內部日趨復雜化但治理無效的現象,都用內卷化來解釋,“它成為解讀中國問題的萬能鑰匙”。
對“內卷化”理論,最廣為人知的是經濟學家黃宗智。2020年恰好是黃宗智在對華北小農經濟研究中系統論述內卷化概念第35年,其基本觀點是指小農經濟在高密度人口壓力之下(這與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不同)的生存需求推動的勞動報酬遞減的“內卷化”(involution)。后來,黃宗智進一步把“內卷化”解釋為“沒有發展的增長”。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黃宗智也說,“內卷化”一詞如今已經相當廣泛地用于農業經濟領域之外,被用來表達“幾乎是沒有任何質變而僅是越來越緊密的勞動投入(以及邊際回報遞減)的現象”,甚至包括了應試教育體系中學習的“內卷化”。
更需要注意的是“市場”是否萎縮的問題。這是我們真正要關心的: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逆全球化變局之下,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都大幅萎縮,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那么,“內循環”會不會導致經濟生活的“內卷化”?這里的“內卷化”更接近其原始含義,即在生存需求壓力(直接體現為社會的就業)之下,仍然不斷在舊有產業結構、過時供給方式與落后技術水平的層面上繼續投入資源,從而被鎖定在低水平重復的困境之中。
顯然,這與決策層期待的經濟的升級、實現創新驅動型發展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現在的中國經濟當然不存在“內卷化”,但必須警惕這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其實是在上升的。尤其是美國對全球化的重新設計和“去中國化”是個長期的過程,不管其決策者是否有過相關考慮,但“內卷化”導致的創新的停步一定會正中其下懷。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最近撰文認為,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并不意味著我國經濟不再重視國際經濟循環,經濟開始內卷化。但必須避免一個重要的錯誤傾向:由于中美貿易摩擦、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和一些國家努力推動“去中國化”等原因,我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短期會受到明顯抑制,我國的供應鏈會受到侵蝕,在現在情況下,國內經濟循環量“此消彼長”會大幅提高,由此就貿然判定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基本形成。
這種被動形成的發展格局,可能就存在某個行業或者某個領域的經濟“內卷化”,就不是我們期待的新發展格局。
在提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黨中央對下一步改革開放也有系列的重要部署,包括擴大開放、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挖國內巨大消費潛力等。簡而言之,要避免出現經濟的“內卷化”,還是得靠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
黃宗智對小農經濟去內卷化過程的研究說明,走出內卷化離不開農業人口的非農就業閘口的打開。正是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對內開放也是開放)才真正讓去內卷化變得可能。這個過程,對今天我們的抉擇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