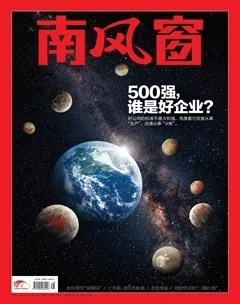美國的“歷史包袱”

雷墨
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美國就有了“另類”的形象,即便是在西方國家眼中。所以我一直在思索這樣一個問題:這位特立獨行的總統,是如何讓美國如此“另類”的?
最近閱讀了一些著作文獻后,有了些許感想:一方面,如今的美國變得讓人覺得陌生,有“特朗普因素”的作用,但實在也因美國的“歷史包袱”使然。
把特朗普的執政與美國的亂象聯系在一起并不難。但亂象在他入主白宮前就已出現,特朗普的角色只是催化劑,加速了這一進程。就像新冠危機加速了國際秩序變遷一樣。設想一下,如果2016年贏得大選的是希拉里,美國的形象或許不會像現在這樣扎眼。
美國建國者們的制度設計里的“約束總統權力”,與特朗普個人的權力欲,形成了完美對撞,結果就是美國頻現憲政危機。
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政府功能失調、治理失序,在新冠危機沖擊下,甚至呈現無政府狀態。對此,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就做了預言式的解釋:“政治衰敗在許多方面是政治發展的條件:破舊才能立新。但這種過渡可能是非常混亂和暴力的,不能保證政治制度會持續、和平且充分地適應新條件。”
福山做出這個分析時,不可能預言到特朗普當選,更不可能預言到新冠危機和種族騷亂。也就是說,沒有這些因素,美國的“破舊立新”也會讓人有如履薄冰之感。有了特朗普總統,如履薄冰似乎就沒有必要了。
在當今主要世界大國中,美國算得上是非常年輕的國家,至今只有244年的歷史。所以,很難把美國這個國家與歷史包袱聯系在一起。但事實并非如此。
美國建國之初的制度設計,有理念先進的一面(比如制度化約束最高權力,當時世界還停留在君權神授時代),也有思想復古的一面。這種復古,在一定的時間內與美國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能和諧共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設計復古的特點越來越成為制度革新、體制轉型的掣肘。
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曾說:“美國的政治現代化勢頭極弱又不徹底。在制度方面,美國整體上雖不是落后的,但也絕非徹底的現代化。”“在當今世界,美國的政治制度僅因其古老這一點,就可以說是十分獨特了。”
在亨廷頓看來,美國建國之初的制度設計,帶有明顯的英國都鐸王朝特性(1485年至1603年)。他是這么說的:“17世紀定居北美的英國人,帶來都鐸王朝時期或中世紀后期的政治實踐。這些古老制度在美國本土盤踞下來,猶如凍結不變的古老社會的一部分,最終被寫入美國憲法。”
都鐸王朝特性指的是什么呢,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有個總結:“普通法作為權威來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門;法院在治理中發揮相應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傳統;主權由多個機構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權力分隔,而不是功能分隔。”
這些如何理解呢?以法院發揮行政功能為例,特朗普的“禁穆令”被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否決,后來又被最高法裁定合法。在其他西方民主制國家,尤其是議會制國家,禁止某個特定群體入境,完全是行政部門的事務。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因財政預算不通過而導致的聯邦政府關門。我們只聽說過某些歐洲國家組閣困難、政府難產,但從未聽說過政府部門因預算問題而關門。因為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編制預算都是行政部門的權力。
美國的權力游戲與政治算計,南風窗新書《重新認識美國》中有詳細的論述。美國建國者們的制度設計里的“約束總統權力”,與特朗普個人的權力欲,形成了完美對撞,結果就是美國頻現憲政危機。特朗普執政的亂象,能不與美國的“歷史包袱”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