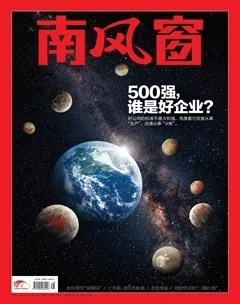誰是“中國好企業”?
譚保羅

廣東東莞,華為新園區
2020年8月10日,最新《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發布。中國大陸(含香港)的500強數量達到124家,歷史上第一次超過美國(121家)。加上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中國更大幅領先,世界500強達到了133家。
第三名日本只有53家,不到中美的一半。之后依次是法國、德國和英國,分別為31家、27家和21.5家。因為知名快消品公司聯合利華是英國和荷蘭“雙總部制”,所以兩個國家各算了一半,為“0.5個”。
回望本世紀加入WTO的最初幾年,中國人一直都希望自己的企業“做大做強”,世界500強成為中國人心中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首要標準。如今,中國企業群體早已超額實現了“做大”的目標,而至于是否“做強”,則標準不一,眾說紛紜。
至少,從“芯片禁運”事件來看,中國企業群體距離“做強”的確還有一段距離,在很多“卡脖子”的領域,中國軍團依然需要奮起直追。而且,對于到底什么是好企業,判斷標準也開始變得和過去不一樣。
企業“做大”的合理性
《財富》世界500強的排行榜始于1955年。從1945年到1950年年代中期大約10年的光景,這是美國經濟最高光的10年,其經濟總量一度超過全球的50%。這個時代,日本、聯邦德國這兩大工業國尚未從戰爭中完全恢復,美國的工業產品風靡全球,一大批大型企業不斷在全球攻城略地。
于是在1955年,《財富》雜志對美國最大的500家工業企業進行了排名,排名根據是各公司1954年的總收入。1995年,《財富》雜志首次發布了同時涵蓋工業企業和服務性企業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之后,“財富500強”成為通行全球企業領域的最重要排行榜,尤其讓后發國家和經濟體趨之若鶩。
除了華為“可以一戰”之外,富士康、聯想和小米與美國ICT制造行業的同行是沒有可比性的。美國軍團無不處于價值鏈的頂端,而中國企業多數都處在更低附加值的環節。
這一排行榜的核心依據是營業收入,即規模領先。在當時,這一標準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首先,在整個20世紀后半葉,都是大公司為王的時代,由于二戰之后全球化的加速,大型企業開始在全球擴張著投資和銷售版圖,營業收入的增長代表著企業是否具有利用全球化做大的能力,這是那個時代的“核心競爭力”。
此外,在工業領域,大公司之間展開了研發競賽。研發投入必須以收入為基礎,研發投入除以銷售收入即為“研銷比”,這是體現企業研發力度的首要指標。換個角度看,即在“研銷比”一定的情況下,收入總量越大,企業的研發投入就越多。于是,全球的大型企業逐漸認同了這樣一個道理:營業收入是研發投入的基礎,“做大”才有“做強”的資本。
今天來看,這一標準依然不過時。以中國最炙手可熱的華為公司為例,其“研銷比”一直在中國大企業中名列前茅。2019年,華為的“研銷比”為15.3%,在全球實現銷售收入為8588億元,其研發費用超過1300億元。此外,近十年來,華為投入研發費用總計超過了6000億元。顯然,巨大的銷售收入是華為加碼研發的“物質基礎”。
2020年的全球500強榜單凸顯了中國力量,但對這份榜單也必須“辯證看待”。首先,最容易觀察到的是,中國企業的“真實實力”并未超過美國。“真實實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核心產業的掌控力,二是企業本身的盈利能力。
在美國的上榜企業中,除了傳統的汽車制造巨頭之外,還有四個產業是上榜企業的主要來源,分別是ICT(信息與通訊技術)制造業、醫療器械制藥業、軍工航空航天和機械制造,而這四大領域無不都是“硬體技術”和“底層技術”的主要創新力量所在。在中國軍團中,盡管也有商飛、華為等“硬體技術”為導向的企業和航天軍工類企業,但龍頭企業的數量和質量和美國還不是一個數量級。
以ICT制造業為例,中國有華為、富士康、聯想和小米等,而美國有蘋果、英特爾、IBM和思科等,理性一點的人都清楚,除了華為“可以一戰”之外,富士康、聯想和小米與美國ICT制造行業的同行是沒有可比性的。美國軍團無不處于價值鏈的頂端,而中國企業多數都處在更低附加值的環節。
此外,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有差距。在這一榜單之中,美國只占企業數量的24.2%,但利潤總額高達8447億美元,占比高達40.98%。對比來說,中國上榜企業數量超過美國,但利潤總和為4437.18億美元,占比21.43%,僅為美國的一半左右。
實際上,除了在“強”的環節和美國還有差距,即使在“大”的環節,中國軍團也還需努力。
還缺世界性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軍團的銷售收入總和為9.8萬億美元,占全球500強企業總和的29.45%,中國第二為8.29萬億美元,占比24.91%。也就是說,中國企業的平均規模低于美國。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的海外銷售占比低于美國同行,這更不是一個秘密。和在海外開疆拓土相比,中國巨頭們更受惠于巨大的母國市場。在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公司絕大多數都是世界性的企業,而中國公司要尋遜色不少。
華為應該算是海外銷售占比最高的一家。2019年,華為全球銷售收入858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9.1%,其中,海外市場占比約41%。如果時間回溯到金融危機的時候,華為海外銷售占比更高。2008年,華為全年合同銷售額233億美元,約為現在的六分之一,但海外收入占比竟高達75%。
顯然,如果沒有華為早期外銷積累的資本和技術,便不會有今天的華為。因為,世界性的企業才有更大概率成為好企業。在沒有母國市場保護的情況下,在全球和同行短兵相接地搏殺,才能真正錘煉出一流的技術和管理。當然,好企業的標準遠遠不止海外銷售收入占比這一項。
那么,中國好企業的標準到底是什么?按照常識的標準,至少有三個。第一,生長于健康的市場結構之中,并非壟斷或寡頭式企業。這些年,不少觀點質疑中國的“三桶油”是在“搞壟斷”。實際上,按照經濟學的市場結構概念嚴格定義,它們更像是寡頭而不是壟斷。而且,這種市場結構也并非一無是處。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在與上游原油供應商議價的時候,規模大意味會削弱原油供應商的定價能力,對降低石油進口價格和緩解輸入性通脹,最終提升國民福利是有好處的—至于內部管理水平,則是另外一回事。換句話說,這種寡頭式市場結構有著其合理性和正義性。那么,問題在于哪里?在于中國的石油公司還應該不斷提升自己的海外銷售收入占比。
好企業的另外一個標準是,商業模式的正義性。在互聯網公司之中,競價排名是最受質疑的商業模式。但是,這不是全部。
埃克森美孚、BP、殼牌和道達爾等歐美石油公司的特點是,它們的非本國銷售收入占比極高,他們在全球與對手展開競爭。這種脫離母國市場的競爭,更能鍛煉出更好的石油開采技術和資源性巨頭的管理效率,而固守母國市場則沒有這種“倒逼”成長的機會。
好企業的另外一個標準是,商業模式的正義性。在互聯網公司之中,競價排名是最受質疑的商業模式。不過百度并沒有進入500強,盡管競價排名的利潤高,但營收規模不高,達不到500強門檻。同樣,其他領域也存在很多飽受質疑的商業模式,比如銀行的“吃利差”。
中國銀行業共有10家上榜,10家銀行利潤占全部上榜大陸企業利潤總額的44%。顯然,銀行利潤過高,必然擠壓非金融企業尤其是實體企業的利潤。中國銀行的超級盈利能力既來源于存貸利率管制的大環境,也來源于貸款主體預算軟約束等深層因素,并非完全是銀行自身的問題,但它的確從一個側面說明好的商業模式的標準到底是什么。
好企業的第三個標準是,它必須以技術與產品服務來贏得市場,并非單純通過資本運作來實現規模膨脹,更不能通過“收割”中小投資者讓股權擁有者獲得超額利潤。在這個意義上講,華為和小米這樣的企業,的確是好企業。華為一直都沒有上市,而小米在香港上市,并未在A股“圈錢”。
顯然,同時符合以上三個標準的中國企業并不多,華為無疑是極少數之一。毫無疑問,這也是任正非廣受尊敬的原因。
技術創新的兩種戰略
中國的好企業,并非只有一個華為,中國臺灣的臺積電也是中國人的驕傲。但臺積電走了和華為截然不同的一條路。臺積電是橫著切入全球產業鏈,成為產業鏈不可替代的一環,而華為則是縱向布局全球產業鏈,在多個環節與全球的巨頭展開了平行競爭。
回顧臺積電的崛起,至少有兩個厲害之處。一是它的創立和發展,直接改變了全球ICT制造業的格局。在集成電路產業最初勃興的時代,設計、制造一體化曾是最流行的模式,即芯片品牌企業擁有研發設計、制造甚至封測等全產業鏈環節。但這個模式也有一個巨大的缺陷—資本密集程度太高。

位于臺灣新竹的臺積電(TSMC)總部大廳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集成電路產業剛剛勃興,一條集成電路生產線需要投資數千萬到上億美元,在當時即是天文數字。而如今,動輒100億美元的生產線也不是新聞。這種超級資本密集的特點給了后發經濟體以機會,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韓國,之后是中國臺灣。
盡管美國人發明了半導體,但在198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一度凌駕在美國廠商之上。日本的殺手锏是“資本優勢”,日本商社控制著銀行和證券公司,而半導體公司又是商社的“子孫公司”,于是通過商社企業集群的內部融資,來自信貸市場和股權市場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支持者日本芯片企業。而且,日本公司采取了從芯片設計到制造的縱向一條龍模式。對比之下,美國的金融市場沒有這種“資本優勢”。
但日本人雄霸全球的產品只是存儲器,到了中央處理器為王的時代,情況突變。在個人電腦逐漸普及的1980年代末,美國人開始后來居上,其秘訣是兩招:一是放棄利潤低的存儲業務,專攻中央處理器,不斷推動中央處理器的升級換代,讓日本人沒有機會趕上。二是產業分工,將制造環節外包給韓國和中國臺灣,而自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設計環節,從而永遠地甩開了日本人。
臺積電是橫著切入全球產業鏈,成為產業鏈不可替代的一環,而華為則是縱向布局全球產業鏈,在多個環節與全球的巨頭展開了平行競爭。
1985年,張忠謀從美國返回中國臺灣,出任“工業技術研究院”負責人。1987年,他在臺灣新竹科學園區創建了全球第一家專業代工公司—臺灣積體電路制造公司(臺積電)。張忠謀創業的時點,正是美日半導體競爭的分化時代,他真正預見到了全球ICT制造業的大勢,順勢而為,造就了中國人的產業奇跡。
目前,在全球的晶圓代工領域,臺積電一直都保持第一,在全球占據約50%的市場份額。第二名則是韓國的三星。
臺積電的第二個厲害之處是,它以領先的制程和規模的優勢成為了代工環節的“價格殺手”,絕對不給進入者一點機會。通過這種方式,臺積電得以固守代工環節這一環,不做芯片設計、不做終端品牌,不用與上下游客戶發生利益沖突,避免了與歐美巨頭的競爭,從而成為全球ICT產業鏈中極具“系統重要性”的超級企業。形象地說,它已與歐美ICT巨頭融為一體。
但華為走的是另一條,它并不固守某一個環節,而是在全球與歐美廠商正面競爭,并且有縱向一體化的趨勢。這種競爭策略的不同,也決定了華為必然在做大做強之后遭到更多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圍堵。
但這種策略是華為作為一家中國龍頭企業的理性選擇,無論日本,還是韓國,東方后發經濟體的技術創新,最終必然和歐美展開全方位的競爭,甚至是全產業鏈通吃的縱向一體化戰略。實際上,三星在縱向一體化的道路上比華為走得更遠,除了和華為一樣有芯片設計企業和移動終端品牌之外,三星旗下的三星電子已經是僅次于臺積電的全球第二大芯片代工企業。
華為和臺積電的模式本無優劣之分,是雙方基于時代背景和地區產業稟賦的自然選擇。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是,2017年張忠謀曾透露,外資持有臺積電已逾八成。也就是說,從資本控股的意義來講,臺積電或許并非嚴格意義的中國臺灣企業,但它無疑是中國人智慧和雄心的產物。
到底什么是中國好企業?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答案可能并不只有一個維度。
責任編輯趙義 z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