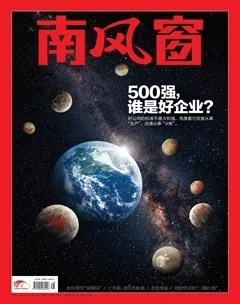解憂大廚房
何承波

油煙升騰的廚房,患者家屬們正在炒菜
在抗癌廚房,江西人竭力收斂嗜辣和重口的沖動。
但那名中年男子還是下了半盤“子彈頭”,辣椒素遇到熱鍋,頓時激發出催淚彈一樣的嗆味兒。一旁的老人大聲提醒:“癌癥病人吃不得辣哦。”—作為晚期胃癌患者,老人深知辣椒對腸胃的危害。
接著中年男子又放了一大勺鹽,許久才說:“我老婆中午喝了一口湯,覺得沒意思,飯都沒吃。叫我一定要多弄辣椒,多放鹽。”
8月27日這天傍晚,他炒了個五花肉,濃黑的醬汁,肉與辣椒幾乎等量。他自顧自地念著:“哎喲,過一天算一天,日子不多了。”
人們不再多說什么。男子匆忙裝好飯盒,領了米飯,快步走出了漆黑的巷子,返回一旁的江西省腫瘤醫院。
這是一間癌癥患者共享的廚房,廚房主人熊庚香逢人便說:“吃好飯,養好病,早點回家。”但有時這個美好的愿望變成殘酷的事實,他們不得不接受—“吃頓合胃口的,時日無多了。”
在抗癌廚房,食物總藏著生死。
鐘
墻上掛了兩座鐘,萬佐成和熊庚香覺得它們像自己。它們24小時不停轉啊轉,他們也24小時不停轉啊轉,轉成了另一種時間。
天沒亮,萬佐成就起床引火,點燃20多口煤爐,水壺裝滿,挨個燒上。另一邊,妻子熊庚香也開始煮粥。
抗癌廚房并不是真正的廚房,它位于腫瘤醫院西側,一棟自建的居民樓。廚房占據了門口10米左右的小巷子,共兩米寬,是炒菜的區域,沿路擺了8個煤灶,另一排是桌板,用來切菜。一樓兩間房子,還有十多個灶眼,用來煲湯。
天剛亮,病人和病人家屬就會趕來,打稀飯、做早餐,拉開抗癌廚房里一種非常態的日常。
早上10點,陽光從腫瘤醫院的高樓上照射過來,這里開啟了一天最忙碌的時刻。剁肉聲、鍋鏟聲、高壓鍋冒氣聲、熱油遇水的爆破聲,滋啦滋啦,哐哐當當,這是熊庚香最欣慰的景象:人們暫時忘卻了生老病死的緊迫性,只為吃好眼前這一餐。這個局促的空間,仿佛成了一間解憂廚房。
64歲的她,是個嗓門大的女人,她叉腰站在大飯鍋前,打飯、拉家常,見著人沖水不關龍頭,她吼叫的聲音會蓋過一切。但她并不總是這么暴躁。面對新來的患者,她總是齜牙笑著,安慰他們:“吃好飯才能養好病。”
混熟的患者、家屬,她會無所顧忌地開玩笑,醫院的氣氛太壓抑了,病人和家屬們需要放松一點。
67歲的萬佐成依然硬朗,頭戴棒球帽,臉上掛著兩只口罩。他提著水壺,穿梭于各個煤爐,為患者家屬們加水。
高壓鍋、蜂窩煤,在這樣一個老舊城中村,安全是懸在頭上的劍,他得隨時盯緊。他就像那座鐘一樣,停不下來。過年時,女兒拉他回家吃年夜飯,不到一個小時,他就趕回來了。
這樣的生活,一過就是18年。
30多年前,夫妻倆在新建縣的鄉下種地,1993年來南昌開餐館,2002年,他們換到這片城中村來,把如今這棟樓租了,擺攤賣油條。
2003年的某天,一對夫妻來問他們,可不可以借個爐火?
他們的孩子得了骨癌,截肢了。孩子鬧脾氣要回家,說飯菜不好吃,要吃媽媽做的。他們問了很多人家,都被拒絕。萬佐成沒多想,答應了:“你們天天炒都可以,我不收錢。”
沒多久,借爐火在病友圈傳開,人越來越多,有時幾十個人一起來,萬佐成索性多添幾個煤爐。久而久之,這里成了病友們約定俗成的“抗癌廚房”。
抗癌廚房長期保持虧損,十多年來,炒一個菜只收5毛錢。好在,他們做油條批發能賺錢,補了這個虧空。2016年,水電和物價飛漲,他們才漲了價,炒菜1元錢,米飯每盒1元,煲湯2.5元,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去年,他們停掉了油條生意,如今全心全意打理這間廚房。
8月的某天,有個南昌的大學生跑來,對熊庚香說,“奶奶,您還記得我嗎?10年前,我媽媽在這里炒菜,您天天給我吃油條。”
這期間,他們上了電視,上了熱搜。抗癌廚房成了個地標,不時有人來觀光打卡、發抖音。愛心也在傳遞。8月26日,快遞送來200斤大米,熊庚香打電話道謝,對方一直未接。
8月的某天,有個南昌的大學生跑來,對熊庚香說,“奶奶,您還記得我嗎?10年前,我媽媽在這里炒菜,您天天給我吃油條。”熊庚香想不起來。大學生接著講,那時候沒人帶他,媽媽病重,常把他扔到廚房,由熊庚香照看。
他告訴熊庚香,他的媽媽還是沒救活,36歲就去世了。
臨時避難所
抗癌廚房從不停止它的運轉。
2月10日,戴驊帶著丈夫,像逃亡一樣從吉安趕來。丈夫得了咽喉癌,去年做了切除手術后,正輪到化療時,疫情來了。
化療掏空了身體,那期間,他吃什么都是苦的,沒有湯,吃不下飯。
疫情管控,進出受限。戴驊守在醫院大門的卡口,“像叫魂一樣”,天天喊:“阿姨阿姨,救命噢,沒有湯活不下去噢。”
熊庚香從卡口接過食材,老萬洗菜,她煲湯、炒菜,在巷子對面架了樓梯,遞過去。
戴驊記得,有個11歲的小孩天天也喊:“奶奶,奶奶,我媽媽不給我煲湯。”
那是個苦命的孩子,他爸爸幾年前從工地上摔下來,死了,現在自己又查出腦瘤。
熊庚香免費給他煲參湯、排骨湯。
清明節剛過,孩子的媽媽發微信給熊庚香,說:“孩子走了,謝謝你。”
又發來一張骨灰盒的圖片。熊庚香嚇死了,“趕緊刪掉”。
但熊庚香轉了500元給她,聊作慰問。
來自弋陽的余紅朝也是疫情期間來的。15年前,他妻子跑了,把1歲的兒子留給了他。今年年初,16歲的兒子查出血液型淋巴癌,腦袋腫成大頭娃娃。
他借了30萬元,很快就花完了。接著要移植干細胞,費用高達50萬元。對于收廢品的他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
他來抗癌廚房做飯。兒子要吃,他必做肉或魚;兒子不吃,他只弄一點蔬菜,打三盒飯回去。他身體壯實,胃口不小,但為了省錢,有時就吃點米飯。
他覺得廚房里有人情味,像個家一樣。
癌癥,是一個家庭的滅頂之災,而抗癌廚房則像一個臨時的避難所。這里大多數家庭是來自鄉下,窮苦者居多。對他們而言,一場癌癥,傾家蕩產并不為過。來這里做菜,李虹梅也是圖節省。
她連連嘆息:“哎,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
兒媳每個月做一次化療,一年過去,已經花了20多萬元。她們住不起院了,擠在狹窄的賓館里,每天二三十元那種。
40歲的兒媳去年查出乳腺癌,但選擇保乳,切除了17個淋巴結。現在手臂使不上勁,免疫力也脆弱不堪,三天兩頭就感冒。更致命的是,癌細胞沒有徹底清除,不久前卷土重來。兒媳害怕了,下定了決心,左右乳房全切。
70歲的李虹梅全程照顧她,她懂得如何把節省發揮到極致。她每天光顧相同的攤主,混熟了,老板多給一點青菜,附贈幾棵蔥。孫子們還未成年,兒媳婦倒下,家庭也跟著塌陷。李虹梅不是家庭支柱,也要極力撐著。
李虹梅算過一筆賬,醫院食堂一份飯菜十多元,兩個人一天要近百元的開支,還不好吃。來抗癌廚房,開銷減半。
但她又有些“奢侈”,她隨身攜帶一大瓶礦泉水。8月27日,她用礦泉水給兒媳做魚湯,湯呈奶白色,不見一點鍋灰和浮渣。
李虹梅在家不太會做飯,但她相信,自來水煮湯沒有礦泉水好喝。
“日常”與殘酷
每一道食物背后,都是一種人生。這是個爛俗到小學生都能隨手用的比喻。但在抗癌廚房,它從未如此貼切、真實。
有的家屬無法忍受長期以來的癌癥食譜,趁著病人做手術的間隙,逮到機會解放味蕾,滿鍋辣椒,大快朵頤。一個長期在這里照顧媽媽的餐館經營者說:“不吃辣椒,我腦殼發昏。”
有人無法忍受醫院的氣味,他們在抗癌廚房找個角落蹲著,吃完再帶回病房。長期與疾病和醫院打交道,他們對病房有一種生理性的不適。有個家屬念叨,一到醫院吃飯,她就想吐。
病人也難以伺候。上餐要吃紅燒肉,下餐要稀飯。有個患者覺得熊庚香的稀飯不好吃,他妻子也不知道哪里不好吃。妻子親自來煮,這次嘗試煮硬一點,下次更軟一點,放點小菜。煮出來別人都覺得一樣,只有她知道區別在哪里。她個柔弱的女人,丈夫肺癌晚期,兒子進了監獄。現在她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柱。
8月26日中午,50歲的吉安人陳美玲炒了個苦瓜,只放了幾滴油,極其清淡。還沒開始治療,丈夫的食欲就比多數化療后的病人還差。
癌癥,是一個家庭的滅頂之災,而抗癌廚房則像一個臨時的避難所。這里大多數家庭是來自鄉下,窮苦者居多,一場癌癥,傾家蕩產并不為過。
53歲的丈夫前年查出了鼻咽癌,做了幾輪放療和化療,本以為萬事大吉,誰知癌癥防不勝防,不久前復發,轉移到肝上。但丈夫心臟也不太好,化療吃不消,要先治心臟病。什么時候開始治癌癥,要花多少錢,一切是未知數。丈夫情緒低沉、焦慮,有時又很暴躁。食堂飯不吃,陳美玲親手炒的,無論葷素,他也覺得沒味道,每天只吃一點稀飯。
他想念自家田里榨出來的菜籽油,念叨著只有家里的油才香。陳美玲能明白他的意思,丈夫是想回家,不想治了,把錢留給沒成家的兒子。
抗癌廚房里維系著一種難得的日常感。這里全是油鹽醬醋的生活氣息,病人家屬們感激熊庚香夫婦給了他們一種家的感覺。但它又是非常態的,生老病死,都藏在背后。對于癌患家庭來說,日常背后掩蓋不了殘酷。
8月底,鷹潭的劉敏給母親做了份甲魚,母親吃完又剝了個獼猴桃,不曾想食物中毒,母親抽搐起來,不斷蹬腳,翻眼皮,好在兩個小時后緩解了,但劉敏嚇到兩天都沒能緩過來。
她一度覺得自己沒能力承擔起這份沉重的擔子。
母親查出宮頸癌,要住院兩個多月。病房里還有個30歲的女人,天天哭:“我有房有車,這么年輕,怎么就得了宮頸癌。”
這搞得劉敏很壓抑,精神緊繃。那天,她來廚房煮稀飯,有人問她媽媽得什么病,她當即抓帽子捂住臉,嚎哭起來。
萬佐成說,很多人來這里,也是一種釋放。
在熊庚香眼里,窮苦人未必事事悲哀,有錢人也未必萬事美滿。這里沒有身份等級,大家都是落難人。
最典型的是56歲的劉進,他是抗癌廚房的特殊病人。
他不炒菜,每天來打個稀飯,卻比其他人逗留更久。他總戴著圓禮帽,Polo衫扎進皮帶里,皮鞋锃亮,指甲修長。他走路慢吞吞的,背著雙手,一直獨來獨往,沒有家人陪護。
劉進時常盯著油煙升騰的爐灶,看得入神。
不久前,劉進查出口腔癌,做了切除手術,傷口從嘴唇延伸到頸部,整個下巴像是鑲嵌上去的。熊庚香說,他是當大官的,來視察。他一笑,說:“只是個辦事人員,早退休了。”跟熊庚香開個玩笑,是枯燥日子里不多得的樂趣。
8月某個周末,他神清氣爽,像換了個人一樣,買了一斤瘦肉,切得大塊大塊的,丟進油鍋,油煙刺啦刺啦的。
我問他哪來的興致。他歪了下頭,示意一旁站著的中年女子,咧著長泡的歪嘴,笑:“女兒來了嘛。”
他總算親自參與了這份人間煙火。

抗癌廚房位于江西省腫瘤醫院西側城中村的小巷子里
生死疲勞
張國勝重新出現在抗癌廚房,她不停抹眼淚,念著:“好好的,怎么說擴散就擴散了呢。”8月26日下午,她炒了兩個菜。一旁病友家屬叫她不要放辣椒,但她還是放了。她說:“老范吃了沒味道。”
去年,丈夫范學景查出肝癌。在腫瘤醫院開刀做手術,切掉一個拳頭那么大的腫瘤,腰上留下了一道近一米的傷口。
她正說著在抗癌廚房一年的生死見聞。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跑進來,掃了掃掛在門邊的二維碼,還沒等收款的聲音響起,人就跑開了。張國勝更加難受起來,眼淚滾落不止,她不斷伸手擦拭。
丈夫患病后,她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天塌了”,也感受到什么是人間情義。她是個悲喜形于色的女人,眉毛緊蹙,臉色也是垮塌的,大多數時候,是丈夫露著大白牙的笑容感染著她。
4月份,夫妻倆滿懷希望地出院。
還不到半年,癌癥復發、轉移,丈夫也蔫了下去。
熊庚香對這些場面習以為常。
每年,有一萬多人跟她的廚房產生聯結,他們來自江西各地,每個月來做一次放、化療,住院10天左右,回去了又來,如此反復兩三年。臨走時,他們在墻壁上留下一個電話。密密麻麻的,字跡褪色,已難辨認。
電話很少撥通過,熊庚香知道,大多數人已經不在了。
臨走時,他們在墻壁上留下一個電話。密密麻麻的,字跡褪色,已難辨認。電話很少撥通過,熊庚香知道,大多數人已經不在了。
半數以上的患者活不過5年。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癌癥患者的5年存活率只有30%,或者更低。最近10年才穩步增長,2019年來到40%。
廚房里的釘子戶是老夏,他老婆得了宮頸癌,熬到第七年才撒手人寰。熊庚香記得,老夏剛來時,神氣得很。他是做生意的,家底深厚,覺得有錢什么病都能搞定,錢定勝天。“那時他這個也瞧不起,那個也瞧不起。”
疾病惡化超乎老夏的預料,沒多久,癌細胞轉移至大腦,壓迫了神經,妻子臥床不起,也沒法說話。老夏掏空了家底,賠上事業,落到熊庚香所說的境地: “油鹽都要我的,飯也免費給他”。疫情剛結束,他妻子就死了。如今他在當保安。
有人不得不懷抱希望,也有人不得不接受現實。
今年6月,馮素琴得知兒媳查出胃癌晚期時,她整個人都崩潰了,自己也跟著病倒,住院。兒媳才32歲,比自己親生女兒還親。一家人本來到南昌的醫院做切除手術,但醫生告知,癌細胞已經擴散,切除毫無意義。腹部積水嚴重,要穿刺放液。一家人必須要接受保守治療的現實了:活一天,是一天,如果不治療,死得會更快。在醫院,痛苦少一些,在家只會活活痛死。
化療后,兒媳吃不下飯。馮素琴改了食譜,她放了辣椒,但每次都切兩三種顏色的,盡量弄得鮮艷一點,看起來有食欲。
8月26日傍晚,馮素琴走后,抗癌廚房也接近天黑了。一對近70歲的老夫妻走了進來。熊庚香認得他們。老頭笨拙,不會做飯。一般是得了乳腺癌的妻子在操勞。妻子為滿足丈夫口味,放了很多辣椒,自己就接杯水,涮一下再入口。
這天,兩人吵架吵得厲害。菜剛下鍋,丈夫就捧著蔥花過來,正準備放進去,被妻子厲聲喝住,丈夫氣得跺腳,差點把蔥花扔在地上。
這是一幅奇妙的景象,病魔的陰影在褪去,他們的生活終于回歸了日常的生機。
早些年,子女和親戚不理解熊庚香,為什么天天跟癌癥病人打交道。那時,她其實也有點私心:“癌癥太可怕,我多做點好事,你別來找我。”
過了60歲,她覺得自己邁入了生命的新階段:“不管得什么病,我都不難過了。”
(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責任編輯李少威 ls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