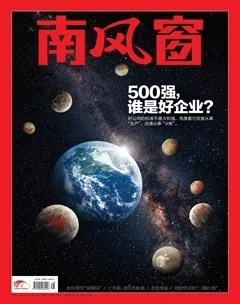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哲學梗”不是這么玩的

徐英瑾
最近有一篇浙江省高考滿分論文被刷了屏。這篇論文用典極多,用詞冷僻,文風歐化,很多網友直呼“讀不懂”。很多網友私信問我,既然這篇作文用到的很多梗都提到了哲學家(如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麥金泰爾、韋伯、尼采等),你們這些職業從事西方哲學研究與教學的專家,又將怎么評價這篇作文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只能報之以苦笑。有點哲學史常識的人都清楚,大哲學家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批評別的大哲學家。因此,如果你要同時對兩個彼此不服氣的大哲學家同時表示服氣的話,你就有很大的概率犯下“自相矛盾”的錯誤。但這位考生一口氣就寫下了這么多哲學家的名字,他能夠保證他所調用的這些資源不會彼此打架嗎?
以他對于麥金泰爾的引用為例。麥金泰爾是西方社群主義倫理學的重要代表,主張個體所在的共同體對于個體的生活的意義奠基作用。就是說:你要過啥生活,成為怎樣的人,取決于你從小從周遭人等那里得到的種種教化。麥金泰爾所強調的這層意思,其實是與作者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中的主人公柯希莫—有所沖突的,因為柯希莫恰恰背棄了自己的家庭共同體,爬到樹上去過半野人式的生活了。當然,作者完全有權利在麥金泰爾的思想與卡爾維諾的思想之間達成某種綜合—但達成綜合的前提恰恰是揭露矛盾,并在此基礎上為如何解決這種矛盾提供理性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假裝矛盾本身不存在。再以他對于維特根斯坦的引用為例。他引用維特根斯坦,據說是要面對“不可說者保持沉默”,但維特根斯坦說這話的真正意思卻是“要把說得清楚的事情都說清楚”,然后讓“不可言說者”自我顯示出意義。換言之,維特根斯坦恰恰是主張人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有話好好說”,而不要故弄玄虛的。而晚年的維特根斯坦又進一步強調哲學家要向日常語言學習,尊重百姓的語言習俗,不要沒事造怪句子。
現在我們就拿這篇作文里幾乎沒出現哲學典故的一個句子來做例子,來看看作者的寫法是否能夠入維氏語言哲學的法眼了吧。這個例句便是:“……何況當礦工詩人陳年喜順從編輯的意愿,選擇寫迎合讀者的都市小說,將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為橋段素材時,我們沒資格斥之以媚俗。”說得不客氣一點,這個語句的構造方式,至少包含三個語法錯誤:第一,此句中提到的“況且”意義不明。“況且”一般表示意義的遞進,并略帶反問語氣,但我們在這句話中卻看不出任何意義的遞進。第二,這個句子提到的代詞“之”指代不明。此句的主干結構是“當……時,我們沒資格斥之為媚俗”—很明顯,“之”在這里既可能指代時間,也可能指代相關時間區間里發生的事件,也可以指代事件的當事人,意義十分含糊。若將其替換為“此作為”或“此舉”,則指代關系能夠明確很多。第三,此句的構造,違背了漢語構造的一般原則,即從句結構不能太復雜。但在時間狀語結構“當……時”之中,作者卻塞入了一個非常冗長的句子,即“礦工詩人陳年喜順從編輯的意愿,選擇寫迎合讀者的都市小說,將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為橋段素材”。這種寫法大大加劇了讀者的閱讀思維負擔,而且犯下了“肢強干弱”的構造錯誤。由此看來,整個句子都需要被重寫。一種可供參考的改寫方式如下:無獨有偶,礦工詩人陳年喜也曾順從編輯的意愿, 將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為都市小說的橋段素材,以求迎合讀者之口味。對于陳氏之舉,我們沒資格斥之以媚俗。這樣的作文被吹捧,可見中學語文界對于漢語語法教學與思維邏輯訓練的輕視,已經到了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