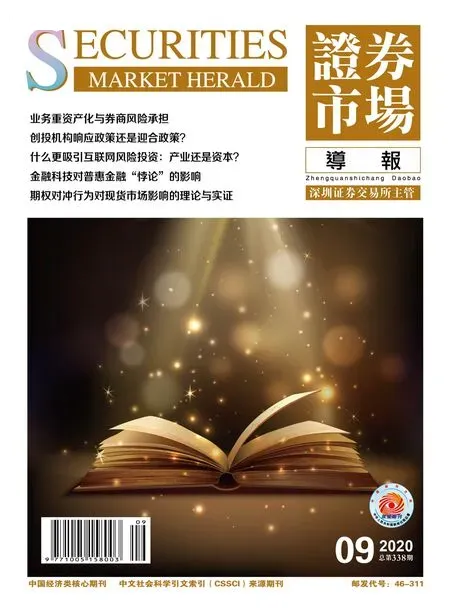創投機構響應政策還是迎合政策?
——基于政府引導基金激勵下的投資視角
李善民 梁星韻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一、引言
創業期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一直面臨嚴重的融資難問題。國際經驗表明,發展創業投資是破解創業期企業融資難問題的重要手段。我國創業投資規模近年增長較快,但是創業投資機構普遍偏好投資短期、低風險的項目,對創業期企業投資明顯不足。為了激勵創業投資機構投資創業期企業,近年來我國積極設立政府引導基金1,向創業投資機構管理的創業投資基金提供資本,同時要求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的投資達到一定金額。當前我國政府引導基金在創業投資市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政府引導基金已累計出資860余億元,帶動市場資金超過4800億元。2但也有媒體指出,部分創業投資機構通過“交作業式”投資來應付政府引導基金的考核要求,投資效果難以保證。3
已有文獻在研究政府引導基金的引導效果時,主要是考察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支持下是否投資政策目標領域(Cumming,2007;叢菲菲等,2019;施國平等,2016)[2][13][21],較少對創業投資機構投資政策目標領域的動機進行分析。部分學者提出市場參與者會積極性地響應政府扶持政策(陸國慶等,2014;許玲玲,2017;余明桂等,2016)[20][25][29],部分學者則指出市場參與者會策略性地迎合政府扶持政策(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楊國超等,2017;趙璨等,2015)[16][27][31]。 那么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扶持下投資政策目標領域,究竟是為了響應政策,還是為了迎合政策?
基于我國創業投資基金的數據,本文探討了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激勵下投資創業期企業的動機及經濟后果。研究發現,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顯著地增加了創業期企業的投資,但增加的投資主要是投向創業中后期企業,較少投向創業初期企業;上述現象在低聲譽和民營創業投資機構管理的基金中明顯存在,在高聲譽和國有創業投資機構管理的基金中則沒有明顯存在;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的投資績效出現了輕微的下降。實證結果表明,政府引導基金會激勵創業投資機構采取策略性行為迎合政策,選擇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降低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違背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本文的研究貢獻體現在:第一,分析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扶持下投資創業期企業的動機,加深了對政府引導基金作用機理的理解;第二,揭示政府引導基金政策引發的激勵扭曲效應,拓展了對政府引導基金政策研究的視角;第三,討論創業投資機構投資行為的影響因素,豐富了對創業投資研究的文獻。
二、文獻綜述
(一)政府引導基金的引導效果
學術界對政府引導基金的引導效果進行了研究,大部分學者支持政府引導基金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發揮引導作用。Cumming(2007)[2]研究表明,在獲得澳大利亞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創業投資基金顯著地增加了創業期企業和科技型企業的投資。Cumming and Johan(2009)[3]研究發現,創業投資基金在獲得澳大利亞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投資創業期企業的可能性顯著地提高了。Lim and Kim(2015)[9]研究表明,在韓國創業投資市場的發展初期,政府引導基金顯著地增強了創業投資基金投資科技型初創企業的意愿。施國平等(2016)[21]研究發現,在獲得我國政府引導基金扶持后,民營創業投資機構顯著地增加了創業期企業的投資。叢菲菲等(2019)[13]研究表明,在我國政府引導基金的帶動下,民營創業投資資本顯著地增加了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投資。李善民等(2020)[17]研究發現,在獲得我國政府引導基金資助后,創業投資機構顯著地增加了科技型初創企業的投資。
(二)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勵效應與激勵扭曲效應
部分學者提出,當政府實施扶持政策時,市場參與者會積極地響應政策,從而增加社會的整體效益,即政府扶持政策具有激勵效應。陸國慶等(2014)[20]研究表明,政府補貼可以激勵企業創新,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余明桂等(2016)[29]研究發現,產業政策可以促進企業創新,對民營企業有更明顯的激勵作用。許玲玲(2017)[25]研究表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策可以激勵民營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對認定前沒有享受稅收優惠的企業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部分學者則指出,當政府實施扶持政策時,市場參與者會策略性地迎合政策,導致政策的實施效果降低,即政府扶持政策存在激勵扭曲效應。趙璨等(2015)[31]研究發現,盈利狀況較差的企業會通過負向盈余操縱的方式尋求政府補貼,盈利狀況較好的企業則會通過尋租的方式尋求政府補貼,導致政府補貼的效果減弱。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16]研究表明,受產業政策激勵的企業為了獲得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會策略性地增加低質量專利的申請數量,造成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楊國超等(2017)[27]研究發現,企業為了獲得高新技術企業享有的稅收優惠和政府補助,會操縱研發投入來達到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要求,導致公司研發績效下降。
(三)文獻評論
大部分文獻的研究結果表明,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會增加政策目標領域的投資,并據此提出政府引導基金發揮了引導作用。但是需要注意,各國的政府引導基金普遍設置了參股的條件,對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方向進行了約束。由此可見,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支持下投資政策目標領域,并不必然說明政府引導基金發揮了引導作用。雖然有部分文獻提出政府扶持政策可以激勵市場參與者積極性地響應政策,但也有不少文獻指出政府扶持政策可能會激勵市場參與者策略性地迎合政策。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激勵下投資政策目標領域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已有文獻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本文研究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扶持下投資政策目標領域的動機及經濟后果,既可以深化對政府引導基金作用機理的理解以彌補現有文獻的不足,也可以為有關部門完善政府引導基金運行機制提供政策建議。
三、制度背景與研究假設
(一)制度背景分析
雖然我國創業投資規模近年增長較快,但創業投資機構追求短期和低風險收益傾向突出,表現為主要投資擴張期企業和成熟期企業,對創業期企業投資明顯不足。上述現象引起我國政府的擔憂,為引導創業投資機構投資長期、高風險的創業項目,政府引導基金這一激勵政策應運而生。2002年我國成立了首只政府引導基金——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2008年我國發布《關于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范設立與運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政府引導基金的運作規范,隨后我國政府引導基金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
我國政府引導基金按照“母基金”方式運作,政府引導基金作為有限合伙人出資參股創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由創業投資機構負責投資和管理,政府引導基金不直接干預創業投資機構的決策,從而保證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決策符合市場規律。同時,政府引導基金采用“少數參股”原則,出資不高于創業投資基金總規模的25%左右,不做第一大股東,創業投資基金的其余資本由創業投資機構向市場募集,這樣既可以放大政府資金規模,也可以利用市場投資者監督創業投資機構。此外,政府引導基金不追求盈利,還對創業投資活動提供一定的風險補償,以吸引市場投資者。
為實現政策目標,政府引導基金對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方向進行了約束:首先,創業投資基金需主要投資于轄區內的企業;其次,創業投資基金應主要投資于新興產業領域;最后,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的投資額需至少達到總投資額的35%左右,或至少達到政府引導基金出資額的1.5倍左右。
(二)研究假設提出
在我國的市場環境中,創業投資機構對創業期企業的投資意愿普遍較弱。創業期企業具有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高度的不確定性,外部投資者無法有效地甄別和監督創業期企業,導致嚴重的市場失靈問題(Lerner,2009)[7]。同時,我國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高風險、缺少抵押品的創業期企業難以獲得銀行貸款,容易出現資金鏈斷裂而倒閉(林毅夫和李永軍,2001)[18]。此外,我國上市制度還不完善,IPO機會稀缺,創業投資機構缺乏暢通的退出渠道(楊其靜等,2015)[28]。
按照我國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初衷,政府為創業投資基金提供資本和風險補償,并對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方向進行約束,以激勵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創業期企業。由于存在事前約定和事后考核,創業投資基金必定會投資創業期企業,從表面上看政府引導基金實現了政策目標。但實際上創業投資基金可能是策略性地迎合政府引導基金政策,其投資行為會偏離政策制定者的本意。
首先,創業投資機構有動力采取策略性行為迎合政策。創業投資基金的收費模式一般為“2%+20%”,即創業投資機構按照基金資本規模的2%收取管理費,并根據基金結算利潤的20%收取利潤分成(Lerner et al.,2012)[8]。在這一收費模式下,創業投資機構會想方設法地尋求政府引導基金的扶持,只要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出資,不管基金的投資結果如何,創業投資機構都可以收取可觀的管理費。同時,創業投資機構有偏離政府引導基金政策目標的動機,如果將基金的資本投資于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創業投資機構就有可能獲取更高的利潤分成。
其次,政府引導基金的現行管理制度會誘發創業投資機構采取策略性行為。第一,政府引導基金有杠桿放大的要求,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創業期企業的金額需至少達到政府出資金額的1.5倍左右,這意味著有相當高比例的市場配比資金需投資于創業期企業。政府引導基金追求社會效益,市場投資者追求經濟效益,兩者的投資目標存在沖突。創業投資機構為了募集足夠的市場配比資金,需要滿足市場投資者的利益訴求(燕志雄等,2016)[26],將基金的資本投資于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第二,政府引導基金采用一般的國有資產管理方法,需要每年考核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以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為了應對國有資產的年度考核,政府引導基金在參股創業投資基金時,一般要求政府引導基金的出資份額不能出現虧損。政府引導基金的保本要求破壞了創業投資基金的有限責任保護制度,即使政府引導基金向市場參與者讓渡全部收益作為補償,市場參與者也需要在基金嚴重虧損時承擔超過其出資份額的損失,這削弱了市場參與者對投資失敗的容忍程度(熊維勤,2013)[24]。為避免投資失敗,創業投資機構會將基金的資本投資于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第三,政府引導基金在與創業投資機構約定基金的投資方向時,一般采用量化指標來界定創業期企業,例如規定創業期企業的范圍為成立期限在5年以內、職工人數在300人以下、年銷售額在3000萬元以下、凈資產在2000萬元以下的企業。這種簡單“一刀切”的界定方法沒有準確地體現創業項目的投資周期和投資風險,為創業投資機構迎合政府考核留下了操作空間(楊國超等,2017)[27]。創業投資機構出于自身利益,會在符合界定標準的企業中挑選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
最后,政府官員有動力默許甚至鼓勵創業投資機構采取策略性行為。一方面,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新興產業政策具有追趕的特點,目標是在新興產業領域中盡快培育出優質的企業(江飛濤和李曉萍,2010)[15]。另一方面,我國對政府官員采用“晉升錦標賽”治理制度,政府官員為了盡快獲得提拔,會在5年任期內爭取獲得更好的政績(周黎安,2007)[32]。因此政府官員更傾向扶持可以在短期內顯示成效的項目,而不是長期、高風險的項目。政府官員有動機與創業投資家結成同盟(Shleifer and Vishny,1994)[10],政府官員向創業投資家提供低成本的公共資本,創業投資家則將公共資本投資于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如此一來,政府官員可以收獲短期政績,創業投資家也可以獲得短期投資收益。
綜上,政府引導基金會激勵創業投資機構采取策略性行為迎合政策。創業投資機構會投資創業期企業以通過政府考核,但同時會避免進入長期、高風險的創業項目,因此政府引導基金激勵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地迎合政策,就體現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基金會挑選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據此本文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
H1: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創業投資基金會策略性地投資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
進一步地,創業投資機構的聲譽會影響其采取策略性行為的傾向。其一,低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為了盡快建立聲譽以便順利募集資金,傾向于追求短期業績(Gompers,1996)[4],更愿意投資能在短時間內獲利的項目。其二,低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受資本約束和職業生涯考慮的影響較大,難以容忍投資失敗(Tian and Wang,2011)[11],更偏好投資低風險的項目。其三,高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在市場競爭中享有更大優勢,一旦遭遇處罰將失去多年積累起的聲譽,面臨更高的損失(Atanasov et al.,2012)[1],因而不會輕易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因此,相比高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低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動機更強。據此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H2:相比高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低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更強。
此外,創業投資機構的產權性質也會影響其采取策略性行為的傾向。首先,國有創業投資機構本身就承擔促進創新創業活動的政策任務(叢菲菲和張強,2019;余琰等,2014)[14][30],即使沒有獲得政府引導基金的扶持,投資時也會向政策目標領域傾斜。其次,我國資本市場的運行機制還不健全,民營創業投資機構面臨所有制歧視(盧峰和姚洋,2004)[19],募集資金的難度更高,維持良好業績記錄的壓力更大。最后,國有創業投資機構具有公有產權屬性(吳延兵,2012)[23],管理者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收益較低,承擔的風險和損失較高。因此,相比國有創業投資機構,民營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動機更強。據此本文提出第三個研究假設:
H3:相比國有創業投資機構,民營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更強。
四、實證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境內創業投資機構管理的創業投資基金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清科私募通數據庫。考慮到政府引導基金政策主要是在2005年后開始實施,并且創業投資基金的存續期一般是5年左右,因此選取2005―2015年成立的創業投資基金作為樣本。本文對樣本進行以下處理:(1)為避免運作異常的基金影響回歸結果,剔除沒有管理資本的基金;(2)由于外資基金與本土基金有較大差異,剔除有外資背景的基金;(3)剔除主要數據缺失的基金。最終樣本為957只創業投資基金。為降低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的上下1%進行縮尾 處理。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首先檢驗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是否策略性地迎合政策。由于清科私募通數據庫沒有提供創業投資基金所投企業的詳細數據,因此本文借鑒Cumming(2007)[2]和Cumming and Johan(2009)[3]的做法,用企業的發展階段來刻畫企業的投資周期和投資風險。一般來說,創業初期企業比創業中后期企業有更長的投資周期和更高的投資風險。清科私募通數據庫將企業的發展階段劃分為種子期、初創期、擴張期和成熟期,其中種子期是指企業的產品處于研發階段,初創期是指企業的產品研發完成但尚未大量生產,擴張期是指企業的產品已獲得市場肯定并且進一步發展需要更多資金,成熟期是指企業為上市做準備。基于數據庫對企業發展階段的劃分說明,本文將數據庫的種子期和初創期作為企業的創業期,其中種子期作為企業的創業初期,初創期作為企業的創業中后期。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Ve n表示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創業期企業金額;NewVen表示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創業初期企業金額;OldVen表示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創業中后期企業金額;Guide表示創業投資基金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虛擬變量,當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時取1,否則取0;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參考相關研究的做法,選取基金規模Fund、機構IPO數量IPO、機構年齡Age、機構產權性質State、機構所在地區Area和基金成立年份Year作為控制變量(變量定義見表1)。如果Guide的系數在模型(1)和模型(3)中顯著為正,且在模型(2)中不顯著為正,則說明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會策略性地迎合政策,挑選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
其次檢驗不同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差異。本文參考Lee and Wahal(2004)[6]、王蘭芳和胡悅(2017)[22]的做法,用IPO數量衡量創業投資機構的聲譽,按機構IPO數量是否大于樣本中位數,將樣本分為高聲譽和低聲譽兩組。接著把這兩組樣本分別按模型(1)~(3)進行回歸,就可以比較高聲譽和低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差異。
然后檢驗不同產權性質的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差異。本文根據數據庫提供的創業投資機構簡介,將樣本分為國有性質和民營性質兩組,并把這兩組樣本分別按模型(1)~(3)進行回歸,就可以比較國有和民營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差異。

表1 變量定義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Ven、NewVen和OldVen的中位數均為0,表明我國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投資明顯不足,一半以上的創業投資基金沒有投資過創業期企業。Guide的平均值為0.099,說明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占樣本的9.9%。其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也基本合理。
表3為變量的相關系數。Guide與Ven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Guide與NewVen的相關系數不顯著,Guide與OldVen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符合研究假設。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也基本合理。
表4為變量的均值差異檢驗結果。相比無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樣本,有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樣本Ven和OldVen的均值顯著更大,但NewVen的均值沒有顯著差異,符合研究假設。其他變量的均值差異檢驗結果也基本合理。
(二)政府引導基金參股與創業投資基金投資
表5報告了政府引導基金參股與創業投資基金投資的檢驗結果。研究結果表明,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創業投資基金顯著地增加了創業期企業的投資,但主要是增加創業中后期企業的投資,并沒有顯著地增加創業初期企業的投資。由此可見,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會策略性地迎合政策,挑選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假設1得到驗證。

表3 變量的相關系數

表4 變量的均值差異檢驗
(三)創業投資機構聲譽的影響
表6報告了創業投資機構聲譽影響的檢驗結果。從結果來看,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高聲譽機構管理的基金沒有顯著地增加創業期企業的投資,這說明高聲譽機構本身投資創業期企業的意愿較強,不存在明顯的迎合政策行為,但政府引導基金也沒有對高聲譽機構發揮明顯的激勵作用,沒有引導高聲譽機構進一步增加創業期企業的投資;低聲譽機構管理的基金則顯著地增加了創業期企業的投資,但主要是增加創業中后期企業的投資,并沒有顯著地增加創業初期企業的投資,這說明低聲譽機構會策略性地挑選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存在明顯的迎合政策行為。由此可見,相比高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低聲譽的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更強,假設2得到驗證。

表5 政府引導基金參股與創業投資基金投資

表6 創業投資機構聲譽的影響
(四)創業投資機構產權性質的影響
表7報告了創業投資機構產權性質影響的檢驗結果。由結果可知,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國有機構管理的基金沒有顯著地增加創業期企業的投資,這說明國有機構本身投資創業期企業的意愿較強,不存在明顯的迎合政策行為,但政府引導基金也沒有對國有機構發揮明顯的激勵作用,沒有引導國有機構進一步增加創業期企業的投資;民營機構管理的基金則顯著地增加了創業期企業的投資,但主要是增加創業中后期企業的投資,并沒有顯著地增加創業初期企業的投資,這說明民營機構會策略性地挑選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存在明顯的迎合政策行為。由此可見,相比國有創業投資機構,民營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更強,假設3得到驗證。
六、進一步的討論
(一)政府引導基金參股與創業投資基金投資績效

表7 創業投資機構產權性質的影響
上文的實證結果表明,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只是策略性地投資創業期企業,因此可以推斷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的投資績效會受到不利影響。由于清科私募通數據庫沒有提供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業績數據和清算項目數據,因此本文參考Hochberg et al.(2007)[5]和Zarutskie(2010)[12]的做法,以成功投資比率來衡量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的投資績效,成功投資是指最終以IPO或并購方式退出所投企業。具體地,被解釋變量為成功投資創業期企業金額比率Ven_PS和數量比率Ven_PN、成功投資創業初期企業金額比率NewVen_PS和數量比率NewVen_PN、成功投資創業中后期企業金額比率OldVen_PS和數量比率OldVen_PN。5表8報告了政府引導基金參股與創業投資基金投資績效的檢驗結果。結果表明,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創業初期企業、創業中后期企業的投資績效均出現了輕微下降。由此可見,創業投資機構迎合政策的策略性行為是缺乏效率的,導致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
(二)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三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種方法是替換解釋變量,用參股的政府引導基金數量的對數GuideNum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表9報告了替換解釋變量的檢驗結果,研究結論不變。
第二種方法是替換被解釋變量,用投資創業期企業數量的對數Ve n N、投資創業初期企業數量的對數NewVenN和投資創業中后期企業數量的對數OldVenN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表10報告了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檢驗結果,研究結論不變。

表8 政府引導基金參股與創業投資基金投資績效
第三種方法是增加控制變量,加入創業投資機構累計投資企業數量的對數Inv和并購退出次數的對數MA作為控制變量進行回歸。表11報告了增加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研究結論不變。
(三)內生性問題處理
本文對內生性問題進行以下處理。首先,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基金和其他創業投資基金可能存在特征差異。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把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樣本作為處理組,將按照傾向得分應該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但實際上沒有獲得參股的樣本作為控制組,以此降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特征差異。本文以Fund、IPO、Age、State、Area和Year為協變量,使用Logit模型估計傾向得分,然后在共同取值范圍內進行最近鄰5個樣本匹配。表12報告了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檢驗結果,匹配后各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大幅減少至10%以下,而且都通過了t檢驗,這說明匹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特征已沒有顯著差異。

表9 替換解釋變量

表10 替換被解釋變量
表13報告了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處理效應(ATT)檢驗結果,研究結論保持一致。

表11 增加控制變量

表12 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檢驗

表13 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處理效應
其次,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機構和其他創業投資機構可能原本就存在投資偏好差異。本文將創業投資機構在樣本期是否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虛擬變量EverGuide作為解釋變量,把沒有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基金作為樣本進行回歸,以檢驗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機構與其他創業投資機構是否存在投資偏好差異。表14報告了創業投資機構投資偏好的檢驗結果。從結果來看,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創業投資機構與其他創業投資機構不存在顯著的投資偏好差異,因此上文的回歸結果沒有受到這一問題的嚴重干擾。
最后,創業投資基金可能本來就會避免同時投資創業初期企業和創業中后期企業,上文所說的策略性投資行為可能只是正常的風險控制措施。本文將樣本分為有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和無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兩組,把NewVen與OldVen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以檢驗創業投資基金是否會避免同時投資創業初期企業和創業中后期企業。表15報告了投資創業初期企業和投資創業中后期企業關系的檢驗結果。由結果可知,創業投資基金本身并不會避免同時投資創業初期企業和創業中后期企業,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才出現了明顯的策略性投資行為,因此上文的回歸結果沒有受到這一問題的嚴重干擾。

表14 創業投資機構的投資偏好

表15 投資創業初期企業和投資創業中后期企業的關系
七、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以我國創業投資基金為樣本,實證研究了創業投資機構在政府引導基金激勵下投資創業期企業的動機及經濟后果。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結論:創業投資基金在獲得政府引導基金參股后,會策略性地投資較成熟、較低風險的創業期企業,以迎合政府引導基金政策;相比高聲譽的和國有創業投資機構,低聲譽的和民營創業投資機構策略性迎合政策的傾向更強;創業投資機構迎合政策的策略性行為是低效率的,創業投資基金對創業期企業的投資績效出現了輕微下降。我國設立政府引導基金的本意是激勵創業投資機構投資創業期企業,但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政府引導基金實際上激勵創業投資機構向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進行投資,偏離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本文建議有關部門從以下方面改善政府引導基金的引導效果:第一,強化政府引導基金的政策性定位,充分發揮政府引導基金彌補市場失靈和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功能,重點扶持長期、高風險的創業項目,避免進入短期、低風險的創業項目;第二,適當降低政府引導基金的杠桿放大要求,加大風險補償的扶持力度,緩解公共資金與市場配比資金的利益沖突,確保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方向符合政策目標;第三,優化政府引導基金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減輕政府引導基金的短期保值增值壓力,建立容錯機制,提高公共資金承擔風險的能力;第四,細化政府引導基金的扶持范圍,根據創業項目的投資周期和投資風險制定扶持標準,避免采用簡單“一刀切”的方法界定扶持對象,減少創業投資機構鉆空子的機會;第五,完善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體制,建立政府引導基金長效運行機制,重點考核公共資金的長期社會效益,消除短期化傾向。
注釋
1.政府引導基金在狹義上一般是指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廣義上還包括政府產業發展引導基金、政府基礎設施建設引導基金等。本文使用政府引導基金的狹義定義。
2.數據來源為《中國創業投資發展報告2019》第107頁,經濟管理出版社,2019年。
3.參見馮櫻子. 9.6萬億政府引導基金也缺錢 “交作業式”投資效果難保證[N]. 華夏時報, 2018-06-29. 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78159.html.
4.我國創業投資機構的投資項目約66%位于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數據來源為《中國創業投資發展報告2019》第65頁,經濟管理出版社,2019年。
5.成功投資創業期企業金額比率是指成功投資創業期企業金額與投資創業期企業總金額之比,若沒有投資創業期企業則該指標為缺失值。其他指標采用類似計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