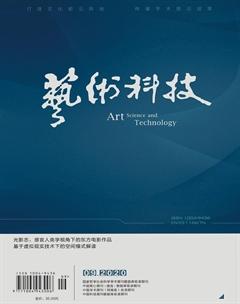近代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之日本因素
于越 王蓮
摘 要:20世紀(jì)上半葉是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的新時(shí)代。隨著西學(xué)東漸與中國(guó)近代史學(xué)之牽引、新式美術(shù)教育興起等各因素的推動(dòng),中國(guó)的美術(shù)史研究無(wú)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和西方藝術(shù)思想的影響,在美術(shù)史分期、美術(shù)史觀、寫(xiě)作方法及編撰體例等方面都發(fā)生了劃時(shí)代的重大改變,從而使具有現(xiàn)代形態(tài)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得以確立。本文從日本學(xué)者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論著角度入手,以姜丹書(shū)的《美術(shù)史》和潘天壽的《中國(guó)繪畫(huà)史》為例,探析近代中國(guó)美術(shù)史理論研究成果的日本因素。
關(guān)鍵詞: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日本因素;姜丹書(shū);潘天壽
中圖分類(lèi)號(hào):J120.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9436(2020)09-00-04
20世紀(jì)上半葉,中國(guó)掀起了“西學(xué)東漸”的熱潮,大批學(xué)者奔赴日本和歐美各國(guó)學(xué)習(xí)并向國(guó)內(nèi)引介西方的藝術(shù)思想和文化。1868年,日本采取了“明治維新”新政策,除了在政治、經(jīng)濟(jì)等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果,藝術(shù)文化上吸收和兼容西方藝術(shù)思想及研究方法也有了重大的進(jìn)展,并且中日兩國(guó)是一衣帶水的鄰邦,近代中國(guó)的有識(shí)之士赴日本學(xué)習(xí)較歐美更加方便容易,因此日本成了中國(guó)間接吸收西方學(xué)術(shù)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橋梁,中國(guó)的美術(shù)史學(xué)研究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實(shí)現(xiàn)了由傳統(tǒng)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形態(tài)的轉(zhuǎn)型。姜丹書(shū)、潘天壽、鄭午昌、史巖、俞劍華等諸多美術(shù)史研究先行者直接或間接受到了日本和西方近代學(xué)術(shù)思想和理論觀念的影響,撰寫(xiě)了《美術(shù)史》《中國(guó)繪畫(huà)史》等美術(shù)史論著,開(kāi)啟了美術(shù)史研究的新紀(jì)元,為我國(guó)現(xiàn)代形態(tài)的美術(shù)學(xué)科的建立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然而20世紀(jì)上半葉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轉(zhuǎn)型經(jīng)歷了一個(gè)吸收、融合和開(kāi)拓創(chuàng)新的坎坷過(guò)程。本文從日本學(xué)者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論著角度入手,對(duì)姜丹書(shū)的《美術(shù)史》和潘天壽的《中國(guó)繪畫(huà)史》進(jìn)行考察、梳理,探析日本學(xué)者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理論研究成果對(duì)其的影響。
1 日本學(xué)者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成果
20世紀(jì)以來(lái),很多日本學(xué)者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文章及著作通過(guò)“西學(xué)東漸”得以被譯介到國(guó)內(nèi),如日本學(xué)者大村西崖1901年編寫(xiě)的《東洋美術(shù)小史》,1913年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繪畫(huà)史》等等,這些研究成果開(kāi)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研究之先河,對(duì)之后美術(shù)史學(xué)科在我國(guó)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揭開(kāi)日本學(xué)者對(duì)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研究序幕的當(dāng)屬1901年大村西崖(1867—1927)撰寫(xiě)的《東洋美術(shù)史》。該書(shū)卷帙浩繁,其內(nèi)容涵蓋中國(guó)、日本和印度。當(dāng)時(shí)的天津南開(kāi)大學(xué)秘書(shū)陳彬和翻譯了此書(shū)的中國(guó)部分,他認(rèn)為“雖非全璧,而實(shí)全書(shū)精神之所寄”。[1]后作為第一部中國(guó)美術(shù)通史著作《中國(guó)美術(shù)史》在國(guó)內(nèi)流傳,而在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外還沒(méi)有如此內(nèi)容豐富、體例完備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說(shuō)這不僅是20世紀(jì)初日本學(xué)者研究中國(guó)美術(shù)史的第一份成果,在歷史上亦是第一份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開(kāi)拓性研究。
當(dāng)時(shí)第一批研究中國(guó)美術(shù)史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學(xué)者還有內(nèi)藤湖南(1866—1934),他撰寫(xiě)的《支那繪畫(huà)史》于1938年由東京弘文堂書(shū)房出版。從美術(shù)史的角度通覽全書(shū),該書(shū)與大村西崖的《東洋美術(shù)史》相比,繪畫(huà)史方面的立論更加具體和深入。內(nèi)藤湖南在中國(guó)繪畫(huà)史研究方面采取了形式分析與風(fēng)格分析相結(jié)合的方法,以此考證中國(guó)繪畫(huà)史上有爭(zhēng)議的作品。這種方法在今天看來(lái)仍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由于近代中國(guó)國(guó)情處于危急時(shí)刻,中國(guó)學(xué)者羅振玉逃亡到日本并將中國(guó)繪畫(huà)作品帶到日本,其中部分畫(huà)作為贗品。而當(dāng)時(shí)內(nèi)藤湖南與羅振玉交往深厚,在繪畫(huà)收藏方面亦受其影響,因此在《支那繪畫(huà)史》中不免有魚(yú)目混珠的中國(guó)繪畫(huà)作品插圖。這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日本美術(shù)界對(duì)于中國(guó)繪畫(huà)作品的認(rèn)識(shí)和鑒賞產(chǎn)生了較大的負(fù)面影響,同時(shí)也導(dǎo)致日本藝術(shù)家對(duì)中國(guó)繪畫(huà)作品的理解有些偏頗,但在一定程度上亦拓寬了當(dāng)時(shí)日本美術(shù)界對(duì)于中國(guó)繪畫(huà)的視野。因此,即使在內(nèi)藤湖南的《支那繪畫(huà)史》之前已有不少美術(shù)史著作問(wèn)世,日本美術(shù)界亦認(rèn)為“《支那繪畫(huà)史》是近代日本自己撰寫(xiě)的第一本專(zhuān)著”。[2]
還有一部不得不提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著作,即中村不折(1868—1943)、小鹿青云的《支那繪畫(huà)史》。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二人出于研究日本繪畫(huà)必須先從研究中國(guó)繪畫(huà)開(kāi)始的原因,撰寫(xiě)了這部以中國(guó)繪畫(huà)史冠名的著作。而他們?cè)诰帉?xiě)過(guò)程中僅僅參閱了中國(guó)美術(shù)史一類(lèi)的書(shū)籍大致二十七八頁(yè),因此該書(shū)的原創(chuàng)性與同期論著相比較高。總體而言,全書(shū)平穩(wěn)地論述了中國(guó)美術(shù)史、繪畫(huà)史的起源與發(fā)展。這種重描述、輕闡釋的論述方式雖然思辨性不強(qiáng),但提綱挈領(lǐng)。后傳入中國(guó),并在國(guó)內(nèi)掀起了第一波美術(shù)史研究熱潮,姜丹書(shū)、陳師曾、潘天壽等眾多中國(guó)美術(shù)史家亦受其影響,他們的美術(shù)史、繪畫(huà)史著述中的日本因素俯拾即是。
2 姜丹書(shū)《美術(shù)史》中的日本因素
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中國(guó)具有現(xiàn)代形態(tài)的美術(shù)教育事業(yè)剛剛起步,教材編寫(xiě)主要集中于譯介日本及西方學(xué)者的外來(lái)美術(shù)史論研究成果和整理中國(guó)古代傳統(tǒng)繪畫(huà)史知識(shí),后經(jīng)過(guò)我國(guó)教育家及美術(shù)史學(xué)家刻苦鉆研,具有中國(guó)文化特色的美術(shù)史教材亦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中。
姜丹書(shū)(1885—1962)曾就讀于兩江師范學(xué)堂,由于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師資力量不足,圖畫(huà)手工科等美術(shù)專(zhuān)業(yè)課教師皆是日本藉,所以即使姜丹書(shū)不像同時(shí)期的其他學(xué)者一樣有留學(xué)日本的經(jīng)歷,他所受的教育亦是較為正統(tǒng)的日本美術(shù)教育,而當(dāng)時(shí)處于明治維新時(shí)期的日本藝術(shù)文化思想主要來(lái)自西方,這些因素在他的《美術(shù)史》中皆有所體現(xiàn)。作為近代以來(lái)我國(guó)學(xué)者中美術(shù)史研究的第一人,姜丹書(shū)從事藝術(shù)教育50余年,著述豐碩,如《美術(shù)史》《美術(shù)史參考書(shū)》《藝用解剖學(xué)》等都是國(guó)內(nèi)當(dāng)時(shí)最早的美術(shù)史書(shū)籍。
出于教學(xué)所需,姜丹書(shū)在1917年撰寫(xiě)并出版了《美術(shù)史》,這部專(zhuān)著解決了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美術(shù)史教材短缺的燃眉之急。《美術(shù)史》在編寫(xiě)體例上相比傳統(tǒng)美術(shù)史有了巨大的進(jìn)步,擺脫了歷史的窠臼,不再是簡(jiǎn)單的史料堆砌和局限于對(duì)書(shū)畫(huà)作品的整理,而是包括建筑、雕刻、印章等多個(gè)藝術(shù)門(mén)類(lèi)。姜丹書(shū)從宏觀角度編寫(xiě)了《美術(shù)史》,全書(shū)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以中國(guó)為主的東洋美術(shù)史,按照藝術(shù)門(mén)類(lèi)劃分成建筑、雕刻、繪畫(huà)、工藝美術(shù)共4章;下篇是西洋美術(shù)史,按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分為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3個(gè)歷史時(shí)期,這顯然是姜丹書(shū)受日本學(xué)者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方法——三段分期法的影響。
總的來(lái)說(shuō),《美術(shù)史》將世界美術(shù)一分為二,內(nèi)容繁多龐雜,雖然這本書(shū)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創(chuàng)新,但還不能稱(chēng)為美術(shù)史研究專(zhuān)著,實(shí)為新興美術(shù)教育發(fā)展的產(chǎn)物。不可否認(rèn)的是,在西方藝術(shù)思想理論和日本治史方法的指引下,姜丹書(shū)尚能脫離傳統(tǒng)史學(xué)方法的困境,撰寫(xiě)出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美術(shù)史》。20世紀(jì)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在新式美術(shù)教育事業(yè)的推動(dòng)下開(kāi)始進(jìn)行,《美術(shù)史》作為國(guó)內(nèi)第一部美術(shù)史教材,填補(bǔ)了國(guó)內(nèi)美術(shù)教學(xué)教材的空白,亦為當(dāng)時(shí)的美術(shù)教育家和美術(shù)史家?guī)?lái)了一個(gè)全新的視角,對(duì)后來(lái)潘天壽《中國(guó)繪畫(huà)史》、滕固《中國(guó)美術(shù)小史》、鄭午昌《中國(guó)畫(huà)學(xué)全史》等美術(shù)史研究著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dǎo)作用,使近代中國(guó)美術(shù)史論研究有了質(zhì)的飛躍。姜丹書(shū)對(duì)近代中國(guó)的美術(shù)史學(xué)科建設(shè)可謂有開(kāi)天辟地之功。
3 潘天壽《中國(guó)繪畫(huà)史》中的日本因素
近代日本和西方的美術(shù)思想及理論雖然極大地推動(dòng)了我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的發(fā)展,但是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文化也因此受到了沖擊。在這個(gè)中西文化藝術(shù)產(chǎn)生碰撞的時(shí)代,為了在汲取引進(jìn)西方及日本的藝術(shù)文化思想精華的同時(shí)也能讓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自立,中國(guó)美術(shù)教育家潘天壽(1897—1971)于1925年編寫(xiě)了《中國(guó)繪畫(huà)史》。潘天壽的《中國(guó)繪畫(huà)史》論述了從三皇五帝至清代的繪畫(huà)史,綱目清晰,亦受進(jìn)化論觀念的影響,因此可以說(shuō)潘天壽的史學(xué)觀念與時(shí)代思潮密切相關(guān),所著的《中國(guó)繪畫(huà)史》是一部緊貼時(shí)代的美術(shù)史著作。
由于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國(guó)情所處的劣勢(shì),日本學(xué)者在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首開(kāi)研究之先河,且國(guó)內(nèi)沒(méi)有編寫(xiě)現(xiàn)代意義上的美術(shù)史論的先例,因此潘天壽只能參考和借鑒日本已有的美術(shù)史理論和成果。正如潘公凱在1983年重版時(shí)的“序言”中所說(shuō):“先父潘天壽當(dāng)時(shí)由于國(guó)內(nèi)缺少系統(tǒng)的美術(shù)史教材,參酌了《佩文齋書(shū)畫(huà)譜》和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繪畫(huà)史》,以黃賓虹、鄧實(shí)的《美術(shù)叢書(shū)》為輔,綜合整理了數(shù)百種中國(guó)古代美術(shù)史料編寫(xiě)出這本美術(shù)史論著。”[3]
潘天壽的《中國(guó)繪畫(huà)史》緒論和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繪畫(huà)史》緒論有不少相似之處,兩部著作皆從文化發(fā)育說(shuō)起,西方為意大利半島,東方則為中國(guó),整體篇幅以敘述中國(guó)繪畫(huà)變遷史為主,雖然潘著的緒論有明顯承襲《支那繪畫(huà)史》緒論的痕跡,但是潘著的緒論對(duì)中國(guó)繪畫(huà)史的梳理更加清晰明了,亦不乏自己的體悟和見(jiàn)地。從美術(shù)史觀來(lái)看,潘天壽在《中國(guó)繪畫(huà)史》中采取的分期方法亦參酌了中村不折、小鹿青云《支那繪畫(huà)史》的三段分期法,二者都是劃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稍有不同的是潘天壽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支那繪畫(huà)史》“上世史”一章中的古代繪畫(huà)加入了自己的見(jiàn)地,另成一章古代史,內(nèi)容包括繪畫(huà)的起源、夏至秦等中國(guó)古代王朝的繪畫(huà)。雖然兩部著作涉及的朝代范圍相同,但潘天壽對(duì)部分章節(jié)進(jìn)行了改動(dòng),并為每個(gè)朝代加上了其特有的畫(huà)論,如此既避免了《支那繪畫(huà)史》內(nèi)容稍顯簡(jiǎn)單的弊端,亦能脈絡(luò)清晰地闡述整個(gè)中國(guó)繪畫(huà)史的發(fā)展,體現(xiàn)出潘天壽對(duì)繪畫(huà)史獨(dú)具匠心的見(jiàn)解和擘肌分理的精神。此外,潘天壽并未拘泥于研究美術(shù)品與同時(shí)代其他文化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而是放寬視野,對(duì)域外美術(shù)與本土美術(shù)相交融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在《中國(guó)繪畫(huà)史》之附文《域外繪畫(huà)流入中土考略》中通過(guò)對(duì)中西方繪畫(huà)交流的考察與梳理,別出心裁地將域外繪畫(huà)傳入中國(guó)分為4個(gè)時(shí)期來(lái)敘述,探究中西方繪畫(huà)不同的深層原因。這是在《支那繪畫(huà)史》之外的突破與創(chuàng)新。
整體來(lái)看,《中國(guó)繪畫(huà)史》在敘述體例、時(shí)期劃分、理論框架等方面具有進(jìn)化論史觀以及參照借鑒日本研究成果的性質(zhì)與特征。因?yàn)楫?dāng)時(shí)處在20世紀(jì)上半葉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階段,引進(jìn)與借鑒西方、日本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論著是歷史的必然趨勢(shì)。潘天壽在棄言中早已明說(shuō)是“學(xué)習(xí)繪畫(huà)史,而不是寫(xiě)繪畫(huà)史”。即使這部繪畫(huà)史著作在體例、內(nèi)容等方面沿襲了日本學(xué)者中國(guó)美術(shù)史的史學(xué)觀點(diǎn)和著史方法,但我們?nèi)匀荒軓闹锌闯雠颂靿奂词故窃谖鞣健⑷毡镜乃囆g(shù)思想文化涌入中國(guó)時(shí)也始終保持清醒,將中國(guó)美術(shù)放眼于世界藝術(shù)大環(huán)境之中,并以進(jìn)化論的觀點(diǎn)來(lái)統(tǒng)觀與理解中國(guó)整個(gè)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對(duì)民族文化作出了理性判斷和繼承發(fā)揚(yáng),同時(shí)系統(tǒng)分析了中西方兩種文化,并將他們合理地區(qū)分開(kāi)來(lái)。
因此,從潘天壽的《中國(guó)繪畫(huà)史》我們可以洞悉,他的美術(shù)史學(xué)觀念和著史思想遵循了與時(shí)俱進(jìn)的時(shí)代特點(diǎn),并且始終以民族傳統(tǒng)為基礎(chǔ),尋求藝術(shù)理論中的民族精神。更為可貴的是,他在借鑒、學(xué)習(xí),取各家所長(zhǎng)時(shí)加入了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的研究,能獨(dú)立思考、發(fā)現(xiàn)新的問(wèn)題,既提高了國(guó)內(nèi)美術(shù)史研究成果的高度,也保持了我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自身的特點(diǎn)。潘天壽所處的時(shí)代正是中西方藝術(shù)文化發(fā)生碰撞的時(shí)代,在出現(xiàn)有人主張全盤(pán)西化而有人盲目排外的兩極分化現(xiàn)象時(shí),他既不保守也不冒進(jìn),不僅在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上邁出了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一步,也捍衛(wèi)了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理論,在我國(guó)美術(shù)理論研究史的長(zhǎng)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4 結(jié)語(yǔ)
20世紀(jì)初期,外來(lái)文化與我們本土的文化因“西學(xué)東漸”產(chǎn)生了碰撞與火花,一時(shí)間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的局面。當(dāng)時(shí)日本學(xué)者對(duì)中國(guó)美術(shù)史的研究在時(shí)間上領(lǐng)先于中國(guó),因此中國(guó)學(xué)者對(duì)美術(shù)史的研究著述多有編譯日本研究成果的性質(zhì)。即使如此,在日本及西方學(xué)者關(guān)于中國(guó)美術(shù)史學(xué)理論研究的帶動(dòng)和啟發(fā)下,我國(guó)學(xué)者在中國(guó)美術(shù)史的研究上掙脫了傳統(tǒng)形態(tài)美術(shù)史觀的桎梏,邁出了走向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研究關(guān)鍵性的一步。在20世紀(jì)研究中國(guó)美術(shù)史的道路上,這些美術(shù)史學(xué)家開(kāi)拓創(chuàng)新、銳意進(jìn)取,用現(xiàn)代化的目光并結(jié)合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的特點(diǎn),重新審視了中國(guó)美術(shù)史,運(yùn)用新的史學(xué)思想表達(dá)文化內(nèi)涵,在中國(guó)美術(shù)史理論的研究方面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參考文獻(xiàn):
[1] 陳輔國(guó).諸家中國(guó)美術(shù)史著選匯[M].長(zhǎng)春:吉林美術(shù)出版社,1992:688.
[2] 古原宏伸.日本近八十年來(lái)的中國(guó)繪畫(huà)史研究[J].新美術(shù),1994(1):69.
[3] 潘天壽.中國(guó)繪畫(huà)史[M].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3:1.
作者簡(jiǎn)介:于越(1999—),女,江蘇鹽城人,揚(yáng)州大學(xué)本科在讀,研究方向:近代日本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及影響。
王蓮(1972—),女,江蘇揚(yáng)州人,博士,留美博士后,揚(yáng)州大學(xué)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教授,研究方向:近代日本的中國(guó)美術(shù)史研究及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