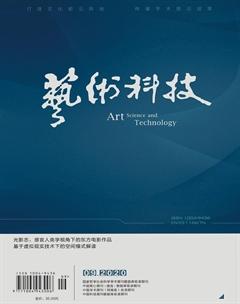論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
摘 要:少數(shù)民族群眾居住的地區(qū)充滿了濃郁的民族特色,這與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習(xí)慣法具有緊密的關(guān)系。在這些民族習(xí)慣法中,樸素的生態(tài)觀、民族禁忌、生態(tài)習(xí)俗和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對(duì)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對(du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少數(shù)民族村寨的旅游開發(fā)今后應(yīng)積極吸收民族習(xí)慣法的有益成分,以實(shí)現(xiàn)對(duì)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
關(guān)鍵詞: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民族習(xí)慣法;保護(hù)
中圖分類號(hào):TU982.2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9436(2020)09-0-04
0 引言
隨著脫貧攻堅(jiān)的深入推進(jìn),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實(shí)現(xiàn)了巨大發(fā)展,生產(chǎn)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呈現(xiàn)了新的狀態(tài)。然而,在這種新狀態(tài)之下,一些傳統(tǒng)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其中,村寨景觀作為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發(fā)生了明顯的改變。例如一些地方進(jìn)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大面積種植油茶等經(jīng)濟(jì)作物,使得原有的梯田、梯土景觀不再顯露,對(duì)鄉(xiāng)村風(fēng)貌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再如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展以磚瓦房為主的民居改造,對(duì)傳統(tǒng)民居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因此,應(yīng)該協(xié)調(diào)、兼顧少數(shù)民族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村寨景觀保護(hù),這樣既能夠提升少數(shù)民族生產(chǎn)生活水平,又能夠保護(hù)一些好的傳統(tǒng)景觀。
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屬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一部分,而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改變可能就是生態(tài)環(huán)境被破壞。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本文著眼于對(duì)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通過探尋苗、侗族村寨景觀的變化,發(fā)現(xiàn)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與其民族習(xí)慣法有重要的聯(lián)系,提出對(duì)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應(yīng)重點(diǎn)挖掘民族習(xí)慣法。
1 民族習(xí)慣法對(duì)村寨景觀的影響
挖掘發(fā)揮民族習(xí)慣法對(duì)保護(hù)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價(jià)值,必須先認(rèn)識(shí)民族習(xí)慣法是如何影響村寨景觀的。通過對(duì)苗、侗族習(xí)慣法的分類考察,發(fā)現(xiàn)民族習(xí)慣法主要是從樸素的生態(tài)觀、民族禁忌、生態(tài)習(xí)俗和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4個(gè)方面對(duì)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形成產(chǎn)生影響。
1.1 民族樸素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觀念,愛護(hù)自然
少數(shù)民族向來有愛護(hù)自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觀念,這種生態(tài)保護(hù)觀念具有一定的原生性特點(diǎn)。可以說,少數(shù)民族愛護(hù)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是源于一種樸素的生態(tài)觀。
一方面,少數(shù)民族的環(huán)保觀念是民族內(nèi)產(chǎn)生的,不具有外來性,這樣的特點(diǎn)使民族習(xí)慣法更加重視解決身邊的問題。如村寨周圍的大樹、流經(jīng)村寨的溪河,這些與少數(shù)民族生活緊密相關(guān)的自然環(huán)境便因此受到重視、得到保護(hù)。而且其立足于現(xiàn)實(shí)的實(shí)際需要,更具有可操作性,不會(huì)出現(xiàn)不適應(yīng)的問題。
另一方面,其環(huán)保觀點(diǎn)不是像現(xiàn)代環(huán)保觀念那樣系統(tǒng)而充滿人文價(jià)值,而是比較注重風(fēng)水這樣的民間認(rèn)同。少數(shù)民族非常看重風(fēng)水,認(rèn)為一個(gè)地方或家族人員的興衰與自然環(huán)境如山川走勢(shì)、水流豐盈及林木繁茂休戚相關(guān),因此他們會(huì)特別注重居住區(qū)域的風(fēng)水狀況。如在貴州黔東南,走進(jìn)苗族村寨,會(huì)最先看到的生長(zhǎng)在村寨周邊長(zhǎng)勢(shì)茂盛的保寨樹,這些保寨樹一般立在寨前或寨后的山坳上,守衛(wèi)著苗寨,且具有一定的年齡。[1]還有一些相似的情景,比如貴州銅仁的一些苗族村寨被古樹環(huán)繞,也是源于風(fēng)水觀念,這些古樹作為保寨樹被賦予了庇護(hù)村寨的功能。
另外,少數(shù)民族人民還具有樸素的生態(tài)保護(hù)觀念,并把這種觀念融入生產(chǎn)生活。比如在貴州銅仁,少數(shù)民族喜歡在田坎和土坎上種植杉樹、油茶樹或者油桐樹。一方面,種植這些樹能夠起到“保坎”的作用,防止過度耕作帶來的水土流失或者垮坎問題,從客觀上形成了“保土生木”的生態(tài)保護(hù)模式;另一方面,通過種植杉樹、油茶樹和油桐樹這類經(jīng)濟(jì)林木也可獲取一定的經(jīng)濟(jì)效益,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增收。可以說,這樣的樸素生態(tài)觀念也具有現(xiàn)代的環(huán)保價(jià)值。
1.2 民族禁忌,敬畏自然
民族習(xí)慣法中包含民族禁忌的內(nèi)容,在許多少數(shù)民族生活的區(qū)域都流傳著古老的關(guān)于“神山”“神樹”“洞神”和“龍脈”的故事。民族禁忌雖具有迷信色彩,但卻在民族區(qū)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如古樹往往被賦予“神樹”的角色,少數(shù)民族群眾相信,一棵樹得以如此久遠(yuǎn)地存在,并且保持枝繁葉茂,是得到了神的護(hù)佑。因此“神樹”被賦予了美好愿望,人們希望通過“神樹”實(shí)現(xiàn)與神靈的對(duì)話,祈求神靈的保佑,借此神化作用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古樹的保護(hù)。
再如在貴州的廣大區(qū)域,具有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溶洞,少數(shù)民族在這樣的自然背景下,形成了溶洞保護(hù)的民族禁忌,“洞神”就是其中之一。在少數(shù)民族看來,“洞神”的存在形式表現(xiàn)為溶洞里面有動(dòng)物寄住,如蛇、蝙蝠和鳥等就是判別“洞神”的指標(biāo),只要洞中有飛鳥出入,溶洞便被賦予神秘色彩,人們不會(huì)貿(mào)然入洞,由此,溶洞里面的鐘乳石和地下水資源得到了較好的保護(hù)。
此外,少數(shù)民族還信奉龍的存在,如苗族就相信龍存在于山體之間,山脈走勢(shì)就是龍脈的形態(tài)。在這樣的認(rèn)識(shí)下,少數(shù)民族極力保護(hù)每一座山體的完整性,不會(huì)破壞山上的林木,認(rèn)為那是龍的胡須,也不會(huì)采挖山上的石頭,認(rèn)為那是龍的鱗片,這樣就保護(hù)了山體,減少了砂石開采和林木破壞。如此種種,都是源于少數(shù)民族對(duì)自然的敬畏之心。正是這種敬畏,使得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得到了較好的保護(hù)。
1.3 生態(tài)習(xí)俗傳承,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
民族習(xí)慣法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并不僅僅停留在帶有迷信色彩的風(fēng)水觀念和民族禁忌上,其在習(xí)俗的傳承過程中也可以見到環(huán)境保護(hù)的蹤跡。這種環(huán)境保護(hù)習(xí)俗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是順應(yīng)時(shí)令的環(huán)境保護(hù)習(xí)俗。比如在貴州的黔東南和銅仁等地,就流傳著“正月栽竹,二月栽木”的民諺,指導(dǎo)人們?cè)谶m當(dāng)?shù)募竟?jié)植樹。另外,生活在貴州銅仁的苗族和侗族,至今保留著封山育林的習(xí)俗,當(dāng)?shù)厝怂追Q“封山”“開山”。“封山”即在每年的農(nóng)歷二月在進(jìn)入山林的必經(jīng)路口舉行儀式(如放鞭炮,請(qǐng)“先生”作法等),宣告從即日起不準(zhǔn)進(jìn)入山林伐木、放牧等,如需伐木用作其他,則必須向村集體申請(qǐng),否則將對(duì)違反者按偷盜林木予以處罰,或“挑谷子”,或進(jìn)行一定的“金錢罰”。“開山”即在每年的農(nóng)歷十二月在進(jìn)入山林的必經(jīng)路口舉行儀式,宣告從即日起人們可以進(jìn)山取薪或伐木作為它用。這樣的習(xí)俗順應(yīng)了萬物生長(zhǎng)的時(shí)令規(guī)律,既保護(hù)了生態(tài)環(huán)境,也使人們有所取,實(shí)現(xiàn)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及社會(huì)的變遷,封山育林的習(xí)俗變成了約定俗成的形式,正在發(fā)揮作用,沒有了傳統(tǒng)儀式的參與。同時(shí),電器的使用也使人們減少了進(jìn)入山林的取薪機(jī)會(huì),因此這些地方的森林資源得到了更好的保護(hù)。
二是伴隨著人生老病死的習(xí)俗。民族習(xí)慣法中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有時(shí)會(huì)與人生老病死的習(xí)俗聯(lián)系起來。如在貴州黔東南州的錦屏縣,存在著栽種“十八杉”的習(xí)俗,即當(dāng)孩子降臨世間時(shí),家人就在自家山坡上為之栽上一片杉樹,并加以細(xì)心養(yǎng)護(hù)管理,一直到孩子滿18歲以后成婚時(shí),姑娘便用“十八杉”做嫁妝,男子便用“十八杉”建吊腳樓。[1]此外,還有在過世的親人墳前栽樹、緬懷親人的習(xí)俗。所栽之樹,以柏樹為多,這在客觀上促進(jìn)了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可見,少數(shù)民族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貫穿生死,涵蓋了生活中的各個(gè)方面。
1.4 明確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間接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
民族習(xí)慣法中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歸屬具有很強(qiáng)的觀念,形成了間接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秩序。如苗族把林木分為風(fēng)景林、用材林和薪炭林,用材林又可分為“責(zé)任山”和“公山”,村民在“公山”被封山期間,可以修剪“責(zé)任山”的樹枝作為燃料。[2]在這里就對(duì)山林的權(quán)屬進(jìn)行了集體與個(gè)人的劃分,使得苗族民眾在伐薪時(shí)知道哪些山林可以砍、哪些山林不可以砍以及在何時(shí)才能砍,從而形成了良好的秩序,以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
另外,在貴州省銅仁市的一些苗族村寨,還用林木來區(qū)分土地、林木的權(quán)屬情況。如在兩片不同承包土地之間栽一棵樹,用于區(qū)分兩片承包土地的范圍,也可約定兩片承包山林由一棵樹為劃分界限。這種用來確定權(quán)屬范圍的樹俗稱“在記”,而且這種“在記樹”任何人都不得砍取,就算今后需要砍取,也需由兩家共同處置分配,同時(shí)在年長(zhǎng)者的見證下在原處重新種上一棵樹或者重新確定一棵相同界限上的樹作為新的界限。這樣對(duì)林木權(quán)屬的劃分,或者用于權(quán)屬區(qū)分的界限,間接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尤其是在土地保護(hù)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生態(tài)保護(hù)格局。
2 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
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是民族的瑰寶,更是國(guó)家的財(cái)富。時(shí)代的演進(jìn)不應(yīng)丟棄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之間,溝通、對(duì)話、協(xié)調(diào)才是應(yīng)有的價(jià)值取向,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亦是如此。
2.1 協(xié)調(diào)國(guó)家法與民族習(xí)慣法的關(guān)系
在現(xiàn)代法治背景下,法律的成文化要求使得民族習(xí)慣法難以融入國(guó)家的治理體系。如果我們站在法學(xué)的視角來審視,就會(huì)發(fā)現(xiàn),現(xiàn)今國(guó)家法有相當(dāng)一部分具有外源性特征,尤其是運(yùn)用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時(shí),極有可能出現(xiàn)不適應(yīng)的問題,因而很難得到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認(rèn)同。在這種情況下,協(xié)調(diào)好國(guó)家法與民族習(xí)慣法之間的關(guān)系,才是上述問題的解決之道。那么應(yīng)該如何協(xié)調(diào)二者的關(guān)系呢?在本文看來,對(duì)存在特定習(xí)慣法的領(lǐng)域,國(guó)家法應(yīng)該保持克制,盡可能減少干預(yù),并為其存在和發(fā)展留出足夠的空間。[3]就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而言,應(yīng)充分尊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景觀空間布局,保持民族風(fēng)格。同時(shí),產(chǎn)業(yè)發(fā)展也應(yīng)具有民族特色,不可“一刀切”。
2.2 發(fā)揮新型民族習(xí)慣法村規(guī)民約的價(jià)值
新型村規(guī)民約是民族習(xí)慣法的表現(xiàn)形式。[4]雖然民族習(xí)慣法具有不成文的特點(diǎn),但是卻能通過村規(guī)民約的形式將民族習(xí)慣法固定下來。而且,經(jīng)過村規(guī)民約固定的民族習(xí)慣法,更能夠?yàn)樯贁?shù)群眾所認(rèn)同。在苗、侗族地區(qū),村規(guī)民約對(duì)民族習(xí)慣法的傳承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說,村規(guī)民約已經(jīng)成為民族習(xí)慣法的當(dāng)代表現(xiàn)形式。
縱觀民族習(xí)慣法的內(nèi)容,可以發(fā)現(xiàn)村規(guī)民約中不乏環(huán)境保護(hù)方面的規(guī)定。例如一些地方的村規(guī)民約對(duì)村居衛(wèi)生和生態(tài)資源保護(hù)進(jìn)行了規(guī)定,對(duì)美化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起到了積極作用。可見,在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保護(hù)上,村規(guī)民約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必須最大限度地發(fā)揮村規(guī)民約的價(jià)值。另外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村規(guī)民約對(duì)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還有待強(qiáng)化。僅僅從村居衛(wèi)生和生態(tài)資源方面保護(hù)村寨景觀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考慮到村寨景觀的整體性,在村規(guī)民約中加入村居規(guī)劃和村寨文化保護(hù)方面的規(guī)定,也尤為重要。
2.3 突顯鄉(xiāng)土法杰在基層環(huán)境治理中的作用
民族習(xí)慣法要發(fā)揮保護(hù)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作用,不僅需要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心理認(rèn)同,也需要具有權(quán)威的鄉(xiāng)土法杰的積極推動(dòng)。鄉(xiāng)土法杰對(duì)習(xí)慣法的傳承和實(shí)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傳統(tǒng)社會(huì)下,鄉(xiāng)土法杰更多是在調(diào)解民間糾紛中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在苗、侗族村寨,“寨老”“榔頭”的職責(zé)就是民間調(diào)解和宣傳習(xí)慣法。在當(dāng)代,“寨老”“榔頭”隨著年歲的變遷已經(jīng)逐漸減少,或者經(jīng)過選舉、任命等形式,轉(zhuǎn)化成了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治理者、參與者。但是稱呼的轉(zhuǎn)換并未對(duì)作用的發(fā)揮產(chǎn)生影響,反而提高了鄉(xiāng)土法杰在基層社會(huì)治理中的重要性。
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鄉(xiāng)土法杰對(duì)村寨景觀的保護(hù)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在少數(shù)民族村寨發(fā)展鄉(xiāng)村旅游的過程中,需要對(duì)村寨景觀進(jìn)行相應(yīng)的改造,這個(gè)時(shí)候,鄉(xiāng)土法杰的決策就可能決定村寨景觀的命運(yùn)。因此突出鄉(xiāng)土法杰在環(huán)境保護(hù)、治理中的作用,提升鄉(xiāng)土法杰的治理才能,是當(dāng)務(wù)之急。少數(shù)民族村寨發(fā)展鄉(xiāng)村旅游,除了要優(yōu)化基礎(chǔ)設(shè)施、提升旅游硬件水平外,保護(hù)好現(xiàn)有的村寨景觀,能夠在無形中提升鄉(xiāng)村旅游的軟件能力。
3 結(jié)語
民族的亦是世界的。少數(shù)民族村寨景觀的保護(hù)不僅需要技術(shù)手段的支持,更需要本土源泉的供養(yǎng)。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治國(guó)家,使法治貫穿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需要國(guó)家層面法律的制定和實(shí)施,更需要本土的供給。這是國(guó)家治理多元化的要求,也是葆有民族性的中國(guó)需要。中國(guó)是一個(gè)多民族的大家庭,其中民族習(xí)慣法資源更是豐富多樣,對(duì)民族村寨景觀的形成、保護(hù)貢獻(xiàn)著力量,應(yīng)大力傳承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 余貴忠,翟星晨.苗族習(xí)慣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的影響[J].人口.社會(huì).法制研究,2013(01):148-149.
[2] 韋志明.民族習(xí)慣法對(duì)西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的可能貢獻(xiàn)[J].內(nèi)蒙古社會(huì)科學(xué)(漢文版),2007(06):97.
[3] 周鐵濤.農(nóng)村法治化治理中的國(guó)家法與民間法[J].行政與法,2017(04):35.
[4] 郭武.論環(huán)境習(xí)慣法的法源價(jià)值[J].民間法,2016,17(01):96.
作者簡(jiǎn)介:游甲戌(1994—),男,貴州松桃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法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