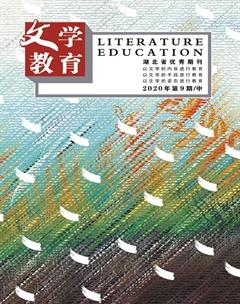尋他千百度

眾里尋他千百度。這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說的第三境界。“尋他”即是尋找文學最恰當的表達方式。只是因“望盡天涯路”的視野或高或低、或近或遠、或寬或窄、或深或淺,“尋他”的結果不同罷了。
一般的寫作者在文學的表達上存在“四缺”。一是缺厚度;二是缺感覺;三是耐心;四是缺溝通。就像我步入老年缺鈣的身體一樣,不補充,兩腿就發軟。
厚度,既有后天的努力,也有先天的基因;既有內因,也有外因。作家博覽群書、涉獵廣泛,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座皆驚。“竟陵派”的代表人物譚元春“一篇文字,不須伸紙和墨,仰屋運思,已自有一篇全文”(《與鐘居易》)。作家才思敏捷、信手拈來是靠平時的積累。搜腸刮肚、江郎才盡,書到用時方恨少正說明積累的匱乏。恰如“公安派”領袖袁宏道所說:“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噴薄之勢,為缺典耳。”積累決定厚度,好文章與厚度成正比。學識淵博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中寫道:“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開頭二句就是借用三國時期的童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化腐朽為神奇的經典之作。
感覺,既有必然,也有偶然;既有睿智,也有氛圍。作家格物致知的敏銳,觸類旁通的應變,無中生有的聯想,酣暢淋漓的抒發,纏綿悱惻的傾訴,憑借“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體驗,依靠“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觀察。蘇軾為了找豪放獨特的感覺,“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感覺不能剽竊,不能拾人牙慧。前些年流行的歌曲《女人是老虎》,竟發現是從清代大文豪袁枚《沙彌思老虎》的小品文改編而來,韻味旋律便大打折扣。
耐心,仿佛與性格有關。“猴急”是形容人沒有耐心的常用詞。文學的耐心體現在持之以恒,反復推敲,過濾沉淀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世說新語》記載:“鐘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于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這是一向崇拜嵇康的鐘會投稿沒有耐心。至于充當晉文帝司馬昭的幫兇害死嵇康與本文無關。與耐心相對應的是自以為是,胸無成竹,缺乏底氣。
溝通,仿佛對暗號。《智取威虎山》中陰險狡詐的座山雕一聲“天王蓋地虎”,如果楊子榮對不上“寶塔鎮河妖”,就犧牲性命。寫作者與報刊雜志溝通需要一種不可言狀的默契。汪曾祺早年在昆明發表的作品主要通過他的老師沈從文推薦。二十歲的汪曾祺正應了《乾卦》九二爻: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現在刊物欄目眾多,選稿參差不齊,投稿也應有的放矢。欄目要求,字數限制,編輯的口味要搞清楚弄明白。順暢的溝通能事半功倍。我的散文《一只不幸的蒼蠅》投稿后,某個雜志的編輯看后說不怎么樣,不予采用。而《散文選刊》(原創版)的黃艷秋老師贊賞有加。文章刊發后,分別被達達文檔網范文大全和家庭文摘網收錄。
我的“尋他”之路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幾百字的處女作發表后,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把它作為定情物送給女友。諸多原因曾半途擱淺,寢食難安。離職后,初心未泯,晚年又搭上了遣詞造句的順風船。一步一個腳印,一年一個臺階,努力尋找文學的表達。
廣閱讀,增加積累。鄭玄家的奴婢皆讀書,開口就用《詩經》對話,堪稱魏晉風骨的經典佐證。帶著問題閱讀,“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但用鄭板橋的話說“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書讀得少,往往筆是心非;有時寫作就像買彩票,憑手氣操觚。2018年9月,我加入中國散文學會后,現為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的同學許正林對我說,現在只能說你是剛入門,你有多少文章經得起推敲,又有幾篇作品能作寫作范文?可謂切中要害,一點沾沾自喜的念頭瞬間被澆滅。悲鏡生白發,讀書歲月老。
勤寫作,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如何以文運事,如何將過往小題大做提煉出有意義的表達,便成為我的日常寫作。寫親情、話變遷、聊童趣、記鄉愁、抗疫情,力求體現最恰當的文學表達。近幾年,僅寫父母親的文章就發了5篇,話變遷的文章也上了《鴨綠江》雜志。一是認真地寫。同學李祥富擔任校長多年,出版了三本與教學有關的集子,還為我的第一本書寫過評論。他的隨筆也透露校長的架子,像述職報告,與文學表達有“學非所用之嫌”。我調侃他說,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參考他的文章,我想到的是如何學寫結合。二是不停地改。拙文《堤街》的結尾原是這樣寫的:“不知這條有故事的老街還能支撐多久。”總感覺太硬,不耐咀嚼。最后改為:“不知這條老街的故事還能延續多久。”文章就增添了綿柔回味感。
多溝通,丑媳婦遲早要見公婆。《西部散文選刊》的執行主編梅雨墨在微信中對我說,怎么寫是你的事,發不發是我的事。采風、筆會是溝通的學習的最好機會。首先是要不怕丑。大自然怕丑就制造了黑夜,寫作者怕丑就跳不出俗囿的陰影。多向大家高手討教。黃明山是本市的作協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詩歌、散文、小說、劇本都有豐碩成果。我2017年在《散文選刊》發表的第一篇散文《嘮叨》就是他推薦的。至今已發表十多篇。習作脫稿后,我首先就請他撥冗賜教。或改題目,或增減一段文字,一個標點符號他都仔細標注。散文《我在旅途當大廚》刊發在《散文選刊》2020年第二期。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是他在路途給我提示的。原題目:我在貴州當大廚。當然,少不了酌問字之酒。參加大型雜志組織的筆會,是最好的學習機會。2018年在黑龍江北安,見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國散文學會會長王巨才。他親自為我頒獎,給我“開小灶”,為我題詞:“道德文章”,令我終身受用。2019年江蘇睢寧,有幸聆聽了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的講座,并與之合影留念。近幾年的筆會,多次聆聽梁曉聲、劉慶邦、鮑爾吉·原野、曉蘇、巴根、蔣建偉、高玉昆等大家的講座,廣泛接觸全國各地的文友,收獲頗豐。經常向資深編輯何子英、鄭建榮、黃艷秋討教,受益匪淺。
舞文弄墨雖然是個體行為,但“畫眉”的深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悅己”者,既要“入時”,就必須肩負春風化雨的社會責任。個人的情感必須融入大眾的情愫,文學的表達必須與時代的節拍契合,留給后世的文字必須經得起時光的考驗。添毫吮墨固然寂寞,“尋他”之路縱然修遠,只要堅持不懈,雖跛躄也將振足而起。
吳斌,湖北潛江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在《速讀》、《參花》、《青年文學家》、《鴨綠江》、《長江叢刊》、《海外文摘》、《散文選刊》、《散文百家》等雜志發表文學作品百余篇。著有散文集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