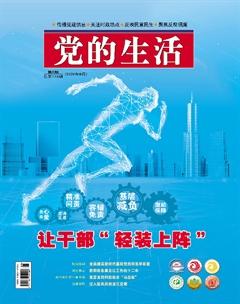張彥龍的科技助農“馬拉松”
柳菲絮
張彥龍是個運動健將,從上大學起就開始練長跑,至今仍堅持年年跑馬拉松。其實,馬拉松在張彥龍的生命中不僅是運動的代名詞,更是他矢志不渝科技助農的堅守與奉獻。
6月是木耳出產的高峰期,張彥龍放心不下勃利縣北興村木耳種植大戶劉林海家的木耳栽培情況,疫情防控局面剛剛穩定,就迫不及待地往村里趕。
到了大棚,看著眼前“噌噌”出耳的“黑色海洋”,張彥龍暫時放寬了心。劉林海拉著張彥龍的手高興地“顯擺”著:“您放心,我今年從做菌到扎眼兒,都是按您教的技術原封不動弄的。瞅這木耳長的,估計今年能多賺近十萬塊錢。”
像這樣一對一的技術指導,在張彥龍長達13年的基層掛職經歷中數不勝數。從廣袤的東北平原到條件艱苦的雪域高原,再回到黑土地,張彥龍一路走來,用小小的黑木耳勾畫出食用菌栽培助力地方經濟發展的大藍圖。
張彥龍覺得,13年間,自己的生活改變了很多,但唯一不變的,就是那顆越走越堅定的科技富農的心。
從群眾期待中尋找突破方向
2007年,為響應校縣合作的倡議,張彥龍以黑龍江中醫藥大學中藥學博士后、黑龍江大學教授的身份赴東寧縣掛職科技副縣長。
當時的東寧已是木耳生產大縣,全縣兩萬多菌農,幾乎家家種木耳、人人懂做菌。“我還能再做點啥?”走馬上任后,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張彥龍。
坐在辦公室是得不到答案的,張彥龍換上一雙運動鞋,開始用腳步丈量東寧。
在天天下大田、跨壟溝的走訪中,他聽到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聲音:“雖然我們東寧木耳已經遠銷美日韓和東南亞,但人家總說,你們的木耳一泡泡一碗,根部還有疙瘩,木耳太大了,能不能撕開?”于是,有的菌農連撕帶剪,結果泡發后的木耳豁牙露齒,品相更丑了。
張彥龍的到來,讓大家看到了希望:“張教授,你是這方面的專家,能不能給我們想個招兒?”
菌農的呼聲讓張彥龍深深意識到,東寧縣龐大的木耳種植規模背后,是缺少規范、粗放發展。
技術革新勢在必行,從哪兒入手呢?張彥龍在調研走訪中發現,有十幾家菌農的菌袋扎眼密度明顯高于其他菌農,可小孔菌袋結出的木耳產量并不比大孔菌袋的低。
這一發現讓張彥龍看到了突破方向。經過反復試驗論證,他決定在全縣菌農中推廣小孔菌袋技術,從每個菌袋扎眼30多孔改為每個菌袋扎眼180孔,讓“疙瘩”營養轉化為單片木耳。
沒想到,新技術剛開始推廣,就受到菌農的普遍抵制——“我們多少年了一直扎30多個孔,你整這么多,賠了算誰的?”
面對來自菌農的不理解,張彥龍又氣又急——氣的是大家不聽勸,急的是出菌不等人。

“不改技術,等著吃土”,張彥龍憋著一口氣,拿出了拉練的架勢——凡是種植小孔木耳的,每袋補貼一毛錢;同時,利用電視節目不間斷宣傳小孔木耳,在每個技術環節為菌農發送操作提示短信;再由科技特派團成員建立服務體系,培訓當地“土秀才”“田專家”,順次培訓菌農。
“大改小”技術推廣兩年后,菌農們服氣了——原來大木耳一袋能賣五毛錢,而小木耳一袋竟能賣上一塊錢,利潤坐地翻番。轉變觀念后的東寧菌農,從此步入高產增收快車道,到2009年年底,全縣菌農應用小孔種植技術已達100%。
在雪域高原上咬牙挺住
西藏自治區林芝市的菌農們一度用椴木種植木耳,木耳產量低,資源消耗大。2010年,張彥龍作為食用菌專家、援藏干部被派往林芝。在這里,他領著團隊攻堅克難,成功分離篩選出“黑大一號”優良菌株,填補了青藏高原黑木耳人工袋料栽培的空白。
回憶起攻堅克難的過程,與張彥龍一同進藏的研究生劉振東感慨頗深:“張老師一面在黑龍江大學負責教學科研工作,一面還要隨時研究攻克林芝木耳種植中出現的技術難點。那一年,基本上一周有三天是在‘天上過的。”
因為當時成都到林芝只排了早班機,張彥龍為了節約時間,頭一天晚上在黑龍江大學下了課,就連夜趕到機場飛往成都。落地后睡不幾個小時,凌晨三四點就爬起來再飛往林芝。
還是為了節約時間,張彥龍下了飛機就直奔菌農的大棚,湊到木耳跟前仔細察看長勢。室內培養黑木耳的架子高高低低,張彥龍每一株都要看,邊看邊和菌農交流。
在海拔2900米、氧氣稀薄的林芝,每次快速蹲下、站起,都會讓人有快要暈厥的感覺。從常理來說,短時間在海拔落差巨大的兩地往返,一般人吸氧臥床都算身體好的,更何況張彥龍還是在東北平原長大的。
一次,劉振東從木耳架子下面暈暈乎乎地站起來后,就問張彥龍:“張老師,您怎么一點兒反應都沒有?”
“我大學時就練長跑,工作以后一直堅持參加馬拉松,身體沒問題。”
可劉振東覺得,張彥龍“沒說真話”。據他觀察,張彥龍每次蹲下再起來時,臉部都會有一絲緊繃。但一直起腰,他就立刻進入工作狀態,不仔細看,根本察覺不出他的不適。
“張老師是怕耽誤工作,也怕給當地添麻煩,一直硬挺著。”劉振東分析。
由于地理環境差異太大,從養菌、滅菌到環境培養,在內地已經成熟的技術到了西藏都要推倒重來。而張彥龍要做的就是在白紙上描繪致富藍圖,用他的話說:“長跑需要體力,更需要毅力。”
在艱難探索了一年后,2011年6月,袋料地栽黑木耳在青藏高原試驗成功。
可現實情況并沒允許張彥龍的團隊高歌慶祝。技術推廣剛開始,菌農們就質疑:“木耳只能用椴木栽培,袋料地栽不可能出木耳!”
菌農們無法接受新技術,讓張彥龍頗感撓頭。這時,當地最大的木耳種植戶巴桑主動找到他:“張教授,我平時經常看科技助農節目,知道你是木耳專家,我信你。”在張彥龍的建議下,巴桑從東北引進了3000袋黑木耳。
從做菌到出耳,張彥龍手把手指導,巴桑當年收入就翻了一番,成了眾人艷羨的致富典型,還因此上了中央電視臺的《生財有道》節目。有巴桑做榜樣,林芝百姓開始逐漸接受張彥龍的袋料地栽技術,紛紛從“等著出丑”轉為“爭先改種”。
援藏期滿后,張彥龍總惦記著巴桑,惦記著曾經艱難“奔跑”過的地方,每年都要去西藏幾次。為了學習前沿技術,巴桑這幾年也沒少往黑龍江跑,用他的話說:“現在我和張教授處得跟哥們兒似的。”
“不用你們上訪,我下訪!”
2018年,七臺河市利用“柔性人才引進”政策,邀請張彥龍到勃利縣擔任副縣長,這也是他第三次帶著技術下基層。
這天,張彥龍正在西藏回訪,勃利縣農業局局長的電話打了過來:“張縣長,你快來回來看看吧,200多菌農層層上訪,說菌是假的,長不出木耳,我們真是頂不住了。”
回到勃利縣,張彥龍一頭扎進地里,打眼一瞅,一條黑線已經冒了出來,多年的經驗告訴他,木耳馬上就能長出來。頓時,他心里就有數了。
張彥龍把菌農們集合到一起,懇切地向大家承諾:“大家放心,木耳不出一周肯定長出來。但產量應該不高,我來就是給大家想辦法的。你們不用上訪,就坐家里等著,我下訪!”
從那天開始,張彥龍跑遍了勃利縣大大小小的所有村屯。他發現,90%的菌農20多年來一直是露天養菌。進入4月后,菌種先被寒流凍了一下,天氣回暖后再被密封導致的高溫灼一下,產量不低就怪了。
張彥龍決定,馬上推行大棚養菌技術,控制好濕度、溫度,11月開始做菌,到第二年4月就可出耳,等到夏季出四五茬木耳不成問題。
剛開始,用慣了老技術的菌農根本不理張彥龍這一套。2019年年初,帶頭采用新技術的菌農有了新發現:原來的木耳大片葉子又薄又黃,一袋只能賣一塊錢,用新技術產出的木耳不僅質量好,一袋還賣到了兩塊錢。
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效益后,全縣菌農開始陸續轉變養菌方式。到2019年年底,90%的菌農都跟上了新技術的腳步,人均年收益比上年實現了整體翻番,小小的黑木耳正在勃利大地開出五彩斑斕的“黑色之花”。與此同時,令人欣喜的消息也不斷傳來——張彥龍帶領團隊研發的“西藏六號”“西藏七號”雙雙獲得專利授權……
在2020年的脫貧攻堅浪潮中,研究醫藥專業的張彥龍又發現,勃利縣的土質利于黃芩種植。從小量試種到如今萬畝中藥田,勃利縣群眾的致富渠道越走越寬。
到“十四五”末期,勃利縣中藥材種植面積將達到50萬畝,其中,黃芩種植面積能達到20萬畝,產值突破50億元,可帶動就業人員20萬人。在張彥龍心中,“寒地中草藥之鄉”“中國黃芩之鄉”,是他正在勾勒的更為長遠的發展目標。
13年間,三下基層,突破層層技術關卡,一心只為百姓致富——這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對科技助農事業的執著,更是一名黨員對群眾的承諾。張彥龍覺得,這場科技助農的“馬拉松”尚未到達終點……
張彥龍,黑龍江大學教授,長期從事天然藥物化學領域研究,多年來先后受科技部、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黑龍江省科技廳、黑龍江大學委派,赴黑龍江省東寧縣、西藏自治區林芝市、黑龍江省勃利縣,利用推廣黑木耳、中草藥助力脫貧致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