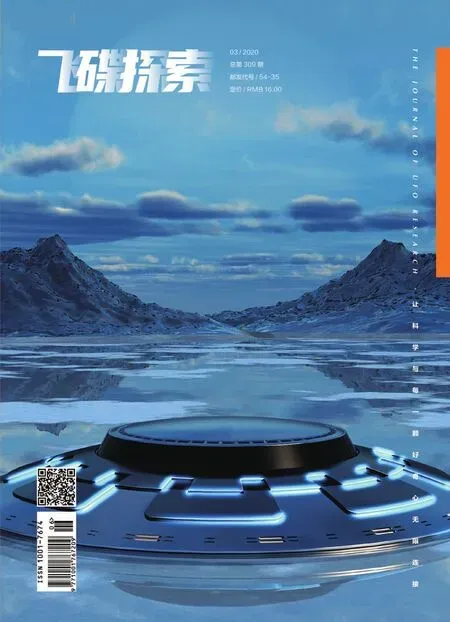機甲時代即將到來?
文|陳 飛


機甲和機器人:其實不一樣
機甲和機器人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機器人(Robot),這一概念包含的范圍非常廣。聯合國標準化組織給機器人下的定義為:“一種可編程、多功能的操作機,或是為了執行不同的任務而具有可用電腦改變和可編程動作的專門系統。”它們是一種機械,可代替人類完成很多危險的任務和工作,英文“Robot”一詞就是源于“奴隸、奴仆”(Robo)的變體。

戰術武裝機器人

由美國陸軍設計的未來士兵裝備
機甲(Mechanical armor),全稱為“戰術裝甲機器人”,同樣也是在人類的實際操作或提前編程的基礎上完成運行的。但這里,主要特指那些符合人體動力學的機械平臺,也就是俗稱的“像人一樣的機械”。
這種機械設計,參照人類的四肢,有機械手臂,下肢為雙足或多足,而且“裝甲”二字,意在強調它們可以像甲胄一樣穿戴在人的身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實中的機甲要比機器人從外形上更像人類。
但在電影里,二者的概念完全相反。在很多科幻電影里,機器人更像人類:比如《終結者》中金屬骨骼質感的T-800、《普羅米修斯》中外表與人類毫無區別的大衛,甚至《變形金剛》中那些來自外星的金屬生物,都被我們稱為機器人;而機甲有的具有人形,有的則只是一套盔甲。
最典型的要屬《阿凡達》中人類駕駛的AMP機甲,主要用來強化人類戰士的力量和防御,它與機器人有明顯的區別。但也有很多機甲外形與機器人沒什么兩樣,比如動畫片《機動戰士高達》和《新世紀福音戰士》中的戰斗機械。
其實,在大量的科幻影視、文學作品中,這二者區別的關鍵在于“靈魂”。人們愛給機器人這具冷冰冰的軀殼中想象一個人類的靈魂:比如《機械公敵》中最后“活”過來的機器人桑尼,《鐵巨人》中充滿童心的戰爭機器——這些角色具有了人格。
而機甲則沒有靈魂,無論外形如何,機甲都是武器、戰斗裝備,它們的個性來自于駕駛機甲的人類,假如沒有人類進行操控,機甲就是一堆廢鐵。在《環太平洋》中,被稱為“機器人”的超級裝備就屬于機甲這一類。
現實與科幻:機甲在發展
機甲,真的可以實際應用嗎?
在冷兵器時代,騎士身穿厚重的鎧甲抵御攻擊,減少傷害。隨著科技的進步,在經歷熱兵器時代各種戰斗車輛演變的同時,古代依靠鎧甲來保護自身的方式卻重新登上了舞臺。
在現實中,很多國家已經開始著手研發機甲項目,用于軍事、救災、消防、工業等多個領域,其最初形態便是“外骨骼”。
外骨骼是一種通過機械來增強人體行動能力的系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最符合機甲概念的裝備。目前,人類開發的驗證機主要用來提高人體的負重和行動能力,已經初具成效了。如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研制的“人類負重外骨骼”,依靠便攜式微型計算機和液壓驅動,最大負重可達90.7千克,能幫助士兵輕松攜帶大量裝備。
目前,外骨骼應用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動力源,一個隨身攜帶并能較長時間供電的電源通常要比一個人還重。此外,人體關節的彎曲程度和奔跑行走時的重心變化也是機械難以模擬的。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外骨骼遲早會進入實用領域。外骨骼的體積和功能還遠沒有達到科幻作品中機甲的程度,但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諸多圍繞科技人員的難關能被一一突破。
那么機甲為什么要執著于“人形”,模擬其他動物的形態不好嗎?
我們始終有著“人形”情節——《環太平洋》中的機甲顯示了人類四肢靈活的優點,由操縱者的雙手和雙足分別控制機械臂和機械腿,機甲關節處還有輔助液壓驅動設備,以符合人體動力學。這樣的機甲充分利用了人類四肢的功能,使得機械體的下肢不再局限于輪子和履帶,更便于應付復雜多變的地形,完成一般運輸工具難以達成的目標。
其實,機甲做成人形,是一個關于人機交互方式的問題。原則上,越接近人類自身動作習慣的交互方式,越能快速地在人機之間進行傳遞。比如,人類在駕駛交通工具時會存在一個“反射間隔”:當大腦傳遞給四肢一個或多個指令時,人體必須將動作執行于操作桿上,或轉向,或停止,其中的信息傳遞就稍有延遲,因為操作儀器與大腦行動指令存在一個轉化過程。但機甲不存在這個問題,它的神經模擬和行為模擬能夠二合一——你動即它動,延遲就小得多了。
舉個例子,在電影《鐵甲鋼拳》中,主角起先用搖桿操作機器拳手,結果在比賽中節節敗退,最后他利用了機器拳手身上的動作捕捉系統,在臺下親自擊拳,臺上的機器拳手也跟著他的動作擊敗了敵人。
這就是機甲“二位一體”的優勢,是其他機械無法比擬的。我們的游戲機有了體感系統,就能比手柄有更好的體驗感,還能健身。話說,今后愛游戲的“阿宅”,說不定個個身形健美呢。
但機甲有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身為操縱者的人。未來,人工智能的飛躍會讓機器人和儀器具有極大的模擬人類的能力。機器人會變得越來越像人類,可以通過編程完成人類的幾乎全部工作。就連現在的軍用科技中,無人機、戰場機器人的出現也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對人類戰士的需求。在這種背景下,依靠人操作的機甲,或許會逐漸走向沒落。但機甲的弱點卻又恰恰是它的強項——操縱它的人類智能可以面對未知做出自己的判斷,而據我們目前的認識和技術,人工智能恐怕還無法做到這一點。

電影《鐵甲鋼拳》中由人類操作的機器拳擊手
鏈接或斷線:爭議的未來
電影《環太平洋》中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設定:人類為了駕駛機甲,將神經系統與人工智能進行了橋接,從而驅動巨大的機甲戰士與自己的行動指令同步進行。這種“人機鏈接”的方式是否就是現實中機甲的未來呢?
在這部電影中,進行人機鏈接的系統被稱為“龐斯鏈接”,這種系統并不是真的往人類大腦上插根電線,而是讓人工智能與人體脊椎相連,就是用片中駕駛員背后所連的“脊髓夾”。成功鏈接之后,人工智能會讀取人類的腦電波數據,在電腦上復制一個虛擬的大腦意識,智能傳送緩沖器會捕捉腦脈沖進行鏈接。
駕駛員必須穿一套“電路內襯服”,衣服上遍布電路傳感器。龐斯鏈接接通,傳感器即被激活,駕駛員的大腦指令和動作也會無偏差地投射給機甲戰士。
在現實世界中,機甲暫時分為兩大類:其一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外骨骼,是一種輔助性機械;另外一種就是相對大型的機甲,依靠動作模擬器(也就是“動作捕捉”)來完成指令。
可惜,依靠后者驅動的機甲,在反應速度上已經落后于人工智能的機器人了。未來,如要使人類操控動作直接“鏡像化”為機甲的動作,達到指令到動作的無延遲,基本上也只能靠“人機鏈接”來實現了。
在外骨骼技術中,日本賽百達因公司的HAl-5型輔助骨骼就采用了類似的鏈接。該技術并沒有鏈接大腦,而是在大腦向運動神經元發送指令時,通過輔助設備探測皮膚表面微弱的信號,再由動力裝置根據接收到的信號控制輔助骨骼運動,這算是“人機鏈接”比較初級的形式。但真正意義上的鏈接,指的是目前正在開發的神經芯片。
神經芯片就是在人類的大腦中植入微電子元件,將腦細胞和硅電路有機地連接,將活的生物體和機器融為一體。在科幻電影和游戲中,這種技術很常見,比如游戲《孤島危機2》中的納米裝甲,就是依靠納米科技在人類大腦中植入芯片,由寄生血糖注射器和電解微堆棧提供動力,使納米裝甲獲得強大的力量和防御功能。
仔細揣摩,這種技術還是挺可怕的。如果真能實現,那些戰士是否還算一個真正的“人”?人類世界是否會進入漫畫《銃夢》所描述的合成人時代?
所幸神經芯片就目前來說仍停留在“夢想”階段,比起戰爭,其應用更偏向于治病救人——比如讓盲人通過植入微電子器件重見光明。當神經芯片真正能實現那些科幻故事里的功能時,恐怕也會和現在的克隆人技術一樣引發倫理道德上的爭議。
在電影《環太平洋》中,有一個場景非常現實地指出了“人機鏈接”驅動機甲的瓶頸——機甲起初被設定為由一個人駕駛,結果實驗顯示,人體與機甲鏈接之后,驅動機甲返回的大量數據和指令超出了人類大腦處理信息的能力,會導致人的神經系統受損,引發癲癇和精神錯亂。因此,片中才會選用兩人駕駛機甲,而且必須依靠神經搭橋的方式將兩個人的意識和思維完全連接起來,把兩個人當成一個人使用。這個設定顯然是為了增強電影故事的戲劇沖突,但一個人無法驅動過于龐大的機甲卻是一個現實問題。
人類的科技正在進步,當它真正成熟時,會如何解決以上問題,誰也無法確定。越來越快的變化如同上好弦的鐘,不停地行進,科幻經由對技術發展和人類未來的想象,為我們展示了無數種可能,而人類命運的方向,則要由我們自己去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