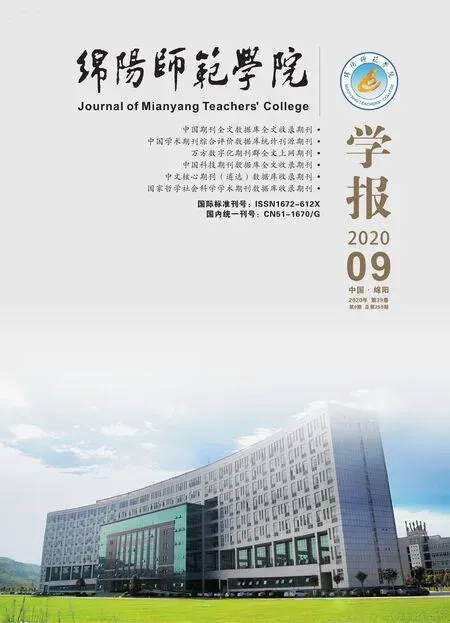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以舞降神”:甲骨卜辭中的樂舞文藝觀念
譚玉龍
(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重慶 400065)
殷商是我國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殷商青銅器不僅品類繁多,而且顯現出極高的文藝水準。但是殷商青銅器上的銘文并不豐富,早期青銅銘文僅有幾個字,且多為人名、父祖名和族徽,晚期青銅銘文最長也不到五十個字,所以殷商被孔子認為是“文獻不足”[1]2466(《論語·八佾》)的時代。從1899年開始,殷商“文獻不足”的情況得以改變,埋藏地下三千多年的、作為晚商直接史料的甲骨文陸續出土,并被科學整理與研究。到目前為止,已發現甲骨約15萬片[2]8,利用商代歷史的“原材料”——甲骨文——進行殷商史研究已經成為相關學者采用的“首要手段”[3]2。甲骨文雖是殷人占卜時刻下的記事之辭,但有關當時的軍事政治、農業生產、文學藝術等內容也被不知不覺地保留其中,如殷人對樂舞及其創作的態度和觀念就存在其中。所以,甲骨卜辭同樣是研究殷商文藝觀念的“原材料”,運用甲骨卜辭也應成為我們研究殷商文藝觀念必須采用的手段。
一、殷商時期的“帝”崇拜
商族的歷史十分悠久,是與大禹同時代的契的子孫。《荀子·成相》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4]464從契到成湯共十四世。大約在公元前十六世紀中葉,成湯滅夏,正式建立商王朝,并成為“王”,如《詩·商頌·殷武》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5]627《說文解字·王部》曰:“王,天下所歸往也。”[6]9戴侗《六書故》曰:“能一下土之謂王。”[7]771成為“王”的成湯乃是商朝一統天下的最高統治者,成湯以后的大甲、祖乙以及盤庚以后的諸統治者無不稱“王”。我們知道,宗教是人類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是異己的力量在人腦中的虛幻反映,所以,“一個上帝如沒有一個君主,永不會出現。支配許多自然現象,并結合各種互相沖突的自然力的上帝的統一,只是外表上或實際上結合著各個因利害沖突互相抗爭的個人的東洋專制君主的反映”[8]53。而天國世界中的至上全能的人格神——“帝”,正是商王朝最高統治者——“王”的投射和幻化。
“帝”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寫法類似,但其形式較為多樣,如:




“帝”是殷人祭祀的對象,是他們構想出的最高神,因其住在天上,故又稱為“上帝”。張衡《西京賦》曰:“此何與于殷人屢遷,前八而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14]421“前八”就是《史記·殷本紀》所謂的“自契至湯八遷”[15]93,即先公時期的八次遷都。今文《尚書·盤庚》所謂“不常厥邑,于今五邦”[16]223指的是從成湯建立商朝后的五次遷都,即“后五”。“后五”中的最后一次為盤庚遷都于殷(今河南安陽),從此至商亡的270多年未變。有學者認為到商代末年的生產還是以畜牧為主[17]8,也有學者認為商代是“以農立國”[18]307。根據先公和先王時期屢次遷都的情況來看,商代很有可能是在盤庚以前以畜牧為主,盤庚遷殷后的270多年以農立國,因為“盤庚遷殷以后社會經濟方面一定有了較大變化,才會一變過去長期以來經常遷都的局面”[19]18。農業與氣候息息相關,在能夠反映晚商思想觀念的甲骨卜辭中出現的“帝”自然被構想為具有控制氣候的神力,如:
貞翌癸卯帝其令風。(《合集》00672正·23)[20]51
自今庚子〔至〕于甲辰帝令雨。(《合集》00900正·7)[20]72
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合集》14127正·1)[21]737
殷人關于風、雨、雷、旱等天氣情況皆卜問“帝”,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天氣變化由“帝”控制,是其神力的體現。基于此,農業的收成也由他決定,如“帝受我年”[20]520(《合集》09731正·3)、“帝它我年”[20]542(《合集》10124正·1)。除自然氣候外,社會中的事務,如戰爭,也是“帝”意志的表現。武丁時代的卜辭有“貞方征,惟帝令作我。三月”[22]2001(《合集》39912·2)。其中的“方”指方國,“”應為《說文解字·戈部》中的“”,“,傷也”[6]631,“”即“禍”字[23]565。這句卜辭的意思是,方國來侵是“帝”降下的災禍。卜辭又有“〔伐〕〔方〕帝受〔我〕又”[20]344(《合集》06273)、“貞勿伐,帝不我其受又”[20]344(《合集》06272·3)。殷人征伐方國要取得“帝”的許可才能受到庇佑,即戰爭及其勝負也是由“帝”所決定。此外,“帝”還可決定一個人的健康與疾病,如“貞亡降疾”[21]724(《合集》13855·4)、“乙卯卜,〔不〕降〔〕”[24]1572(《合集》32112·2)。
要言之,“帝”是殷人塑造的至上全能的人格神,自然氣候、戰爭勝負、個人疾病等都由“帝”所決定,是其意志的表現。殷人圍繞“帝”還構想出了其他神靈,如四方神,人主去世后也可以“配帝”而成神,不過,“帝”仍然是最高神,是神界架構之核心。這種以“帝”崇拜為核心的思想觀念也成為殷人樂舞文藝觀念生成的文化背景。
二、關于樂舞的本質
“帝”及與之相關的其他神靈是殷人崇拜的對象,但“帝”是最高神,決定著自然氣候、戰爭勝負、個人健康,所以殷人凡事都要卜問“帝”,取得他的許可,同時也會按時祭祀“帝”以及其他神靈,否則就會有災難降臨。祭祀從本質上講,是古人的一種“推己及神”[25]75的思維方式和實踐活動,所以神與人一樣會有一系列需求。

乙酉卜,奏舞……(《合集》12821·1)[21]670
甲辰卜,爭,貞我舞岳。(《合集》14472)[21]759
甲辰卜,翌乙巳我奏舞,至于丙午……(《英國所藏甲骨集》Y01282)[28]6717
戰國末期的荀子提出了“夫樂者,樂也”[4]379(《荀子·樂論》)的命題,表明樂舞一方面是人快樂情感的表達,另一方面又給人帶來歡樂之情,所以樂舞的本質為“樂”(lè)。雖然在甲骨卜辭中,樂舞之“樂”已被察覺,但殷人卻將樂舞所“樂”的對象限定為神而非人,相對于進獻牲肉而言,樂舞滿足的是神靈的精神需求,希望通過娛神而得到庇佑。因此,認為中國古代樂舞美學具有“人本主義”特色的觀點[36]342顯然在殷人這里并不適用,因為殷人的樂舞觀念是在以“帝”崇拜為核心的文化背景中生成的,是以神為本,希望通過娛神而實現“以舞降神”[6]201(《說文解字·巫部》)的目的。
三、關于樂舞的功能
英國美學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認為:“藝術可以通過它對人的性格和觀點的影響來作用于現實生活。”[37]50這種文藝觀念在殷人那里也存在,只不過文藝不是通過對“人”的影響而是通過對“帝”及其他神靈的影響作用于現實生活。在殷人的思想中,“帝”及其相關神靈控制自然現象,決定著戰爭勝負和個人禍福,所以通過對這些神靈的卜問和祭祀就有可能趨利避害,獲得庇佑。這就決定了祭祀中的樂舞能夠間接發揮控制自然現象,決定戰爭勝負和個人禍福的功能。
至少從盤庚遷殷開始,殷商以農立國。雨水的多少與農業收成具有緊密聯系,所以甲骨文中有許多是關于祈雨的卜辭,其中又有不少是記錄殷人通過樂舞來祈雨的,如:



庚寅卜,辛卯奏舞雨[21]670。(《合集》12819·1)



貞其疾。七月。[20]1(《合集》00006·25—28)
“王弗疾”正是進行樂舞演奏(“奏”)想要達到的目的,當然這也是通過娛神而實現的。
簡言之,在殷人看來,樂舞能夠對現實生活產生影響,在祈求降雨、征伐勝利、拔除疾病等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體現出殷商樂舞文藝觀念的實用功利特色。不過,樂舞本身不具備直接影響現實生活的功能,而要靠愉悅神靈才能實現。
四、結語
在殷人的思想觀念中,一切自然現象、社會現實和個人吉兇等都由以“帝”為中心的神靈所決定,是神靈意志的表現,所以殷人凡事皆卜問神靈,按時祭祀神靈,以求庇佑和福報。這也成為殷商樂舞文藝觀念生成的文化背景。一方面,殷人將樂舞活動視為祭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有些樂舞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祭祀,體現出樂舞的本質就是宗教祭祀活動,而不是后世所認為的道德教化的工具或歡樂情感的表達,其直接目的是愉悅神靈;另一方面,殷人對樂舞抱有實用功利的態度,認為祭祀中的樂舞表演可以祈雨(或“無雨”),在戰爭中也可以運用樂舞鼓舞士氣、振奮人心以及通過樂舞拔除個人疾病。當然,樂舞的這些功能需要通過娛神來實現,樂舞本身無法直接發揮這些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殷人的樂舞文藝觀念中已暗含樂舞能夠對人的內心情感產生影響的內容,這對我國后世文藝創作論、審美教育論等是有所啟發的。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這段時間是我們人類的“軸心時代”,在此之前為“神話時代”[42]8-9。甲骨卜辭體現出的殷商樂舞文藝觀念顯然屬于“軸心時代”前的“神話時代”。那時,“人還沒有真正成為其自身”,“沒有覺醒的意識”[42]13,所以以宗教祭祀活動面貌出場的樂舞不是娛人而是娛神,對現實發揮作用、產生影響也必須通過神靈才能實現。但盡管如此,殷商樂舞文藝觀念不僅是早期中國文藝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對此后產生了不是突破就是傳承的影響。這也顯示出利用出土文獻進行早期中國文藝觀念、美學思想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