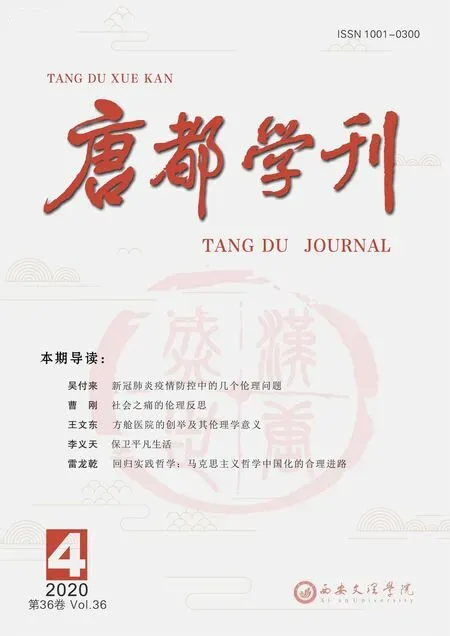朝鮮林椿散文與中國文化之關(guān)聯(lián)考論
王 成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哈爾濱 150080)
林椿(生卒年不詳),生活時間大致在高麗毅宗(1147—1170年在位)、明宗(1171—1197年在位)。他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林仲平、父親林光庇都曾在朝廷為官。到了林椿之時,因武臣政變,家道衰落。據(jù)《高麗史》卷15《列傳》載:“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鳴世,屢舉不第。鄭仲夫之亂,闔門遭禍,椿脫身僅免,卒窮夭而死。仁老集遺稿為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于世。”(1)參見鄭麟趾等《高麗史》,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館藏本。林椿的創(chuàng)作得到后人一致的贊譽,朝鮮肅宗時期崔錫鼎(1674—1720)《林西河集重刊序》言:“林西河耆之先生,生負絕藝,大鳴于世,文苑之評,謂得蘇長公風格”[1],李仁老《西河先生集序》曰:“先生文得古文,詩有騷雅之風骨,自海而東,以布衣雄世者一人而已。”[2]209林椿的散文創(chuàng)作與中國文化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取得了很高的藝術(shù)成就。
一、引經(jīng)據(jù)典,以中國文化典故來議論、說理
按高麗科舉制度,像林椿這樣的功勛之后可以不經(jīng)過科考而進入仕途,但以才華自恃的林椿并沒有選擇這種方式,他并不想借助父親林光庇的權(quán)勢而走上仕途,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心境:“仆自幼不好他技,博奕投壺、音律射御,一無所曉。唯讀書學文,欲以此自立。”[2]244別無他好、只嗜好讀書為文的林椿,希望憑借自己的才華揚名顯身,“而恥籍門戶余蔭,以干仕宦,故先君柄用時,豈求取祿利、以為己榮哉?”但現(xiàn)實是殘酷的,林椿曾參加過兩次科舉考試,但并未因富有才華而科考中榜。
希望被賞識、得到有識之人相助是林椿一直的渴求,他曾多次引用這類事典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趙勝之門,雖未作請行之毛遂。孔融之表,遽已為被薦之禰衡。毫發(fā)身輕,丘山恩重”[2]263,此處引用了兩個典故,一是毛遂自薦于平原君趙勝,出使楚國,促成楚、趙合縱,獲得了“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的美譽;一是孔融向曹操推薦好友禰衡。自薦需要有能賞識的人、有知己才有意義,林椿在《謝金少卿啟》中寫道:
伏念某,一曲之士,三尺之童,弧矢射天地四方,早懷壯志,錦繡為心肝五藏。未負奇才,久對揚黃卷之圣賢,猶未得青云之岐路。傷足泣淚,自貽獻寶之疑。斫鼻成風,誰識運斤之巧。我辰安在,自進誠難。以此痛心,不遑寧處。雖將寸管,愿瞻樂廣之云天。猶冒覆盆,未睹仲尼之日月。[2]263
“斫鼻成風,誰識運斤之巧”典出《莊子·徐無鬼》,莊子送葬,經(jīng)過惠子的墓地,他對身邊跟從的人講述發(fā)生在郢人、匠石、宋元君之間的故事,莊子以石匠的故事表達了知音難求以及對好友懷念的心情,慨嘆惠子死后,他再沒有可以談話的知己了,“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zhì)矣,吾無與言之矣”[3]。林椿引此典要表達的是,沒有真正識得自己才華的人,如同莊子痛惜好友惠子之死一般。
林椿又引用了樂廣的典故,樂廣為西晉名士,出身寒門,早年即有重名,受衛(wèi)瓘、王戎、裴楷等人欣賞,得以步入仕途。衛(wèi)瓘曾稱贊他“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云霧而睹青天也。”[4]林椿希望能得到賞識,如同見到樂廣一樣,撥開烏云見到太陽。但自己猶如頂著覆盆,無法沐浴到圣人孔子的光芒。“覆盆”,語出晉葛洪《抱樸子·辨問》“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nèi)也”[5],謂陽光照不到覆盆之下,后因以喻社會黑暗或無處申訴的沉冤。
林椿多次向人言及自己的窮困以及世態(tài)的炎涼、人情的冷暖,“仆自遭難,跋前躓后,隱匿竄伏,投于人而求濟者數(shù)矣,皆以犬彘遇之而不顧。故居京師凡五載,饑寒益甚,至親戚無有納門者,乃挈家而東焉”[2]248。他在《與趙亦樂書》中還把自己與古代賢人的窮厄相比較,“嗟乎!自古賢人才士例多窮厄矣,而無有如仆者。子美之流落,韓愈之幼孤,摯虞之饑困,馮唐之無時,羅隱之不第,長卿之多病。古人特犯其一,而亦已為不幸人。仆今皆犯之,豈不悲哉!”[2]246杜甫、韓愈、摯虞、馮唐、羅隱、司馬相如等都有不幸的經(jīng)歷。杜甫一生顛沛流離,居無定所;韓愈3歲時,父親去世,由兄長撫養(yǎng)長大。后兄長病亡,韓愈隨寡嫂顛沛流離;摯虞曾流離到鄠、杜地區(qū),糧食斷絕,以橡子充饑,最終清貧餓死;漢武帝求賢時,馮唐已年過古稀,后世文人常用馮唐之典來比喻老來難以得志;羅隱應進士試,斷斷續(xù)續(xù)考了十多次,自稱“十二三年就試期”,史稱“十上不第”;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患有消渴病。林椿認為自己相比古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吳郎中啟》是林椿寫給吳啟的一封信,全文一千五百余字,幾乎全篇用典,引用中國歷史、文化典故達近百處,顯示出林椿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熟諳,同時這些典故的運用也使他的表達、訴求顯得真誠,合情合理。現(xiàn)錄幾段文字于下,以見其實。如開篇曰:


這段文字所引都是士子受禮遇或士子因受舉薦而最終發(fā)跡的典故,這也是林椿一直希望能遇到或者可以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因為自己就如同那些歷史人物一樣,勤學苦讀,“早樂父兄之訓,切勤翰墨之功,童而習之紛如,謾自勤于晝夜”。但由于沒有遇到真正的伯樂,自己又“寧誤身于儒冠,恥藉榮于門蔭”(7)參見《上吳郎中啟》。,所以蹉跎至今,受到世人的不解、唾棄。但是“燕雀焉知鴻鵠志四海九州,騏驥不與駑駘爭一日千里”(8)參見《上吳郎中啟》。,“燕雀”句典出《史記·陳涉世家》,“騏驥”句典出《荀子·勸學》。林椿對于他人的不解是不屑的,自己甘心“慨然抱璞,翹以待求”(9)參見《上吳郎中啟》。。在他看來,這些人就如同燕雀、駑馬,是不知道鴻鵠之志、騏驥能一日千里的。
林椿寫家庭遭遇的變故以及自己的心情時也運用典故來作襯托:“曩者因其積釁之所萌,忽爾私門之發(fā)禍,遭家不造,叫天無辜,以有涯之生,罹不測之患。拋戈泣血,方銜桓氏之冤。陟屺興悲,繼有魏人之苦。何中散之途窮,信賈生之命薄。閉門卻掃,絕交游而遠讒。丐食假衣,攜細弱而避地。一涯流落,幾度寒暄。迺遑遑而無歸,常郁郁而居此。久類虞卿之羈旅,誰憐令伯之零丁。”家門慘遭橫禍,呼天不應叫地不靈。作者用了一連串的歷史典故來表達自己的心情:桓彝被殺,其子桓溫“枕戈泣血,志在復仇”(10)參見《晉書·桓溫傳》。。作者引用這個典故,表達了對造成家禍之人的憤慨。《詩經(jīng)·魏風·陟岵》有詩句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后以“陟屺”為思念母親之典,林椿引此典故傳達出對母親的思念。嵇康曾任中散大夫,史稱“嵇中散”,向往出世的生活,一生窮頓。賈誼曾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是失意士子的代稱。不幸遭遇使林椿“閉門卻掃,絕交游而遠讒。丐食假衣,攜細弱而避地”(11)參見《上吳郎中啟》。,常常遑遑無歸、郁郁寡歡,就像羈旅的虞信、喪母的李密。不幸的處境、遭遇,使林椿產(chǎn)生了回歸田園的心愿,他說:“樂潘岳田園之居,輸阮籍黍稷之稅。鑿而飲,耕而食,但虛老于太平。用則行,舍則藏,無茍容于斯世。于焉養(yǎng)志,不復有求。”[2]265“鑿而飲,耕而食”語出漢代王充《論衡·感虛》“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6];“用則行,舍則藏”語出《論語·述而》,這幾句話連用潘岳、阮籍、《擊壤歌》《論語·述而》等典故抒發(fā)心志。
林椿幾乎篇篇引用中國文化典故,如他恭賀李奎報高中狀元時說:“武帝讀相如之賦,喜于同時;明皇聞李白之才,召而親見。朝纔綴行于桂嶺,夕必待詔于玉堂,選士以來,唯公而已。”[2]271《漢書·司馬相如列傳》載:漢武帝讀《子虛賦》,大加贊賞,感慨自己不能與作者同時。后召見司馬相如,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云氣游天地之間意”;唐玄宗讀了李白的詩賦后非常欣賞,召李白進宮,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李白面前,并親手調(diào)羹。后多用作皇帝賞識臣下之典。林椿引用此二典,不僅表達出對當今賢明君主的贊揚,善于取才,也對李奎報能“首登優(yōu)第”,并“位佇登于廊廟,使聞風而大振,為儒者之極榮”充滿艷羨,反觀自身的遭際,心情可想而知。再如《上安西大判陳郎中光修啟》中的典故引用,“聞循吏善政之風,其惟良二千石也,使游民不耕而食,故取禾三百囷兮,不有仁人”[2]272,語句化用《詩經(jīng)·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伐檀》詩歌原意是對剝削者不勞而獲的諷刺,林椿在此反用此典,突出陳光修的循吏善政,能使民豐足安樂。
受韓愈《毛穎傳》及《下邳侯革華傳》的影響,高麗文壇出現(xiàn)了一種特殊的文體——“假傳”。所謂“假傳”,是以擬人化的表現(xiàn)手法,采用人物傳記的形式,為動植物、日常用品等立傳的文學形式。林椿作有《麴醇傳》《孔方傳》兩篇假傳,二文在介紹傳主籍貫、世系、生平經(jīng)歷等背景時大多采用典故。
《麴醇傳》云:“麴醇,字子厚。其先隴西人也。九十代祖牟,佐后稷粒蒸民有功焉,《詩》所謂‘貽我來牟’是也。牟始隱不仕曰:‘吾必耕而后食矣。’乃居畎畝。”[2]259“牟”又作“麥牟”,即大麥。醇酒是用麥子等釀造出來的,所以說麥為醇之祖先。《詩經(jīng)·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酎”“醇”都是味道醇厚的酒,分別作為主人公及其父系的名字。
至魏初,醇父酎,知名于世,與尚書郞徐邈偏汲引于朝,每說酎不離口。時有白上者:“邈與酎私交,漸長亂階矣。”上怒,召邈詰之,邈頓首謝曰:“臣之從酎,以其有圣人之德,時復中之耳。”上乃責之。及晉受禪,知將亂,無仕進意,與劉伶、阮籍之徒為竹林游,以終其身焉。[2]259
語段中提及的幾個人物都以愛酒聞名于世,如徐邈,“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圣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圣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7]劉伶、阮籍與嵇康、山濤、向秀等人結(jié)社飲酒作詩文,號稱“竹林七賢”。劉伶作有《酒德頌》,其嗜酒不羈,被稱為“醉侯”。
《孔方傳》也運用了大量典故,如在描述錢幣的使用歷史時,作者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列舉歷史上重視錢幣的人物,如吳王劉濞、漢武帝、和嶠、劉晏、王安石等;另一方面舉出歷史上輕視甚至主張取消錢幣的人物,如漢元帝、貢禹、魯褒、王夷甫、司馬光等。
時吳王濞驕僭專擅,方與之為利焉。虎帝時海內(nèi)虛耗,府庫空竭。上憂之,拜方為富民侯,與其徒充鹽鐵丞僅同在朝,僅每呼為家兄不名。方性貪污而少廉隅,既總管財用,好權(quán)子母輕重之法,以為便國者不必古,在陶鑄之術(shù)爾。遂與民爭錙銖之利,低昂物價,賤谷而重貨,使民棄本逐末,妨于農(nóng)要,時諫官多上疏論之,上不聽。方又巧事權(quán)貴,出入其門,招權(quán)鬻爵,升黜在其掌,公卿多撓節(jié)事之,積實聚斂,券契如山,不可勝數(shù)。其接人遇物,無問賢不肖,雖市井人,茍富于財者,皆與之交通。所謂市井交者也,時或從閭里惡少,以彈棋格五為事,然頗好然諾,故時人為之語曰:“得孔方一言,重若黃金百斤。”[2]260
孔方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富民侯”,總管財務,權(quán)傾一時,有“得孔方一言,重若黃金百斤”之語。漢元帝時期,孔方“蠹國害民”,使得“公私俱困”“賄賂狼藉”,終被朝廷驅(qū)逐。
二、林椿“文氣”觀、“詩樂”觀與中國文學思想
林椿作為高麗文壇大家,對文壇發(fā)展有著深刻的體悟、認識,如他對高麗文壇模擬蘇詩現(xiàn)象的認識。林椿生活的時期,正是宋詩風盛行之時,學蘇軾、仿蘇軾是文壇主流,是一種時尚,并且,不學好蘇軾詩文也很難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李奎報《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曾言:“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時所尚而已。然今古以來,未若東坡之盛行,尤為人所嗜者也。豈以屬辭富贍,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匱故歟。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后學,未嘗斯須離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8]515李奎報指出了當時社會對蘇軾詩文的推崇程度,蘇軾的文集成為高麗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范。徐居正《東人詩話》云:“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二東坡出矣。’高元間,宋使求詩,學士權(quán)適贈詩曰:‘蘇子文章海外聞,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為灰燼,千古芳名不可焚。’宋使嘆服。其尚東坡可知也已。”[9]185這里所說的“高麗文士”包括朝廷文人,也包括備考學子以及一般詩壇文家。可見在高麗科考中蘇軾詩文已成為必讀之書目。
林椿曾寫信給李奎報,闡釋了自己對于蘇軾詩文的認識,《與眉叟論東坡文書》中說:
仆觀近世,東坡之文大行于時,學者誰不伏膺呻吟?然徒玩其文而已。就令有挦搖竄竊、自得其風骨者,不亦遠乎?然則學者但當隨其量以就所安而已,不必牽強橫寫,失其天質(zhì),亦一要也。唯仆與吾子雖未嘗讀其文,往往句法已略相似矣。豈非得于其中者暗與之合耶?[2]242
林椿指出了蘇軾詩文盛行于世的客觀事實,同時也指出存在的弊端,即只是學習其形式,“徒玩其文”,模仿其形而不得其神,所以他提倡“自得”,通過“自得”而得詩文之“風骨”,不失詩文之“天質(zhì)”。所謂“自得”即不“牽強模寫”、不“挦搖竄竊”。林椿認為自己和李奎報的詩文是“自得”之作,未嘗讀蘇軾詩文,卻做到了句法相似,“豈非得于其中者,暗與之合耶”。林椿所謂的“未嘗讀其文”當指沒有刻意模仿蘇軾詩文,而不是不讀蘇軾詩文。
作為高麗文壇大家,林椿對文壇的認識,不僅僅體現(xiàn)在關(guān)于蘇軾詩文、地位等認知上,還體現(xiàn)在他關(guān)于“文氣”觀、“詩樂”的詩學理論命題的闡釋。
(一)林椿“文氣”觀對中國文學思想的接受
自曹丕將“氣”引入文學批評中,“文”與“氣”的關(guān)系就成了歷代詩家重點探討的問題之一。曹丕《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劉勰、韓愈、蘇轍等人在繼承曹丕“文氣”觀的基礎上又有所創(chuàng)見,如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分文章風格為典雅、遠奧等八種,并指出這幾種文風都是因作家不同的才、氣、學、習而形成,作家的氣是根本性的。韓愈《答李翊書》也論及文氣與作家道德修養(yǎng)的關(guān)系,韓愈認為作家的思想道德如果得到提高,培養(yǎng)出旺盛的正氣或浩然之氣,文章也就可以寫好了。蘇轍認為“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yǎng)而致”,為文應該追求疏宕平淡的文風、抒發(fā)不平之氣。
韓國古代文論也頻繁討論“文”與“氣”的關(guān)系,如高麗李奎報《論詩中微旨略言》曰:“夫詩以意為主,設意尤難,綴辭次之。意亦以氣為主,由氣之優(yōu)劣,乃有深淺耳。然氣本乎天,不可學得。故氣之劣者,以雕文為工,未嘗以意為先也。”[8]524李奎報突出了“氣”在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意義,但也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他認為“氣”本于天,人是不可學得的。晚于李奎報的崔滋《補閑集》(卷中)說:“詩文以氣為主,氣發(fā)于性,意憑于氣,言出于情,情即意也。”[9]111崔滋認為“氣”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動力。李奎報、崔滋關(guān)于“文氣”關(guān)系的論述,過于理論化,沒有具體的指向性,這必然會增加理解的難度,也不利于學習者學習。
林椿也探討了文學創(chuàng)作與“氣”的關(guān)系,兼具理論價值與現(xiàn)實指導意義。他在《上李學士書》《上按部學士啟》中曰:
文之難尚矣,而不可學而能也。蓋其至剛之氣,充乎中而溢乎貌,發(fā)乎言而不自知者爾。茍能養(yǎng)其氣,雖未嘗執(zhí)筆以學之,文益自奇矣。養(yǎng)其氣者,非周覽名山大川,求天下之奇聞壯觀,則亦無以自廣胸中之志矣。是以,蘇子由以為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于人見歐陽公、韓大尉,然后為盡天下之大觀焉。[2]243
文以氣為主,動于中而形于言,非抽黃對白以相夸,必含英咀華而后妙。歷觀前輩,能有幾人?子厚雄深,雖韓愈尚難為敵。少陵高峭,使李白莫窺其藩。圣俞身窮而詩始工,潘閬發(fā)白而吟益苦。賈島之病在于瘦,孟郊之語出于貧。至如以李賀孤峰絕岸之奇,施于廊廟則駭矣。雖張公輕縑素練之美,猶得江山之助焉。才難不其然乎?賢者足以與此。[2]268
林椿指出,文學創(chuàng)作是復雜而難以言說的事情,一個作家想要創(chuàng)作出一部作品,就必須培養(yǎng)出“至剛之氣”,做到“充乎中而溢乎貌,發(fā)乎言而不自知”。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是作家內(nèi)心深處剛健之氣的結(jié)果。如果作家能養(yǎng)其氣,即使沒有模仿他人,文章也自然能有自己的風格,“文益自奇”。那么,如何養(yǎng)成這種可以使文章“自奇”的“氣”呢?林椿認為需要遍覽名山大川,觀覽天下的奇聞壯觀,這樣做的話,就可以“廣胸中之志”了。
“蘇子由以為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以下幾句化用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于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愿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后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10]《上樞密韓太尉書》開篇提出養(yǎng)氣與作文的關(guān)系,認為“以為文者,氣之所形”,文章是“氣”的表現(xiàn),進而提出總領(lǐng)全文的“養(yǎng)氣”說,“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yǎng)而致”。蘇轍結(jié)合自身經(jīng)歷對“養(yǎng)氣”說展開論述,他非常重視人生閱歷,他認為多接觸自然界與現(xiàn)實社會,了解其規(guī)律和內(nèi)蘊,提高認識,獲得創(chuàng)作的靈感,才能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作品。林椿引此典是為了下文做鋪墊,他希望能拜見“以雄文直道,獨立兩朝,為文章之司命”的李知命學士,“仆常愿摳衣函丈,執(zhí)弟子禮,與其門人賢士大夫,然后將以退理其文”。
“文以氣為主”出自曹丕《典論·論文》、“動于中而形于言”出自《毛詩序》、“抽黃對白”出自柳宗元《乞巧文》、“含英咀華”出自韓愈《進學解》。文章開篇連續(xù)引用四個典故討論文氣關(guān)系以及與之相關(guān)聯(lián)的一系列問題。林椿繼承了曹丕的“文氣”觀并有所發(fā)揮、拓展,他連續(xù)引用《毛詩序》、柳宗元、韓愈的話語,認為情感在心里被觸動必然就會表達為語言,語言又形成文字進而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創(chuàng)作、鑒賞以及作品審美價值的高下應以“氣”為主,不能只求語句對仗的工穩(wěn),而是要品味、體會詩文中所包含的精華。文學作品之“氣”與作者之“氣”也是相一致的。氣有清濁之分,作者的才性、氣質(zhì)也有不同。先天稟賦的區(qū)別、后天的不同經(jīng)歷,是決定文之高下的根本原因。由此林椿指出,柳宗元的雄深,韓愈難與之相匹;杜甫的高峭,李白望塵莫及。這是稟賦不同導致文風各異。梅堯臣之詩窮而后工,潘閬年老而愈苦吟,這是后天經(jīng)歷不同而使文風有異。郊寒島瘦,也是個人氣質(zhì)所致;李賀的奇絕不能施于廊廟,張說的詩得江山之助而體現(xiàn)輕縑素練之美。
文章以氣為主,如果沒有“氣”會變成怎樣?林椿云:“仆廢錮淪陷,為世所笑。屏居僻邑,坐增孤陋,學不益加,道不益進,遂為庸人矣。凡作文,以氣為主,而累經(jīng)憂患,神志荒敗,眊眊焉真一老農(nóng)也。其時時讀書,唯欲不忘吾圣人之道耳,假令萬一復得應科舉登朝廷。吾已老矣,無能為也。”[2]245林椿“凡作文,以氣為主”中的“氣”,指作家精神氣質(zhì)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xiàn),“文”與作家的精神之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并深深影響到作品的優(yōu)劣。他以切身經(jīng)歷、親身感受作為事例來闡說這一觀點。1170年的武臣政變改變了林椿這一類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屢試不第,過著窘迫的生活,靠朋友的救濟勉強度日。在這種境況下,他的銳氣日漸消磨,精神狀態(tài)也大不如從前,寫作文章的狀態(tài)也與之前不可同日而語,即是他所說的“屏居僻邑,坐增孤陋,學不益加,道不益進”(12)參見《與皇甫若水書》。。由此可見,精神氣質(zhì)、生活狀態(tài)與文章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林椿累經(jīng)憂患,神志困怠,在這種狀態(tài)下,自然無法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盡管他沒有放棄讀書,但目的卻是不忘圣人之道,并不是真心于文學創(chuàng)作。
(二)林椿“詩樂”觀與中國古代詩學
古代詩歌與音樂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大多數(shù)詩篇都是可以合樂而歌的,詩歌與音樂是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的。詩歌與音樂的關(guān)系也是歷代文學批評家積極探討的重要課題之一,如孔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正因為詩與歌有著如此密切的關(guān)系,后來就合稱為詩歌。
高麗文學以漢文學為主流,文人們學習創(chuàng)作漢詩漢文,但對中國古樂的認知卻存在一定的困難,林椿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與皇甫若水書》云:
仆觀近古已來本朝制作之體,與皇宋相為甲乙,而未聞有以善為樂章名于世者。以為六律之不可辨,而疾舒長短、清濁曲折之未能諧也。嗟乎!此亦當世秉筆為文者之一惑也。茍曰能曉音樂之節(jié)奏,然后乃得為此,則其必待師曠之瞽然后為耶?蓋虞夏之歌、殷周之頌,皆被管弦、流金石,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也。至后世作歌、詞、調(diào)、引,以合之律呂者皆是也。若李白之樂府、白居易之諷喻之類,非復有辨清濁、審疾徐、度長短曲折之異也,皆可以歌之,則何獨疑于此乎?[2]242
林椿認為高麗文學已經(jīng)取得了很高的藝術(shù)成就,與宋朝文學比美也不為過,但尚未聽說有以音樂聞名于世的人存在。如果無法辨識“六音”,那么就不可能知道音律的疾舒短長、清濁曲折,也就不可能寫出優(yōu)秀的樂章。對于音樂的不熟識,正是高麗文人的一大困惑,也一定程度上滯后了高麗文學的發(fā)展,影響了更多優(yōu)秀作品的產(chǎn)生。但是大多數(shù)高麗文人盲目無知,都以為能知曉音樂的節(jié)奏就可以了,不需要懂得樂理。照這樣的話,只有成為師曠般的樂師才能作出樂章。高麗文人還是停留在“虞夏之歌、殷周之頌,皆被管弦、流金石,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也。至后世作歌、詞、調(diào)、引,以合之律呂者皆是也”的認知世界中,沒有意識到中國的樂府詩體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李白、白居易的樂府詩“非復有辨清濁、審疾徐、度長短曲折之異也,皆可以歌之”,他們的樂府詩已經(jīng)不再以是否入樂為標準了,而是一種寫時事的新詩體。所以林椿鼓勵黃甫沆大膽去嘗試,“今又于樂章,推余刃而為之”。
林椿進一步指出:“正聲諧韶頀,勁氣沮金石,鏗鋐陶冶,動人耳目,非若鄭衛(wèi)之青角激楚以鼓動婦女之心也。論者或謂淫辭艷語,非壯士雅人所為。”所謂“正聲”即儒家所認可的“純正之音”,也指符合音律標準的樂聲。儒家思想認為,文藝應該“發(fā)乎情,止乎禮”,必須符合儒家的倫理道德與審美標準,為教化服務。“韶頀”,指廟堂、宮廷之樂,或泛指雅正的古樂。如果用儒家認可的純正之聲來協(xié)調(diào)廟堂或?qū)m廷之樂,那么就可以獲得“動人耳目”的效果,其“勁氣”可以“沮金石”,“鏗鋐”之聲可以陶冶人心。但是,也無法做到“若鄭衛(wèi)之青角激楚以鼓動婦女之心”。也就是說,廟堂或?qū)m廷的音樂之美,也不如鄭衛(wèi)的民間之樂可以悅男女之情。同時,林椿猜想會有人認為這是“淫辭艷語,非壯士雅人所為”,林椿打了形象的比喻,“然食物之有稻也粱也,美則美矣,固為常珍。至于遐方怪產(chǎn),然后乃得極天下之奇味,豈異于是哉”。稻子和高粱都是美好的食物,深受人們的喜愛,但是人們的日常飲食生活只有這兩樣食物是不夠的,也需要雜糧特產(chǎn)、奇珍山貨等補充、搭配,人們的口味、營養(yǎng)才能豐富、均衡。林椿認為廟堂之樂與鄭衛(wèi)等民間之樂的關(guān)系,與此是一樣的道理。
詩歌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文學家們必須學習音樂知識,懂得樂理,從而創(chuàng)作出更高水平的詩歌作品。林椿強調(diào)了音樂于詩歌的重要意義,無疑會對高麗文壇產(chǎn)生一定的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
綜上可見,林椿的散文與中國文化存在密切的聯(lián)系,他不僅大量引用中國文化典故來議論、說理,還對高麗文壇的現(xiàn)狀、高麗文學的發(fā)展等有著深入的理解,他關(guān)于“文氣”觀、“詩樂”觀等詩學理論的闡發(fā),在繼承中國詩學觀點的基礎上,又有一定的突破,為我們?nèi)蘸蟮南嚓P(guān)研究提供了域外的審美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