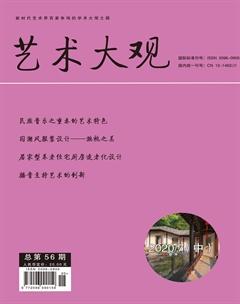絲綢之路新疆段文化景觀遺產廊道的傳承機制研究
姜丹
摘 要:縱觀絲綢之路新疆段,作為新疆區域內最大跨度的線狀、多維度的文化景觀、歷史遺產以及生態廊道,是人類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觀的龐大的遺產復合體。本文引入文化景觀遺產廊道的概念,兼顧景觀生態和遺產保護的有機聯結,強化對新疆鄉土社會結構和地域文化的理解,將文化景觀與線性組成的歷史遺存進行空間整合,拓展了大型線性文化景觀保護與發展的研究方法與視野。
關鍵詞:絲綢之路新疆段;文化景觀;遺產廊道;價值認知與傳承
中圖分類號:G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0)20-0-02
一、文化景觀遺產廊道的理論框架
(一)何為文化景觀遺產
文化景觀這一概念于1992年12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并納入《世界遺產名錄》,是指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的、人類罕見的、當前無法替代的文化景觀,是在全人類范圍內被公認的、具有突出意義的、擁有普遍社會價值的“自然和人類的共同作品”。其中包括了具有美學價值和人類有意識設計的建筑及景觀;代表某種過去時態,并且已經完結進化的殘遺景觀;具有進化性的以及可持續發展性的傳統社會性景觀;與自然因素、藝術、文化相聯系的瀕危建筑及景觀遺產。截至2019年10月,我國已獲批 5項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分別為:江西廬山、山西五臺山、浙江杭州西湖、云南紅河哈尼梯田、廣西花山巖畫。
(二)文化廊道與遺產廊道
“文化廊道”一詞的概念起源于美國的“遺產廊道”理論,并且與世界遺產保護領域中的“文化線路”概念有著緊密的關系。“遺產廊道”是源自西方區域化遺產保護戰略的相關理論及研究方法,因為具有“廊道”的屬性,因此通常“遺產廊道”多被強調與具有線型特征的“遺產區域”[1]。遺產廊道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分別為:路測綠色生態廊道、歷史遺產、解說系統、游步道,與此同時遺產廊道保護方式也具有機動性、靈活性的特點,它不僅泛指大范圍區域性的保護,也同樣適應用于某一特定區域或者個體的線性遺產保護。
進入新世紀,隨著“遺產廊道”理念研究的逐漸深入,眾多學者開始探討如何將線性遺產理論的實際落地,因此,隨著我國線性遺產區域的整體性開發保護的發展,結合我國國情提出了屬于線性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的新視角、新思路,“文化廊道”的理念隨即孕育而生。
(三)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國內外關于廊道、線路遺產以及文化景觀遺產的研究早期研究可追溯至19世紀,20世紀中后期,隨著《威尼斯憲章》等國際權威性文件的頒布,奠定了世界范圍內遺產保護的價值觀和方法論,隨之而來“綠道”概念被引入了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并涌現出大批代表性著作,例如《設計結合自然》[2]等。20世紀末,隨著人居環境和遺產保護問題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關注,因而文化景觀概念被正式提出。我國于20世紀 80 年代將文化景觀的概念被應用于人文地理學等領域,21世紀后開始向綜合領域延伸,對開展文化景觀及遺產資源保護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近年來,文化景觀遺產、線路遺產、遺產廊道等先后進入主流研究視野,遺產保護的理念不斷深入。
二、絲綢之路新疆段的價值認知
(一)新疆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中的重要性
“絲綢之路”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提出,他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隨后這一命名很快被大眾和學術界所接受并運用。[3]
從絲綢之路發展的段落、走向和功能來看,新疆的確是古絲路的重要樞紐區之一,更是是世界五大古文明匯集的重要區域之一,是古代中原王朝通向中西亞甚至歐洲的要道核心區,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各民族交匯、交融、交往的要塞地區。如今黨中央在古代絲綢之路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共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同時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國成功聯合申報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首例跨國合作而成功申遺的項目。由此可見,新疆作為我國西部邊疆的戰略屏障,即是國家西部大發展戰略實施的重點區域,更是我國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絲綢之路新疆段在多方位、多領域、多學科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二)絲綢之路新疆段遺產資源梳理
首先,絲綢之路新疆段是具有線狀跨度特征的多維度的文化景觀,自古便是古絲路上“使者相望于道”“貝販往來不絕”的經濟和文化腹地,并自先秦以來繁衍了眾多古代民族聚落,段孕育了數以百計的古絲路城鎮及建筑遺址,其次絲綢之路新疆段是擁有中亞腹地特殊干旱區域的景觀風貌,在宏觀角度具有完整的生態廊道特征,影響了我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人居環境的發展走向。
因此對于此類大跨度、多維度、系統龐雜、分支多樣的線型文化遺產而言,其研究絕不能停留于或文化或遺產保護的單一層面。對于其文化景觀遺產的大尺度建構,應承擔起對地域歷史文脈的吸收,應該更多地具有當代文化價值的創造。然而反觀絲綢之路新疆段的研究現狀,缺乏整體性、延續性,人為割裂古道遺產和遺產之間的聯系性是問題的瓶頸,因為古絲路線路路上任何單體的文化遺產,其身份、地位、價值都難以代表整體線路的復雜多樣性的展示。
絲綢之路新疆段符合文化景觀遺產廊道概念的特征,因此,希望能夠此概念搭建起更具多樣性的遺產保護框架 ,進而深刻見證區域文化的價值和歷史文脈的傳承。
三、絲綢之路新疆段文化景觀遺產廊道構建的實踐研究
(一)推進絲綢之路新疆段文化景觀遺產廊道概念的本土化思考
文化景觀和遺產廊道的概念雖為我國開展大尺度線狀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構建文化景觀遺產廊道是突破當前保護困境 、提升其文化影響力的新舉措,但根據當前國內外學術成果的輸出情況可見,優秀成果相對偏少,針對在絲綢之路新疆段的地理范圍內開展相關研究的著述更加罕見,導致目前尚無確鑿的經驗可循。同時,鑒于該思想起源和運用對象的背景差異,必須對其進行本土化調適。
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在絲綢之路新疆段的認定標準上,協同遺產廊道保護的專家制訂專門的識別標準,厘清遺產廊道資源整體的賦存狀況;其次進一步查證歷史沿革和現實狀態,深入剖析各個重要遺產點的文化內涵,以及各種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的作用等;之后應該對絲綢之路新疆段文化景觀遺產廊道的保護資料,建立全面而科學的遺產檔案;結合區域特征和特點,采取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從以歷史為依據,依據考古、民族、民俗、藝術、生態、地理等個角度考察各遺產點的構成及屬性,最終全面概括絲綢之路新疆段的遺產價值,以此實現文化景觀遺產廊道概念的本土化,并有助于充實古絲路西域人類文明史料以及學術研究體系的積累。
(二)絲綢之路新疆段文化景觀遺產廊道構建的實踐方法探索
首先,根據絲綢之路歷史地理區域的劃分特點,選擇新疆段作為研究對象,思考該遺產段落在快速城鎮化發展背景下出現的問題,分析適合“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計劃導向的研究方法,基于國內外學術現狀,確定研究路線及可行性。
其次,通過大量文獻研究和實態調研,對新疆段文化景觀遺產廊道建立相對全面和準確的認知,例如地理及區位、景觀生態基礎、歷史沿革、區域發展現狀、鄉土社會特征等,是開展研究的重要前期基礎。
再次,采集并梳理物質及非物質性遺產要素,厘清各要素的復雜線索,引入綜合評價法,分析各要素在宏觀、中觀、微觀層次上的特性與價值構成,建立層次分析結構和指標體系,確定各項指標權重并建立評估模型,得出評價結果。
然后,分析文化景觀遺產廊道的整體空間格局,以及段落空間、點狀空間的數量構成、復雜性和現狀碎裂程度,并提出廊道空間的整合策略,例如:基于評價結果提煉空間控制點,梳理各空間的現行約束力、文化景觀序列等措施。
最后,基于生物多樣性、知識和遺產保護體系,探索新疆段文化景觀和遺產資源的保護與展示途徑。例如:強化廊道生態及基礎設施建設;保護聚落遺產地傳統文化;構建科學的解說系統;完善服務站網的建設;以優秀的文化景觀資源發展旅游業等。
四、結束語
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一帶一路”發展框架的實施,絲綢之路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挖掘與保護被列入了國家議事日程,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引入文化景觀遺產廊道的概念,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時代框架下,進一步拓展西部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建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孫葛.對絲綢之路(新疆段)遺產廊厘文化景顏進行頑覺建構意義晌研究[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6(06):91-95.
[2]柴文斌.論新疆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中的重要性[J].湖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06):30-35.
[3]王麗萍.文化遺產廊道構建的理論與實踐以滇藏茶馬古道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11(05):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