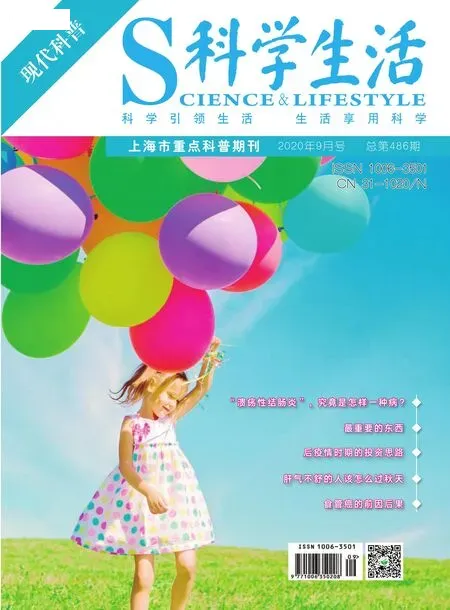“偷錢”的少年
文/陳露 編輯/南溪

一對中年夫婦和胖胖的兒子走進咨詢室。丈夫張先生看上去就像個大老板,身板厚實,步態沉穩,目光銳利,與他對視,有絲絲被審視的感覺。妻子李女士纖瘦,語速很快,透露出對13歲孩子的無比不安。
咨詢師只是問孩子叫什么名字,李女士就著急地對兒子說:“快說啊,快說呀!老師問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不想和我們說的,那你和老師說,你……”李女士一連串的話語像機關槍一樣掃射出來。母親的快速反應,反而讓兒子更加不知所措地看著她,一臉很懵的樣子。張先生見狀,身子坐直,說:“要不,我們出去,你單獨和老師說。”李女士更加著急,依舊催促道:“你說呀,你說呀。”短短幾分鐘內,父母輪番上陣,貌似淡定的爸爸居然要離開現場。
咨詢師會想,這個13歲的少年為什么不講話?他的母親為什么要這么著急地替他講話,她那么大的焦慮從哪里來?爸爸為什么要選擇離開?
于是,咨詢師問李女士發生了什么,為什么要著急地去催促孩子?李女士說孩子行為不良,屢教不改。張先生說因為孩子總是和他媽媽膩在一起,孩子會偷偷記下媽媽的手機密碼,然后把媽媽的錢轉到自己手機上,用于買游戲裝備。或者翻箱倒柜找到家里的錢,偷偷地藏起來或者花掉。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四次了。
對于孩子的偏差行為,父親的理解是:孩子有問題,偷錢被發現后還說謊。認為孩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也認為孩子的媽媽李女士沒有盡到該盡的責任,使孩子有空子可以鉆。
李女士愁容滿面,說:“好話、歹話說盡,打罵、批評,什么招都使了,就是沒有用,孩子這樣下去,要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而孩子的解釋是報復父母對他的嚴厲管教,“你們越是這樣對我吼,越不相信我,我就越這樣做。我以后的每一次行為,90%的目的就是報復你們, 10%的目的是需要用錢。”張先生說:“我就是不相信你!你就是在狡辯,你就是在為你的行為找借口。”
這個家庭的困難在于,當孩子不說話的時候,父母很想讓孩子說出真實的想法。但是當孩子說話了,父親又不會相信,甚至反駁孩子。于是,孩子就干脆不說了。
看著父子陷入僵持狀態,李女士說:“我能相信你。但是,我們怎么樣配合你,才可以讓你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孩子說:“第一,爸爸要經常回家,不要把家當旅店。我需要爸爸,媽媽需要老公。第二,爸爸、媽媽不要隨便吵什么最后都扯到我身上來。第三,要相信我,我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要腦補沒發生的事情。”
張先生聽著不說話,也沒什么反應,孩子就急了,說:“我說了也沒用,還不如不說。”
張先生說:“你讓我相信你,但是,為什么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偷錢的事情。所以,你現在所說的,還是在為你自己開脫,找借口。”
孩子瞬間像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
妻子李女士說:“孩子爸爸就是這樣,在單位是領導,在家里也是領導,對我們從來不相信、看不慣,說話很極端。”

1
家是一個系統,父親、母親和孩子的看法會各不相同,或者互相矛盾。但是,家庭里所有不同的觀點都是需要被聽見的,是有價值的。也許對爸爸來說,他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形成了自己一套認識世界的經驗和標準,他的價值體系幫助他在社會上很成功,成就了他今天的地位,同時,他在成年世界積累的經驗可能與一個13歲少年的內心世界不一定匹配。
而13歲的少年,正逐漸形成自己的觀點和想法,雖然他的想法和做法可能是片面的、局限的,他的叛逆和報復行為更多是指向與父母的關系。當然,少年的偏差行為是成長中的問題,是需要被引導的。所以,少年更需要的是被看見、被聽見,而不是用成年人的標簽去定義他,說他是個“說謊成性、品行不端的孩子”。這個標簽不會讓這個孩子變得更自信、更有自尊感,只會讓他更自暴自棄。
對此解釋,張先生點頭,表示同意。
良好的親子關系,才能開啟父親對孩子有效引導的可能,所以,父親和兒子必須盡可能地彼此看得見和明白對方。所以,父親需要機會重新去理解成長中的13歲少年;少年也需要去看見父親的不理解不是單純的父親不在乎他、不愛他,而是父親需要拓寬自己的視角,重新學習怎樣做一個13歲少年的父親。否則,雙方堅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僅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待事物,會導致誤解的產生,并且相互責怪,最后雙方都會很挫敗。
咨詢師也轉頭問孩子,第一次擅自挪用錢的行為是怎么產生的?孩子說:“我問媽媽要錢,媽媽不給。”當孩子希望獲得一點對金錢的支配權,但是正常的途徑不能獲得的時候,他就付諸行動,甚至想過去送一個月的快遞來掙錢。而沒等孩子說完,媽媽直接插嘴說:“你只要開口問我,我哪次沒有給你錢?”隨后,媽媽舉了很多例子來證明自己,孩子被問得張口結舌,低下頭不說話了。
母親很操勞,很辛苦。因為常年是母親帶孩子,先生在外地工作,每個周末回來。現在孩子出了問題,張先生會認為是李女士沒有帶好,甚至覺得作為母親的李女士有很多不良的生活習慣,給了孩子模仿和鉆空子的機會。
現在孩子居然也說他自己的拿錢行為是和媽媽有關。也許媽媽內在的情緒是感到委屈、困惑和無助,但是,她表現出來的說話方式是咄咄逼人。于是,孩子、丈夫,包括妻子本人也沒有看見她內在脆弱的部分。因為沒人看見,所以,媽媽的傷心、疲憊的情緒不僅不會得到安撫,而且媽媽從一個受傷的人變成了一個很會指責的人,讓孩子有了新的壓力。
當母子兩個人搞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咨詢師問孩子:“為什么不找你爸爸商量?”孩子一口咬定“爸爸是不會給我的,一年也說不了幾句話”。
這三口之家,每個人都是那么固執,彼此都沒有信任。父母不信任孩子,孩子不信任父母。父母之間也沒有情感的支持、理解和信任。
家庭是一個系統,如果我們看到母親和孩子的糾纏,那說明父親沒有有效地參與。而父親的無效參與會讓母子關系更加難解難分。在家庭結構中,父母屬于同一個位階,兒子屬于低一個位階。如果父親缺位,母親和孩子關系太過糾纏,孩子就等同于占據了父親的位置,母親就沒有辦法實施家長的權威,無論懲罰或者獎賞都很難奏效。

2
孩子發生了偏差行為召喚了不常在家的父親的“回家”,父親必須要和母親攜手一起處理孩子的問題。但是,父母在處理孩子的問題上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父母和孩子的行為實際上處于報復性升級的循環模式。一個越是要用權威來控制孩子不要那么干,另一個就越是要那么干。父母采取對孩子吼叫、逼迫孩子簽署各種協議的方法來試圖阻止孩子挪用金錢,而成長中需要獨立和自由的叛逆少年學會了陽奉陰違:你越是這樣,我越要“計劃下一次的行為”。相互的刺激接踵而至。
父母沒有辦法解決孩子的問題,本就脆弱的夫妻關系又一次面臨考驗。父母為了孩子的事情吵架的時候,父親扮演的角色是咄咄逼人的吼叫者,但是母親一句“你有本事你來管”把本來與孩子不熟、更擅長講大道理的父親架到一個讓孩子很抗拒的位置。當事情變得讓父親難以應對時,他選擇退縮到書房里,他也很挫敗。而父親的“無所作為”,也讓母子的關系更加纏結,母親就更加管不了孩子。好好的一個家,每一個人都活得很壓抑。
咨詢師需要創造性地處理父親、母親和孩子的困難三角,讓丈夫看見妻子的焦慮和孤獨,提升丈夫的功能去幫助面臨崩潰的妻子,加強夫妻之間的合作,一起想辦法,彼此鼓勵,相互支持,用溫和而堅定方式去引導孩子;同時,讓妻子去看見,雖然丈夫滿口的道理,滿臉的不信,但還是一次一次地堅持來見咨詢師,還是想解決問題,甚至妻子也補充道:“孩子爸爸只要不被激怒,在心平氣和的狀態下還是很有能力與我和孩子溝通的。他只要自己想做一件事,就會做得成。”孩子也流著眼淚承認拿錢這個行為是錯誤的。咨詢師讓這個家看到他們彼此的資源:爸爸是有能力的,媽媽更具彈性和包容,孩子是有判斷力的。
咨詢師放慢腳步,給每個家庭成員時間和空間去表達他們的想法,同時去聽見其他兩個人的想法,不要太本能地著急自我辯護或者批評對方,只是去回應對方值得肯定的部分,求同存異,一起探討如何從新的視角去理解孩子,以及解決孩子問題的策略有什么需要調整的地方。可能父母的眼光更需要資源取向,而不是“缺陷取向”。所謂缺陷取向,指的是只會看見孩子糟糕的地方,不曉得注意孩子有好的表現的時候,孩子即使錯誤百出,也有精彩的瞬間時刻。而我們的行為的鑄就,有時候可能取決于我們花很多精力去強化的那部分。我們真心強調的東西,也是孩子的心之所向。我們的焦慮也會成為孩子的不安全感。所以,有句話叫做:擔心是詛咒,愛和信任才是送給孩子成長的禮物。如果家長覺得“我信任孩子,但是他還……”那么這可能只是家長表層的感覺,其實內心并沒有放棄擔心。
作為兒子,需要學會選擇更公開、更成熟的方式爭取自己想要的對錢的支配權和想要的獨立,必須停止以不正當的、偷偷摸摸的方式獲取,或者采用報復的手段,要學會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家長需要理解兒子的偏差行為和以往家長的控制以及孩子的反控制有關。父母不再相信兒子,再三地懷疑、檢查、審問,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戲,反而可能增加偏差行為發生的概率。
這個家庭需要讓缺位的父親“歸位”,夫妻雙方的連接與合作增加了,母子之間的糾纏就減少了。夫妻能做到彼此安撫,情緒上會感覺輕松一些,對青春期少年的情緒性反應以及偏差行為的應對也能好一些,可能更具包容和接納,理性的回應,有效的引導就可能產生。
少年的問題是成長中的問題,隨著父母關系、親子關系的調整,孩子也漸漸走向正常的軌道。而有時候,正是少年出了問題后才反映出家庭出了問題,它的潛在的功能是拯救父母的婚姻,而后者是更隱秘的,很少被人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