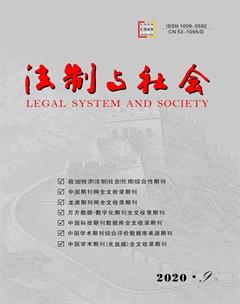少年司法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專業化建設
張媛 李小龍
關鍵詞未成年人 犯罪 社會化 建設
一、應然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服務體系
(一)服務對象中心主義
服務對象中心主義是指:在整個未成年人犯罪防治服務體系中,未成年人不僅僅是整個服務體系的服務對象,更是整個服務體系的主體。每一個未成年人都具有獨立的思維與個性,我們無從預測他們將給予我們何種反饋,更無法強制他們接受既定的服務計劃。或許在未成年人眼中,整個社會給予積極性價值評價的服務體系往往變得一文不值。因而,我們應該將未成年人作為整個社會服務體系的核心和主體,社會服務以他們的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充分調動和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為目標宗旨。唯有此,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服務體系才能擁有持續不斷的動力。這就要求整個服務體系的構建必須基于對未成年人實際需求的深刻認識之上。不僅如此,服務體系的構建更應該根據不斷的效果評估呈現出一個動態修正的過程。
(二)專業化的服務體系
隨著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理論研究的深入,我們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正在漸漸脫離“大普法”模式,轉而發展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相結合的防治體系。未成年人犯罪的類型較為固定,涉及的犯罪大多也主要集中在聚眾斗毆、故意傷害、搶劫、搶奪和盜竊等罪名之上。隨著我們對未成年人犯罪類型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化,我們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服務體系將走上類型犯罪預防的專業化道路。這不僅意味著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服務體系將擁有自己的獨立地位,更意味著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服務體系將以不同的犯罪類型為脈絡主干、結合犯罪成因,形成類型化、專門化的預防脈絡支系并形成支系之間彼此相對獨立又統一融合的有機整體。
(三)良好的資源整合能力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會的義務與責任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在這種共識下,社會各方主體通過緊密配合都在為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做出卓有成效的貢獻。立法機關加強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方面的立法,制定了“懲教結合,以教為主”的刑罰指導思想;司法機關從刑事司法程序著手,充分尊重和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以人文關懷為基礎重視涉罪未成年人的矯正與幫教工作;各級政府部門也在為確保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而制定、實踐各項專項活動,如:加強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拓寬社會就業渠道……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服務體系就是要把這些資源放到一個視角下,確定好各類工作的分工及轉介機制,做好各種資源的整合工作,減少社會資源的重復性利用,以便使社會各方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優勢發揮到最大,與此同時,各項工作在分工明確的基礎上又緊密協調、有機統一,使得整個社會化服務體系猶如一個運轉流暢的流水線一樣,各個節點環環相扣、連貫流暢。
二、當下青少年犯罪預防社會化服務的缺陷與不足
(一)過重的“家長式”社會化服務理念
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方面,我們的社會化服務理念依然帶有較為濃厚的“家長式”色彩。對未成年人提供的社會化服務依然具有較重的主觀色彩,在設計和實施服務過程中缺少與未成年人之間平等的互動與交流。在我們設置具體的社會化服務項目之前,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對服務項目的設置缺少項目評估;在我們設置服務項目時,缺乏對未成年人對社會服務項目意見的傾聽與采納;在我們運行服務項目時,欠缺對服務項目進行動態的修正與改進。
(二)社會化服務啟動時間的滯后
David olds的護士——家庭伙伴關系項目(NFP)告訴我們,對幼年群體提供社會服務的時間比我們預計的要早得多。可能在嬰兒期或出生之前,他們就需要我們適時的給予幫助。當然,此時幫助的對象是孩子的父母,即通過護士在嬰孩0至兩周歲期間積極的介入,幫助父母建立積極向上的人生從而促進孩子的健康和發展。這個項目得到了美國司法部青少年司法和預防犯罪辦公室的大力支持并且在紐約州的埃爾米拉地區試點。NFP項目的實驗報告于1986年發表,其研究成果引人注目。積極撫養項目(Tripl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則讓我們懂得:在孩子0至16歲期間,增加父母的知識、技能和信心對防止青少年在行為、情感和發展方面出現嚴重問題的重要意義。家庭是個體出生后接受社會化的第一個社會環境,家庭尤其母親的教育和影響對個人早期社會化甚至一生的社會化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當下,我們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服務面向的卻大都是10歲至20歲的青少年。由于這些青少年的一些習慣養成已經形成,此時要想通過我們的努力去改變一些他們不良的行為和思想或許會收效甚微。現實當中,很多年輕的父母自己都還沒有成熟,根本不明白養育孩子的責任,倘若我們的社會忽視對他們的關注與幫助,就容易讓未成年人在“家庭”——人生的第一個社會化場所中產生性格上的缺陷,進而更容易出現罪錯行為。
(三)社會化服務時空上的不連續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人口的流動性進一步增強。面對這些現實因素,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步伐尚不能跟上時代變遷的節奏。特別是對于具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而言,犯罪防治服務一方面要有時間上的持續性,另一方面又要有地域上的連續性,即無論身處何處,他們都能享有持續的、不分差別的社會化服務。然而,現實是,各個地域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一,使得所設定的服務機制與內容的兼容性、統一性不夠,使得未成年人在隨父母變換住所地的過程中,犯罪防治的社會服務無法在地域與地域之間實現良好的無縫對接,加之工作側重點的不同,容易造成了社會化服務的斷點。這樣,既容易削弱之前社會化服務帶來的良好成效,也容易在程序不斷重啟的過程中引發資源的重復性浪費。
三、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
(一)強化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服務性”
1.樹立“對象中心主義”的理念,加強征詢調研工作
第一,摒棄“家長式”管理意識,建立“傾聽式”平權型問詢理念。我們應該“多聽”“多看”,盡量避免對未成年人群體的需求進行主觀臆測。暢通青少年表達訴求的途徑,做好稱職的“傾聽者”,讓未成年人群體“愿說”“敢說”。在我們開展工作前,應該進行充分扎實的社會調研,提前了解未成年人群體的預期想法和工作運作的可行性和效果,并切實讓未成年人群體感知到自己的主體地位,增強他們積極主動參與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的積極性。
第二,建立社會化征詢調研機制。應把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調研工作放在“社會”的大環境下來考慮。家庭、社區、學校等每一個與未成年人生長有密切聯系的部門都應成為調研工作的主體,以最廣泛的視角來獲取最大化的信息量,從而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群體在家庭、社區、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工作中面臨的困境,進而不斷改善我們的工作,為他們的成長提供保障,及時防止其走向犯罪的邊緣。
第三,依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合理設置服務項目。比如,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我們在著眼于改造其不良思想與行為的同時更應注重其原有生活環境與方式的改變和剝離;在征詢調研的基礎上,依據未成年人群體的心理需要及其層次水平,科學地設置服務項目,使得我們的工作真正做到未成年人群體的“心坎里”。隨著項目的不斷運行,我們應根據實際及時作出調整。
(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配套機制,形成專業化運行模式
隨著社會的發展,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呈現出越來越綜合、復雜的特點,僅僅依靠法治觀念的樹立、正確價值觀的培養已經滿足不了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的實際需求。因而,我們也應加強其配套機制的完善,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立育齡夫婦的扶助、教育機制。對育齡夫婦中經濟困難或有不良行為的夫婦,我們應該給予特別的關注,引導他們形成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幫助他們形成良好的生活行為方式,必要時可以給予一定的生活援助以讓他們暫時緩解生活困難。在母親懷孕期間乃至生產之后的一至兩年內,對嬰幼兒的家庭環境與氛圍持續不問斷地給予關注,通過社區管理建立家庭氛圍危機預警監控機制,為嬰幼兒身心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第二,建立未成年人心理干預機制。我們應建立家庭、學校——社區——社會的三級心理干預機制。家庭和學校最易于也最便于感受未成年人的心理變化與波折。對于其中較為異常的心理變化,學校與家庭必須給予積極的疏導與引導。在無法疏導與引導時,必須向未成年人住所地所在地區的心理診療部門申請,酌情對其進行強制心理干預,做到及早發現,及早矯正。
(三)完善溝通協調機制、增強資源整合能力,提高社會化服務實效
雖然目前開展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社會化服務的主體眾多,但各主體之間的工作欠缺銜接性與協調性。這種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信息的不對稱。第二,兼容銜接性不強。因而,我們必須完善現有的協調反饋機制,通過建立信息共享平臺來扭轉信息不對稱的不利局面。我們可以建立網上信息共享平臺,司法機關定期發布轄區未成年人群體的涉案數據、類型及多發時間段等案件信息;社區管理機關從宏觀與微觀兩個維度對轄區未成年人成長氛圍的信息進行披露,為未成年人關愛援助項目提供基礎信息或直接提供候選援助對象;政府主管部門主動發布涉及未成年人的各種觀護項目及項目援助方向。在完善信息分享機制的同時,我們還需做好頂層設計,盡量讓個主體之間的工作有緊密的聯系和銜接性。我們可以讓司法機關為學校法治教育提供充盈的數據與現實案例,通過學校自身的教育資源確保教育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