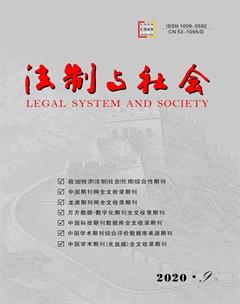依法治教視域下教育懲戒權的立法思考
陳美艾
關鍵詞依法治教 教育懲戒權 立法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自古懲戒與教育相佐,懲戒實際上是教育的代名詞,古代的“懲戒”在意義上與今天的“教育懲戒”含義不同,古代的“懲戒”有“懲罰”的意味。在西周時期,《禮記·王制》中有詳細記載,在官學中,對屢教不改的學生由周天子親自教育,在鄉學中,不符合規范的學生將被要求更換學生環境,即“轉校”;秦漢時期實行“嚴教嚴懲”的教育制度;在唐代的《尚書·舜典》中提到教師對不認真學習的學生可以施以刑法;在宋代的《京兆府小學規》中講到,“凡學生犯過錯,雖事大小而行罰”。
在國外,教師教育學生的手段也十分嚴厲。在古埃及的教育中主張采取嚴厲的體罰以刺激學生勤奮學習,最常用的方式是“鞭打”,通過嚴厲的教育手段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古希伯來人主張“懲罰使人明智”,教師經常體罰學生,學生也默認接受教師的體罰;在中世紀時代,棍棒是教育學生的必要手段,學生在學校隨時都有可能受到教師的棍棒毒打,懲罰過程中,學生不得哭喊,懲罰后學生要立下誓言勤奮學習,遵守紀律。奧古斯丁認為學生的內心是邪惡的,如果不對學生施加外部的強制性懲罰,學生則不會努力學習,他主張用懲罰以糾正學生的行為,在奧古斯丁所寫的《懺悔錄》中提到他在學生時期對于學習不敢怠慢,因為他恐懼教師的懲罰;在文藝復興時期,雖然主張尊重學生權利,但是教育懲罰仍然被視為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夸美紐斯認為,教育懲罰的目的是為了規范學生的錯誤行為,應該提倡,同時,赫爾巴特認為教育懲罰是學生違紀的必然結果。康德認為教師懲罰學生應該謹慎以免扼殺學生的權利意識,康德所強調的“懲罰”接近于今天意義上“懲戒”;前蘇聯教育學家馬卡連柯認為,懲戒應與學生的尊嚴聯系起來;盧梭、洛克、杜威等人開始強關注兒童的人格和個性,主張教育“以兒童為中心”。
綜上所述,在一定程度上,現代社會的規訓權力取代了我國古代的君主權力,在依法治教的大環境下,“懲戒”逐漸取代“懲罰”。
二、依法治教視域下教育懲戒權立法的價值審視
(一)保護學生的受教育權
學生的法律地位具有穩定性與靈活性的二元性的特征,學生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首先在憲法層面上,學生具有”公民“的身份;在教育法的層面上,學生具有”受教育者“的身份,另外,部分學生尤其是中小學生具有“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這三重身份規定了學生的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在教育場域內,教師的受教育權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受教育權是教育法律關系的主軸,因此教師懲戒權的功能之一就是保護學生的受教育權,為受教育權的實現提供保障。首先,穩定的教學秩序為學生的正常學習和受教育權的實現提供了前提條件,懲戒是教育的輔助手段,沒有懲戒就會造成學校的在學生管理方面的“無政府主義”。
其次,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施加任何強制,教育的任務和目的都無法達成。
根據斯金納的強化理論,學生發出行為后,出現滿意結果的行為,重復的可能性會增加,對于帶來煩惱的行為,重復性的可能性會下降。懲戒是控制或者試圖控制行為的有效方法,可以有效糾正違紀學生的行為。教師懲戒權的目的在于思想的傳播,給學生實施負強化,使學生懲戒的感覺慢慢融入到所有學生的觀念中,規范自己的行為,從而進行教學秩序的維護與教學管理,降低學生的犯錯率。在來源上,教師懲戒權源自于教育權的授權,然而教育權的背后是存在保護受教育權的目的指向的。
(二)保護教師的教育權和尊嚴權
教師懲戒權要解決教師教學工作的兩大難題:一是目前部分學校和老師對違紀學生不敢管、不愿管的現象,沒有履行教師應盡的職責。根據我國《教育法》《教師法》等法律的有關規定,教師承擔教書育人的責任,在教學過程有責任和義務對學生進行教育;二是改善不善管和管理不當的局面,懲戒過度的后果就是“變相體罰”。教師懲戒權有利于規范懲戒的具體細則,有利于教師依法執教,避免家校之間發生沖突。教師懲戒權保障了教師的個人權益,消除教師教育學生后果的后顧之憂,為教師安心進行教學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只有從法律制度層面明確教育懲戒權的范圍和尺度,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教師才敢于實施,讓師生關系回到正軌。
三、依法治教視域下教育懲戒權立法的疑惑與破除
“不敢管,不想管”的現象派生了很多棘手的問題。教育懲戒權受到公眾的質疑甚至反對的原因,主要來自以下兩大疑惑或印有,若不破除,教育懲戒權的具體實施難以落實和受到大眾的認可。
(一)教育懲戒權的使用是否會危及學生人身權
學生人身權包括學生的生命健康、隱私權、肖像權、人格尊嚴權等權利。許多人認為教育懲戒權與學生人身權存在兩個沖突:一是教師在履行教學義務時出于保證教學質量和穩定教學秩序的目的,教師會對違反課堂紀律的學生進行適度的懲戒,二是雖然在《教育法》和《教師法》明確規定教師有責任對學生進行教育和管理,但其表述尚顯模糊,難以界定教育和管理的度,教育懲戒權在我國目前尚未有明確的立法規范和法律保護,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公布《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征求意見稿)》旨在進一步保障教師職業權利,但目前征求意見稿還在修訂中,同時《教育法》明確規定學生擁有人身權和受教育權,因此會造成兩個極端:一是學生或家長對懲戒與體罰不能很好作區分,在實施懲戒過程中一旦學遭到人身傷害,學生便會告知家長企圖維護自身權利,往往會導致“校鬧”現象的發生;二是教師為了保障自身權益,對違紀的學生“放任不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學生的受教育權。
平衡教育懲戒權與學生人身權首先要明確“懲戒”和“體罰”間的區別以及二者的邊界。《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草案)》曾規定教師可對違反教學秩序的學生采取“罰站”“罰跑”等方式教育學生,但該規定于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二審中被刪除。同時,許多人反對懲戒權立法的原因在于,他們把“懲戒”與“體罰”的概念等同。首先,”懲戒“是指教師對學生采取合理、合法的,在確保學生身心安全的前提下,以規范學生學習行為和維持教學秩序為目的教育方式,“懲戒”是一種符合教育目的的懲罰方式,但并不意味著”懲戒“等同于”懲罰“。它是教育的主要手段,同時也是教師的職責所在,倘若學生應受懲戒而不懲戒,事實上屬于屬于教師的失責,“體罰”不利于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而且不利于教育目的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