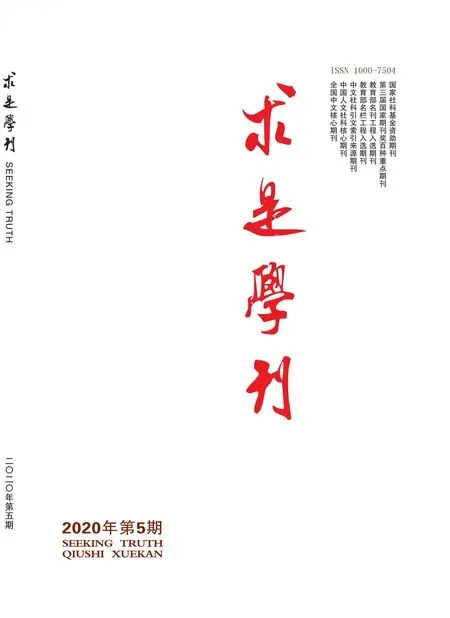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綠色金融發展問題研究
侯曉輝,王 博
引言
產業轉型與金融發展一直是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因此綠色金融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著密切聯系。在我國,綠色金融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幾乎興起于同一時期。隨著經濟發展中生態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綠色金融作為一種將金融約束與環境約束相匹配的手段,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綠色金融的發展日益受制于整個金融業改革步伐。我國金融業改革發展還不能夠很好地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主要體現在市場結構、產品工具、創新能力以及監管水平等供給側。因此,以優化結構、創新產品、完善監管、服務實體經濟為核心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然成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一環。2019 年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集中對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闡述。在2019 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強調,“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融資,更好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金融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新審視和調整傳統產業政策、金融政策,進而推動綠色產業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近年來,從供給側角度加快金融業改革、促進綠色產業發展受到國內外學者關注。筆者研究發現,目前關于綠色金融的理論研究,多是圍繞需求端、融資端展開;關于綠色金融的企業實踐,主要是圍繞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企業的綠色績效;關于綠色金融的政策導向,主要是圍繞鼓勵創新和加強監管。而這三個層面都缺乏從綠色產業需求側出發,完善金融供給的視角;缺乏從金融結構與實體經濟結構吻合、優化要素稟賦、完善制度安排的考慮。
本文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視角,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本文首先從綠色發展理念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入手,探討綠色金融對市場主體(商業銀行、企業等)的影響、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綠色金融與經濟發展等;其次結合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階段、新特點,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綠色金融發展的相互關系和機制進行探討;最后從結構性改革的方法和角度出發,對加快發展綠色金融提出政策建議。
一、綠色發展理念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
(一)新發展理念與綠色金融
綠色金融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和現實意義。關于綠色金融的概念和定義,國內外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解讀。國際上,綠色金融起源于“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EPs)的提出,最早出現于2003年6月,由一些私人銀行制定。國外學者也沿用“赤道原則”,研究商業銀行的綠色金融業務。①Scholtens,B.,Dam,L.,“Banking on the equator.Are Banks that Adopted the Equator Principles Different from Nonadopters?”,in World Development,2006,Vol.35,No.8,pp.1307-1308;Wright,Christopher,“Global banks,the Environment,and Human Rights:The Impact of the Equator Principles on Lend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i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2012,Vol.12,No.1,pp.56-77.直至2016 年G20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才給出了綠色金融較為權威的定義,其在2016 年發布的《G20 綠色金融綜合報告》中指出,“綠色金融指能產生環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投融資活動”。
綠色金融的重要理論基礎,主要是環境經濟學的外部性問題、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以及政府規制等。其中,外部性理論是綠色金融的重要特征,產權理論是綠色金融制度和政策的工具依據。相應的,綠色金融制度則是建立新型金融模式,規范投融資活動,達到促進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正效應。隨著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深水區,綠色金融逐漸成為落實新發展理念,踐行“兩山”理念的重要支撐,并成為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與發力點。②紀志宏:《深化綠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習時報》,2019年5月8日,第002版。黨的十九大報告、十三五規劃中都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G20 杭州峰會首次將其納入世界級會議議程。隨著綠色發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綠色金融將成為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推力。
(二)中國綠色金融發展政策
“綠色”理念進入五大發展理念,標志著我國對環境保護、綠色產業的定位從“以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環境負外部性”這一被動舉措,轉變為“引領新的發展方式”“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主動性戰略。③陳玲、謝孟希:《十八大以來我國環境治理體系的五大變革》,《CIDEG 政策研究報告》2018年第1期,第1頁。國家政策層面對綠色金融的支持,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幾乎是同步的。

表1 國家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有關政策
研究這些文件和政策后發現,國家層面綠色金融支持政策有以下特點:一是注重頂層設計,將綠色金融政策納入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和“十三五規劃”,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二是重視供給側的改革,從改善要素供給的角度發力。三是體現系統性、整體性,通過建立綠色金融體系,從信貸、債券、保險等方面系統推進。四是通過啟動改革試點,設立若干綠色金融改革創新實驗區,開展先行先試,總結經驗后再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
(三)綠色金融發展現狀
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由于金融市場、環保產業比較發達,綠色金融發展起步也更早。現有的文獻對上述國家研究較多,對本土化創新實踐的關注度不夠。
近年來,中國綠色金融實踐取得了明顯進展,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步建立,綠色產品不斷創新,綠色金融市場也在逐步形成。我國在綠色金融頂層設計、政策體系、先行先試等方面已走在國際前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尤其是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設立以來,在促進金融改革、培育綠色產業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先行先試,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對今后我國復制推廣綠色金融模式,促進產業綠色升級更有借鑒意義。
1.綠色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產品服務創新不斷涌現。截至2019年末,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余額超過10萬億元。2019年中國境內外綠色債券發行規模合計3390.62億元人民幣,發行數量214只,較2018年分別增長26%和48%,約占同期全球綠色債券發行規模的21.3%。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綠色信托、綠色PPP 等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涌現,有效拓寬了綠色項目的融資渠道,降低了融資成本和項目風險。
2.地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持續推進,初步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有益經驗。一方面通過綠色產業政策、貨幣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組合,激發了綠色金融市場主體的發展動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加強了綠色金融服務模式創新,各地在實踐中因地制宜,陸續推出了環境權益抵押融資、綠色市政債券等將近200 項創新型綠色金融產業和工具,以此來滿足不同綠色項目的個性化融資需求,使綠色項目的融資渠道不斷拓寬。
3.綠色金融多邊和雙邊合作不斷深化,有利于進一步參與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2018 年,人民銀行牽頭的G20 可持續金融研究小組將發展以綠色金融為核心內容的可持續金融的相關建議寫入《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公報》,繼續在全球范圍內推廣綠色金融共識。中國綠色金融政策、標準逐漸與全球接軌,中國綠色金融市場、產品在國際上的認可度不斷提升,展現出了中國在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負責任大國形象。
綠色金融作為一種市場化和政策性緊密結合的制度創新,還面臨很多挑戰和難題,特別是在綠色金融體系的構建和完善、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等方面依然存在許多不足。一是綠色金融產品單一、期限錯配。我國各類綠色金融產品日益豐富、工具箱日益完善。但發展并不均衡,綠色信貸仍居于主導地位,從規模來看,占比超過90%,仍需創新發展多元化的綠色金融產品體系。二是缺乏統一的綠色項目指引和綠色金融標準,金融機構的認定差別較大。加上數據整合進展緩慢,數據共享壁壘重重,統一標準和體系的建立任重道遠。三是環境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問題較為突出,企業“漂綠”“假綠”等綠色造假現象較為突出。由于綠色產業和項目在概念、標準等方面的模糊性和非強制性,一些提供綠色金融產品的金融機構依然以逐利為唯一準則,繼續為環境重大負面影響、爭議較大的項目融資,存在“漂綠”的嫌疑(Aizawa and Yang,2010)。①Aizawa,M.,Yang,C.,“Green Credit,Green Stimulus,Green Revolution?China’s Mobilization of Banks for Environmental Cleanup”,i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Development,2010,Vol.19,No.2,pp.119-144.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綠色金融發展:關系與作用機制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金融領域深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隨著現階段經濟運行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在不斷深化。2018年以來,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日益突出,實體經濟融資出現結構性問題,金融改革的緊迫性逐漸顯現。2019 年以來,中央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決策,也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漸深入金融領域的直接標志。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可以從“供給側”“結構性”和“改革”這三個關鍵詞代表的三個方面來分析。首先,“供給側”重點在“供給”,相對于以信用擴張為代表的“需求管理”手段,金融業供給體系的關鍵在于更高質量、更有效率地提供信用創造、金融服務等功能。其次,“結構性”改革所要解決的是“結構性”問題,重點是金融體系的結構調整優化,包括供需結構、融資結構、期限結構以及市場體系、產業體系等在內的系統性結構調整。與上一輪金融去杠桿單純強調“做減法”不同的是,金融供給側改革強調“有增有減”,強調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使金融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金融資源需求結構變化。第三,“改革”意味著框架性、制度性、系統性變革。其本質是通過改革的手段,整合金融要素,完善金融制度,創新金融產品,優化金融服務,管理金融風險,提升融資效率。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的實踐意義,就是實現金融體系服務產業體系、金融改革服務產業政策,進而推動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這個本源。隨著綠色發展成為國家戰略,綠色產業成為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重中之重,綠色金融便成為綠色產業政策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安排。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金融具有典型的雙向關系。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不斷推動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綠色產業占比不斷上升,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在增加;另一方面綠色金融的發展,又能夠通過信息傳導機制、投資導向機制等方式,引導金融資源更好服務綠色產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當前的理論研究多從金融需求端展開,實踐層面則是以大型銀行為主導的金融供給,且主動參與綠色產業和項目投融資的積極性不高,綠色金融供給顯著滯后于綠色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升級,亟待系統性改革。
(二)綠色金融與結構性改革的作用機制
國內學者受到新結構經濟學影響,逐漸從產業和結構層面進行研究。綠色金融工具能夠引導替代能源的發展,抑制污染項目,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①Anderson J.,“Environmental Finance”,in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le Finance,Amsterdam:Elsevier,2016,p.23.馮文芳從供給側角度做了研究,認為綠色金融能夠有效減少傳統行業產能過剩、優化生產要素供給結構、促進經濟轉型升級。②馮文芳、康海斌、李春梅:《綠色金融與民族地區供給側改革研究》,《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23—126頁。王遙等人從提高微觀效率、優化宏觀經濟,以及與其他經濟政策的互補效應等方面分析了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與貢獻。③王遙、潘冬陽、張笑:《綠色金融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6年第6期,第33—42頁。寧偉等人利用誤差修正模型和協整檢驗,對綠色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正向結論。④寧偉、佘金花:《綠色金融與宏觀經濟增長動態關系實證研究》,《求索》2014年第8期,第62—66頁。不過,麥均洪等人對商業銀行綠色信貸影響因素的研究表明:商業銀行對于開展綠色金融業務的積極性并不高,企業還款能力依然是商業銀行決策的首要影響因素。⑤麥均洪、徐楓:《基于聯合分析的我國綠色金融影響因素研究》,《宏觀經濟研究》2015年第5期,第23—37頁。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回歸市場主體、服務實體經濟。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從長期來看,企業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表現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性。⑥魯政委、方琦:《金融監管與綠色金融發展:實踐與研究綜述》,《金融監管研究》2018年第11期,第1—13頁。蘇冬蔚、連莉莉研究發現,綠色信貸政策能夠顯著抑制重污染企業的投融資行為。⑦蘇冬蔚、連莉莉:《綠色信貸是否影響重污染企業的投融資行為?》,《金融研究》2018年第12期,第123—137頁。2018年,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上市公司ESG表現與企業績效相關性研究》對上市公司ESG和環保表現與企業績效相關性進行了研究,顯示企業綠色績效、ESG績效均與企業績效正相關。
與此同時,綠色金融的發展,也能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何凌云等人的研究表明,綠色信貸規模的擴大能夠顯著促進環保企業的技術創新,從而加快產品升級。⑧何凌云等:《綠色信貸能促進環保企業技術創新嗎》,《金融經濟學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9—121頁。徐勝、趙欣欣和姚雙選取31個省份的相關面板數據,對綠色信貸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進行了研究,發現綠色信貸主要通過企業的資本形成機制與資金渠道影響產業結構。⑨徐勝、趙欣欣、姚雙:《綠色信貸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分析》,《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8 年第2 期,第59—72 頁。王康仕研究了我國工業轉型過程中的綠色金融支持機制,研究表明,綠色金融的發展能加劇污染企業的融資約束,抑制其投資水平,從而起到去產能、去杠桿的目的。①王康仕:《工業轉型中的綠色金融:驅動因素、作用機制與績效分析》,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年,第119—120頁。
現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已經從“三去一降一補”擴展到“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綠色金融作為綠色產業政策中的一種市場化工具,在新階段進一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綠色產業發展,也可以作用于上述四個層面。
1.從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上,鞏固“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
綠色金融一方面能夠通過大力培育低碳經濟、循環經濟,能夠持續降低鋼鐵、水泥等行業的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另一方面能夠通過產品和工具創新,促使金融機構調整對污染企業的信貸策略,影響其投資效率和投資結構,從而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源向新興綠色產業配置(Wang et al,2019)。②Wang,E.et al.“Green Credit.Debt Maturity,and Corporate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China”,in Sustainability,2019,Vol.11,No.3,p.583.銀行監管政策也可以通過調整監管政策,有效激勵銀行將信貸和資本重新分配給綠色產業。此外,綠色IPO 通道、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產業基金等,可以調整和分配風險,緩解去產能對經濟帶來的陣痛,進一步補齊發展短板。
2.從服務實體經濟上,增強微觀主體活力
多項研究表明,企業的環保表現、綠色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呈正相關,同時環保表現較好的企業創新能力也較強。因此,綠色金融的發展一方面能夠對企業的環保責任、綠色績效起到篩選和正向激勵作用,提升企業創新發展能力;另一方面,綠色金融的發展有助于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增強實體企業、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之間的信任,從而強化綠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可持續性。
3.從培育綠色產業上,提升產業鏈水平
綠色金融在加大環境污染防治力度、推動產業結構綠色轉型方面潛力巨大。一是綠色金融的發展通過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和共享機制,能夠彰顯綠色投資企業的聲譽優勢,使得為污染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金融機構面臨更大的行政處罰風險與聲譽風險。③Allet,M.,and Hudon,M.,“Green Micro-finance:Characteristics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i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5,Vol.126,No.3,pp.395-414.二是通過綠色股票、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金融產品,創新降低綠色企業的投資風險和融資成本,提高綠色企業的盈利能力,進而促進企業綠色投資,培育壯大綠色產業。三是為節能減排、環境治理等綠色項目提供重要的資金來源。四是通過發行綠色債券、綠色ABS(資產證券化)等綠色金融創新,緩解綠色項目的期限錯配及其他風險。五是通過綠色金融標準體系的建立完善,整合綠色產業鏈發展。
4.從完善現代市場體系上,暢通綠色經濟循環
一方面,綠色金融能夠有效解決環境資源負外部性問題,將環境負外部性成本內部化,糾正由環境問題所引發的市場失靈。另一方面,能夠有效解決目前經濟循環系統中金融和實體經濟循環不暢、資金“脫實向虛”等問題。通過綠色金融市場,將資本資源等要素向綠色產業聚集,打通各個環節的梗阻,促進綠色產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
(三)綠色金融體系與綠色產業匹配中存在的問題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基本內涵,就是金融供給要匹配金融需求,金融結構要匹配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在加快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框架下,就是綠色金融體系必須和綠色產業結構、綠色產業政策相匹配。在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雙重約束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不能只關注經濟數量和速度,還應側重于經濟質量,即效率問題和綠色發展問題。當前綠色金融體系在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改善供給、服務綠色產業發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和短板。
1.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長期以來,我國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與總量供給充足形成對比的,是有效供給不足。從地域上看,大量金融資源供給集中在東部地區、大中城市,而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金融供給不足。從行業領域上看,金融供給多投向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及基礎設施、能源化工、房地產等,對中小微企業、輕資產行業、綠色創新產業的支持不夠。
2.過剩產能行業占用的金融資源尚未完全釋放。國家開展“去產能”以來,過剩產能貸款總額和占比均有所下降,但“僵尸企業”的退出始終遇到障礙,甚至不少“僵尸企業”仍在依靠貸款續命,擠占了寶貴的金融資源,拖累了新舊動能轉換步伐,這也是造成供需錯配的重要因素。
3.綠色產業仍然融資難、融資貴。綠色產業多屬于新興產業,普遍具有風險高、資產輕、投資回報期長、抵押物不足等特點,不管是銀行信貸還是發行債券等融資方式,成本都更高,綜合生產成本總體上仍明顯高于傳統產業。可以說,綠色產業面臨的降成本、補短板需求更為強烈。
4.綠色金融體系與綠色產業政策存在脫節。中國綠色產業政策源于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實踐,當前的政策仍然是行政強制性環境管制手段與傳統產業政策的組合,對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以及政策之間的協調性關注不夠。①李曉萍、張億軍、江飛濤:《綠色產業政策:理論演進與中國實踐》,《財經研究》2019年第8期,第4—27頁。
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綠色發展,必須大力發展綠色產業。綠色產業的蓬勃發展,又離不開綠色金融的推動。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產業結構的綠色化、金融改革的深化,都需要從金融供給側尋求方案。
三、加快發展綠色金融的實踐路徑
結合上述探討,本文沿循結構性改革的思路,針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加快發展綠色金融,從金融要素供給、產品供給、制度供給以及改善供需結構等四個方面提出實踐路徑。
(一)提升綠色金融要素供給
優化綠色金融體系不是單純擴大投融資規模,而是要暢通金融要素的流動渠道和配置渠道。因此,一是要發揮價格信號作用,完善資源環境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需情況和生態價值的資源環境要素市場。二是完善綠色金融基礎設施,設立專業性綠色信貸銀行、綠色產業投資基金、綠色保險機構、綠色資本市場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場等。三是改善金融機構治理和市場結構,滿足綠色產業融資需求,發展風險投資、股權融資等直接融資方式。積極推動金融機構差異化定位,鼓勵大銀行開展綠色金融業務,同時促進農商行、城商行、農信社等中小金融機構聚焦綠色產業和三農,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綠色金融體系。四是要發揮好政府干預和財政資金在市場機制下的“杠桿效應”,撬動更多社會資源進入綠色金融,推動綠色產業發展。
(二)加強綠色金融產品供給
一是要創新綠色金融產品,推動綠色證券、私募股權投資、綠色債券、綠色保險以及碳金融、生態補償抵質押融資等創新型綠色金融產品加快發展。二是金融機構增強識別綠色項目的專業能力,通過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手段來突破綠色項目信息不對稱、期限錯配、綠色企業抵押品受限等融資制約。三是不斷完善政策工具箱,用好宏觀審慎評估等工具,加強再貸款、貼息、擔保等政策支持。采用排污權交易、環境稅、資源產品定價、碳排放標志認證等市場化政策工具,引導市場主體參與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綠色化轉換。四是加大綠色金融支持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力度,鼓勵和推廣綠色消費、生態農業、鄉村旅游等。
(三)健全綠色金融制度供給
健全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和法律法規,構建規范統一、國際接軌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完善綠色項目分類標準,完善綠色金融專項統計體系。搭建和推廣“綠貸通”銀企對接服務平臺,金融機構共享綠色企業、綠色項目信息,互認企業綠色認定和環境風險審查結果。政府層面或第三方機構要建立完善統一的環境信息披露標準,探索建立全鏈條的環境信息披露機制。探索企業環境信用評級制度,依據評價等級實行差別化電價、排污收費以及財稅優惠等綠色產業政策。在金融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復制推廣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經驗,進一步擴大試點范圍,將更多的省市納入試驗區范圍。金融機構要加快改革和制度創新,比如廣泛采納“赤道原則”、推廣設立赤道銀行,在組織結構上推廣設立董事會綠色金融委員會、綠色金融部等。
(四)改善金融與綠色產業供需結構
應注重將金融政策、產業政策、環境政策相結合,使供需結構更加匹配,政策銜接更加緊密。政府應加快構建“政產學研用金”六位一體的綠色產業創新體系,提高新能源、節能環保等綠色技術成果的轉化率。同時促進實體經濟綠色轉型,圍繞綠色產業創新開展綠色科技創新,帶動形成綠色產業體系,推動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金融機構應加強產融銜接,進一步完善綠色信貸等評估機制。同時要加大科技手段的應用,通過大數據分析、區塊鏈技術提升甄別綠色項目、評估企業環保風險的能力,淘汰“假綠”“漂綠”等綠色造假企業和項目,為綠色融資提供有效的激勵相容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