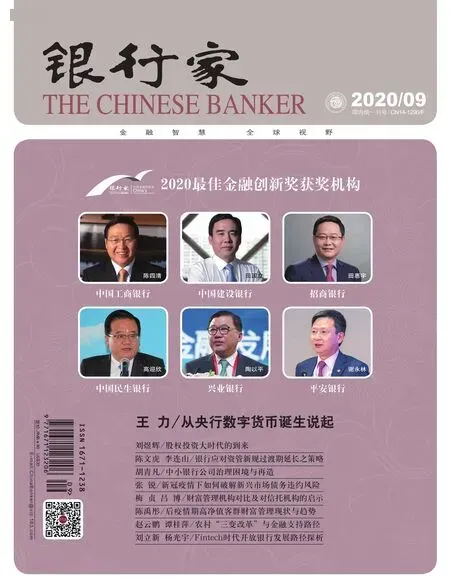我國居民債務:水平、風險及緩釋策略
高廣春



近年來,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努力持續顯示出對消費拉動的倚重,居民債務問題也因此備受關注。本文聚焦居民負債的管控視角,試圖對居民債務的水平、風險進行分析和評估,進而提出相應的管控策略。
居民債務高企且過度集中于住房貸款
從現狀看,我國居民債務存在“三高”,即債務總水平高、增長速度高、對房貸集中度高。
居民負債水平高企
首先看居民債務規模。依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調查結論,銀行貸款占家庭總負債的96.8%,由此可以用住戶貸款規模代表居民負債總規模。截至2019年底,用住戶貸款衡量的居民債務總規模余額達到55.32萬億元,占GDP的55.83%。判斷這個水平是否高了的一個重要視角是,比照一些重要經濟體在大致相同GDP水平上的住戶貸款與GDP之比。2019年中國人均GDP約在1萬美元左右,而美國、日本、韓國等在人均GDP約1萬美元水平時住戶貸款與GDP之比均在50%以下,分別為47.7%、48.9%和29%。其中,美國和日本人均GDP約至1.5萬美元時該比例才超過50%,分別是53.8%和55.6%;而韓國依然在50%以下,為40.58%。由此而言,以住戶貸款與GDP之比衡量的我國居民債務水平已經處于高位(見表1)。
居民負債上漲過快
從中國居民負債變化情況看,居民債務近10多年來持續上漲,2005~2019年的15年間,住戶貸款從3萬億元增長到55萬億元,增量超過52萬億元,增長近17倍。以10萬億元單位計的增速持續加快,從3萬億元到13萬億元用了約6年時間,從23萬億元到33萬億元用了約3年時間,從33萬億元到43萬億元用時約1.5年,從43萬億元到53萬億元用時不足1年(見圖1)。
再從住戶貸款與GDP之比的變化速度的視角看,居民債務水平也是一路加速走高。從2006~2019年,住戶貸款與GDP之比從16.86%升至55.83%,增幅超過2倍。其中完成一倍的增長用時近8年,再加一倍只用了3年多的時間。
居民債務對住房集中度過高
首先,從住戶貸款的集中度看,居民債務高度集中于住房抵押貸款。圖2顯示,近10年間,住戶貸款對住房抵押貸款的集中度持續提升。2019年在約55萬億元的住戶貸款余額中,住房抵押貸款余額約33萬億元,占比約60%,考慮到其他住戶貸款細分項目(即其他消費類貸款和經營性貸款)中實際包含一定數量的住房抵押貸款(如裝修貸款,經營性貸款挪用為住房抵押貸款等),實際住房抵押貸款在住戶貸款中的占比可能達到70%。
其次,從居民總債務集中度看,央行最新調查所顯示的居民債務對住房抵押貸款的集中度更高。2020年4月底由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題組發布的《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報告顯示,2019年有負債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貸款,占家庭總負債的比重為75.9%,另外還有約5%的貸款是裝修貸款。
居民債務償付結構性風險日益凸顯
在居民債務加速高企的同時,公開披露的居民個人債務不良率和違約率的相關數據總體頗為樂觀;央行最新的抽樣調查也顯示,居民家庭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基于結構視角的判斷則難以如此樂觀,央行的最新抽樣調查認為,剛需型房貸家庭的債務風險突出。筆者基于如下三個細分指標的分析推出的結論是,約一半的居民債務償付風險隱患堪憂。
約五成居民債務償付壓力較重
國際上衡量居民家庭或個人債務負擔壓力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債務償付比,即每月(或每季、每年)債務償付額占同期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就全部債務(包括住房、汽車及其他居民債務)而言,債務償付比的警戒線約為40%,即在40%以下的比例為可承受,超過40%債務償付壓力趨于不可承受。如果只用住房債務來衡量,合理的比例是低于30%,高于30%則償付壓力趨于加大,50%以上則意味著住房債務壓力達到較為嚴重的地步。由于住房債務在居民總體債務中的占比超過70%,加之居民住房債務數據易得、易測算,因此可以用住房貸款負擔代表總體債務負擔情況。測算的數據口徑是:居民家庭規模為3人,貸款期限為20年,利率為個人住房貸款加權利率,貸款首付比例20%,房價為2019年全國住宅銷售額和住宅銷售面積相除所得的均價,居民家庭收入是中位數,住房面積中位數估計為100或90平方米,償付模式是分期等額償付。測算結果如圖3所示,由此可見,近幾年來,無論是以100平方米還是90平方米為住房面積中位數,居民住房債務償付壓力均已經較為嚴重,但還沒有進入不堪重負的區間。其中,2019年的債務償付比分別是52.17%和46.96%,這意味著中位數下約50%的居民(主要是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的住房債務償付壓力已經處于或接近較為嚴重的程度。由于住房債務在住房貸款中占有絕對權重,住房債務壓力基本反映了居民債務的壓力(見圖3)。
約六成居民債務償付來源過于集中于工資性收入
不僅居民債務償付壓力大,而且償付來源過于集中于工資性收入。圖4顯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來源結構分布中,工資性收入一直居高不下,持續穩定在近60%的水平。2019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可以用來償付債務的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占比分別是55.9%、8.5%和8.1%(見圖4)。
進一步觀察,上述收入來源分布的集中度更為明顯。依據前述央行調查報告,金融資產最高的10%的家庭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占所有樣本家庭的58.3%,由此財產性收入高度集中于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也存在高度集中于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居民的問題。由此,至少有60%的家庭的債務償付來源幾乎全部依靠工資性收入。
居民收入增速下行侵蝕其債務償付能力
隨著經濟增速的下行,我國居民收入增速也出現緩步下行的趨勢。如近5年GDP指數(上年為100)從2014年的107.4下降到2019年的106.1;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同比從9%下降到7.9%,實際累計同比從6.8%下降到5%,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累計同比從10.3%下降到7.8%(見圖5)。
2020年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其給經濟和就業產生的巨大負面沖擊對居民收入無疑會帶來更大的下拉作用。從一季度的情況看,這種下拉作用已經顯現,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只有0.5%,同比降幅達7.4個百分點,實際可支配收入同比為-3.9%,降幅達9.8個百分點,中位數同比為0%,降幅達8.2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增速的下行勢必會侵蝕其財務狀況,下拉其債務償付能力。其中,基本靠工資性收入還債的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所感受到的債務償付壓力則將更為明顯。
居民債務償付風險緩釋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有必要針對居民債務償付風險提出相關緩釋策略。緩釋方向:降低債務負擔壓力、緩釋債務償付風險、穩定居民財務狀況。主要控制群體則是中等收入及以下居民。具體策略可以概括為“三可”:可支付交易、可償付債務、可救助機制。
可支付交易
該策略旨在將居民負債保持在合理水平。所謂可支付交易主要指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消費或經營的可支付性,集中體現為住房消費或投資的可支付性。有多種方法可以衡量居民住房的可支付性能,如剛需住房購買可支付性常用的指標為房價收入比(即住房套均價格與家庭年平均收入之間的比值),綜合考慮聯合國人居中心、國際經驗及我國實際,3~6倍是可支付交易匹配的區間。但由于住房市場的過度商品化,大多數住房的房價收入比位于10~20的區間,遠遠高于多數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不具備可支付性,多數居民只能通過背負更高的債務來完成購房的支付,因此積累了日益沉重的債務。
顯然在房價已經高漲的前提下,簡單化的降房價難以有效適應可支付交易的需求,更為可行的切入點不是降房價而是調結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戰略下,聚焦住房供給結構的優化,提供匹配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可支付能力的住房。可落地路徑包括:(1)立法保障。即盡快推出《住房保障法》規范住房供給端的行為,使其提供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可支付的住房。(2)政策激勵。即借助有效的政策性金融和財稅手段,激勵商業性房地產開發企業建構中等收入及以下居民可支付的住房,以促進可支付住房供給側的商業可持續性。(3)多元參與。如慈善資金參與建設可支付住房,互助合作建設可支付住房房,同時政策層面在稅收、土地、監管等方面給予支持。
可償付債務
主要指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債務的可償付性,信用卡、汽車、住房等均存在可償付債務問題,這里還是以住房為例來說明。就住房債務而言,市場上有了可支付住房,可償付債務問題就解決了一半。換言之,住房抵押債務規模自然就隨之降下來了。另一半的問題就是債務償付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更為直接的方法是用收入中債務償付的占比判斷債務的可償付性,對于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而言,30%是判斷債務是否可償付的分水嶺:在這個比例以下的債務具有可償付性;在這個比例以上的債務可償付性就存在問題。相應的,持續滿足債務可償付性要求的舉措包括:(1)穩定居民收入。由于這類居民的主要收入是工資性收入,穩定其就業成為首當其沖的要務。(2)適當政策援助。主要的手段包括減免收入稅、物業稅、財政貼息等。(3)優惠利息支持。主要是對住房公積金貸款設置門檻,限制中高收入居民住房公積金貸款,取消高收入居民住房公積金貸款,以此將更多的住房公積金貸款用于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購房需求,從而使其獲得盡可能多的優惠利息購房貸款。
可救助機制
即在居民無力償付債務時可以借助公共救助機制改善其債務償付能力或減免所負債務。失業、疾病、收入狀況惡化、房價持續下跌、情緒化高消費、濫刷信用卡等均有可能導致居民收入流銳減或資產縮水,甚至陷入一貧如洗或負資產的困境。可救助機制旨在對沖這些問題。有效之策是引入個人破產制度即盡快制定并頒行《個人破產法》,阻斷債務進一步放大并危及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可能性,同時幫助誠信債務當事人擺脫財務困境。值得關注的是,筆者撰寫本拙文之際,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發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征求意見稿)》,表明個人破產制度在國家層面的落地應該為期不遠。
基于可救助機制條件下的《個人破產法》的核心內容有兩個:(1)規定過渡期并實施財物救助。即啟動破產程序后,設立一定的過渡期,如4年,在此過渡期內通過政策救濟和當事人消費約束等方法幫助其修復財務狀況。包括借助免費技能培訓、小額財政援助等政策性手段支持再就業、自主就業或創業;通過擴大當事人醫保范圍、適當減免醫藥費等方式緩釋其因病致貧的風險;限制當事人的不合理消費、負債和投資活動;當事人財物收支封閉管理等。這些都有助于修復其收入流和資產負債表,恢復其債務償付能力。(2)中止或終止破產程序。對在過渡期內通過前述救助方式使財務狀況持續好轉,重新恢復債務償付能力的,減免一定數量的剩余債務,中止破產程序;對確難以恢復償付能力的,進行破產清算,免除其剩余債務,核銷其無限清償責任,并終止破產程序,以使其重新開始并重歸正常生活狀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