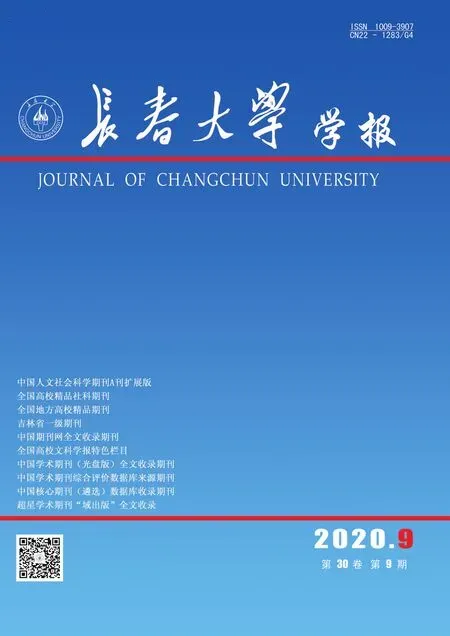現(xiàn)代漢語植物名的語言認知分析
譚宏姣,雷會營
(吉林師范大學 中國語言研究所,吉林 四平136000)
人與植物的關(guān)系是人與自然之間最重要的關(guān)系。在長期的生產(chǎn)活動中,人類對植物有了整體的認知和概念,這種認知體現(xiàn)在人類的語言中就是大量植物名的存在。“語言也是一種認知活動,是對客觀世界認知的結(jié)果,語言運用和理解的過程也是認知處理的過程。”[1]以《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版為語料,對其中的植物名進行范疇化、隱喻與轉(zhuǎn)喻方面的分析,試圖揭示漢語植物名的構(gòu)詞特點、命名緣由、詞義引申機制以及漢民族對植物的認知規(guī)律,并以此就教于方家學者。
1 現(xiàn)代漢語植物名的范疇化認知
1.1 基本層次范疇
人類根據(jù)世界萬物差異性中的相似或相關(guān)將萬物進行分類,進而形成概念,這種意識活動就是范疇化。范疇化是人們對客觀事物通過感知后進行反復概括和分類的過程,導致等級結(jié)構(gòu)的產(chǎn)生。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語境下,植物范疇化是有差異的,科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對于植物的范疇化等級劃分也不一致,如“松柏綱—松科—雪松”屬于科學語言的范疇化等級,“植物—樹—雪松”是生活語言中的上下位層次概念詞。
“具體來說,認知范疇分為基本層次范疇、上位范疇和下位范疇三部分,其中基本層次范疇在認知習得上具有優(yōu)先性。”[2]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對植物界的認知最先開始于基本層次范疇。語言學家發(fā)現(xiàn),處于中間位置的基本層次范疇更重要,因為它的形態(tài)結(jié)構(gòu)最簡單、特征最顯著,與人類的生活關(guān)系密切且容易識別和概括,這類事物現(xiàn)象更容易用于語言命名。考察現(xiàn)代漢語植物名,我們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植物名的構(gòu)詞語素中的屬語素都來自基本層次范疇,包括科學語言和生活語言兩類基本層次范疇。
如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以“樹(或木)、草、花、果”這些生活語言中的基本層次范疇概念構(gòu)詞的植物名非常普遍:
“樹”(或木)——白蠟樹、鴿子樹、公孫樹、果木、紅木、花櫚木等。
“草”——藨草、毒草、甘草、狗尾草、含羞草、葒草、草莓等。
“花”——報春花、菜花、朝陽花、大麗花、玳玳花、芙蓉花等。
“果”——長生果、蓇葖果、瓠果、開心果、芒果、奇異果等。
“菜”是典型的生活語言中的基本層次范疇概念,以“菜”構(gòu)成的植物名也很常見:
甜菜、蓋菜、莧菜、香菜、蒠菜、荇菜、蕺菜、芥菜、莼菜、蔊菜、堇菜等。
由科學語言中基本層次范疇概念構(gòu)成的植物名也有許多。如“木蘭綱—蓮科—睡蓮”屬于科學語言中的層次范疇等級,其中“蓮”被認為是基本層次范疇概念,相對于上位層次范疇“木蘭”與下位層次范疇“睡蓮”。語言中由“蓮”構(gòu)成的植物名較多:
穿心蓮、蓮花白、西番蓮、雪蓮、轉(zhuǎn)日蓮、王蓮、并蒂蓮、榴蓮、蓮霧、馬蓮等。
當然,由于科學研究的專業(yè)性需要,生物科學性詞典中收錄大量的植物專名,其構(gòu)詞的屬語素有下位層次范疇概念參與,如由“睡蓮”構(gòu)成的下一級品種有“黃睡蓮”“白睡蓮”“紅睡蓮”“帝王睡蓮”“延藥睡蓮”“香睡蓮”等。但《現(xiàn)代漢語詞典》作為規(guī)范性和實用性的詞典,以詞語價值性與需求性的要求為原則收錄的現(xiàn)代漢語詞匯,不同于專業(yè)詞匯,表現(xiàn)出植物名構(gòu)詞上基本層次范疇概念參與度高的特點。
1.2 原型范疇的家族相似性
不同的植物,我們可以找到它們的共同特征,使得植物的各個范疇得以建立;也可以找到能使它們相區(qū)別開來的特征,對植物詞進行合理的分類,使人們更細致地認識植物。
菜豆[草本植物+嫩莢是常見蔬菜+可入藥]
蔥[草本植物+常見蔬菜+可做調(diào)味品]
姜黃[草本植物+可入藥+可做染料]
根據(jù)上述詞義分析,這3個植物都具有“草本植物”這個共同特征,可以將它們聯(lián)系在“草本植物”這同一范疇;根據(jù)“常見蔬菜”這個共同特征,可以將菜豆、蔥分類成“蔬菜”這同一范疇;根據(jù)“可入藥”這個共同特征,可以將菜豆、姜黃分類成“草藥”這同一范疇。這些就是范疇化的過程。
共同特征的存在是各類范疇形成的必要條件,而判斷事物是否能夠進入該范疇,依賴于事物與該范疇之間是否具有家族相似性(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這3個植物詞的共同特征是草本植物。共同存在的特征是各類范疇存在的必要條件,共同特征越多,具有的相似性越多,它們就會同時歸屬于層次不同的多個范疇中。如“可入藥”“可做調(diào)味品”是“菜豆”和“蔥”的區(qū)別特征,但“可入藥”卻是“菜豆”和“姜黃”的共同特征。這就是草本植物所反映出的家族相似性。
值得說明的是,許多范疇都是圍繞一個原型構(gòu)成的,同一個范疇的內(nèi)部成員的地位并不相等。例如《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對“水果”的釋義是:“可以吃的含水分較多的植物果實的統(tǒng)稱,如梨、桃、蘋果等。”[3]在“水果”這個范疇中,“梨、桃、蘋果”是典型成員,因為它們詞義中含有“果實可以吃”“含水分較多”這些主要特征。我們分析一下“橘”“甘蔗”的詞義:
橘[果實可以吃+果肉多汁+味酸甜+可入藥]
甘蔗[莖可以吃+多汁+含糖分多]
根據(jù)上述詞義分析可知,“橘”“甘蔗”都可歸于水果范疇。“橘”與水果的范疇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在水果范疇中屬于典型范疇。但是,“甘蔗”這種水果,它可食用的是莖,并不是果實,因此,它屬于水果的非典型范疇。
2 現(xiàn)代漢語植物名的隱喻認知
現(xiàn)代隱喻認知理論指出,隱喻的本質(zhì)就是用一種簡單、具體、為人所熟知的概念去理解復雜、抽象、陌生的概念,通過人類的認識和理解將一個概念域投射到另一個概念域。人們在認知未知植物時,經(jīng)常選擇與植物特征相似的概念為源域形成隱喻。我們考察《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142個含隱喻的植物名稱,發(fā)現(xiàn)這些植物名稱的隱喻按照“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認知原則,可以分為以人為喻、以動物為喻、以植物為喻和以其他事物為喻4個大類。
2.1 以人為喻
人們用人的活動、人體器官以及人物為參照物去描述植物,體現(xiàn)了“植物是人”這一概念隱喻。詳見表1。

表1 以人為喻的植物名
從表1可見:(1)以人物為喻的植物名最多,合計占58.6%,一般人物與傳說人物數(shù)量相同。在一般人物中比較注重人物的身份地位,如用君主的稱謂“王”來參與造詞的“王蓮”“王蔧”。劉師培《物名溯源續(xù)補》曾指出:“凡物之大者,或謂之王,蛇曰王蛇,鳥曰王騅。”[4]448只是劉氏未舉植物名例,植物“王蓮”是蓮的一種,以巨型奇特似盤的大浮葉為特點。“王蔧”本為草本植物,古書上指地膚,即掃帚菜,但其特點是叢株高大,又名“王帚”。《爾雅·釋草》:“葥,王蔧。”晉郭璞注:“王帚也,似藜。”古書中以“王”命名的植物名還有“王延”(即薯蕷、山藥)、“王棘”(棘之堅善者)、“王芻”(綠竹,即淡葉竹)。以人物命名的除表1列舉的外,還有“將軍”(大黃的舊稱)、“虞美人”等。此外,人們還以神話人物為始源域,突出植物的特征、習性等,如“仙客來”“仙人掌”“水仙”“佛手爪”等。
(2)在以人為喻的植物名里,人體器官隱喻數(shù)量較多,占比高達31.7%。這說明人對自己的身體結(jié)構(gòu)特征最為熟悉,所以是植物名稱隱喻重要的選擇對象。
(3)用人的活動(包括心理活動)和狀態(tài)參與造詞的植物名數(shù)量最少,是隱喻中較少使用的。
2.2 以動物為喻
人類對動物詞的認知應該要早于植物詞,因為動態(tài)的事物比靜態(tài)的事物更能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這形成了“植物是動物”的概念隱喻。詳見表2。

表2 以動物為喻的植物名
從表2可以看出:(1)植物名中以家畜類動物為喻體的數(shù)量最多,占總數(shù)的36.1%,說明家畜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馬”為隱喻的植物名最多,這有三種情況:一是以“馬”命名的名物多有“大”義。劉師培《物名溯源續(xù)補》:“物之大者,古人均稱為馬。于植物則有馬芹、馬藻、馬棘、馬蓼、馬藍、馬。”[4]449“馬藺”“馬蓮”因植株高大而得名,“馬藍”是植株高大的灌木狀板藍屬植物,“馬蘭”的葉子較長大。二是以馬的器官命名的植物。如“馬齒莧”因其葉互生或接近比并對生而類比為馬齒,“馬蹄蓮”塊莖外有漏斗狀的大型苞片狀如馬蹄,“馬尾松”針葉細長柔軟猶如馬尾。三是以馬身上的佩飾命名。如“馬鈴薯”的地下橢圓形塊莖頗似古代馬騎頸項上所懸掛的鈴;“馬纓花”是杜鵑花科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早春時節(jié),紅色花球競放枝頭,宛如馬頭披戴紅纓。
(2)植物命名反映龍鳳崇拜。龍鳳是中國神話中極具文化色彩的兩種神異動物。傳說中的龍,身長,形如蛇,有鱗爪,有長須,能興風降雨,為水族之長。漢語中存在大量的以“龍”命名的植物名,《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版僅收錄了4個,“龍眼”“龍爪槐”“龍膽”“水龍”。其中前3個植物名是用龍的身體部位和器官命名的,“龍膽”和“水龍”(全草入藥)還因其是藥用植物為示其藥效之神奇而去“攀龍附鳳”。日本學者森立之《本草經(jīng)考注》卷三“龍膽”條注云:“凡藥物以龍名者,皆假托其德以神其效耳。以似骨非骨名龍骨,以似眼非眼名龍眼,以似葵非葵名龍葵之類是也。龍膽亦復此例。張思聰云:‘龍乃東方之神,膽主少陽甲木’,此說甚拘。”[5]夏緯瑛也曾指出:“方術(shù)之家,故弄虛言,示其藥物之名貴,往往稱龍道鳳,如‘龍須’、‘鳳尾’之類,在在皆是。‘龍膽’的名稱,該當是此類,實即以其根苦如膽,而漫稱‘龍膽’耳。”[6]漢語中也有一些用“鳳”修飾的植物命名,但不如以“龍”命名的植物多,《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版收錄了“鳳梨”“鳳尾竹”“鳳眼蓮”“鳳仙花”4個植物詞。
(3)家禽類動物中以雞、鴨、鵝為喻體隱喻植物名稱,其中“雞”這種動物更為人所熟知,在植物名稱中更常見。如“雞冠花”“雞頭”“雞頭米”“雞樅”。
(4)蟲蛇類、鳥類、野獸類和魚類在現(xiàn)代漢語植物名中出現(xiàn)較少,但古代漢語中有大量的此類植物名。如以“虎”(虎杖、虎豆)、“鹿”(鹿藿、鹿梨)、“羊”(羊棗、羊桃)、“菟”(菟瓜、菟葵、菟絲)等命名的植物名較多。
2.3 以植物為喻
“以已知達未知”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人們在認識新植物時,往往根據(jù)該植物與已知植物的相似性,采用熟悉的植物作源域映射到新植物上,從而為新植物命名。詳見表3。

表3 以植物為喻的植物名
從表3可以看出:(1)以“草”為喻的植物以植株矮為主要特征。如“草棉”是植株矮的一種棉,“草莓”是植株矮的匍匐莖草本植物。
(2)以花類為喻的植物多是該植物的某部位形態(tài)似花形或某種花。如“西藍花”的外形像花,“蓮花白”指結(jié)球甘藍形似開放的蓮花,“桃花心木”因其心材為淺紅褐色似美麗的條狀花紋而命名。
(3)其他以植物為喻皆是基于兩種植物的形似類比。“地栗”是荸薺的別稱,因其球莖形似栗子而命名。“石刁柏”是百合科草本植物,但因其直立莖高可達1米,故以“柏”為喻;“楊桃”因其懸掛枝頭而稱為“桃”;“土豆”是馬鈴薯的地下塊莖似豆子而得名。還有的植物名是兩種植物的類比組合而成,如“楊梅”葉似水楊子,果實味同酸梅。
2.4 以其他事物為喻
其他事物是指除了人、動物、植物這些有生命的個體之外的無生命事物,種類繁多,范圍較廣。人們在這些事物與植物相似性基礎(chǔ)上,用事物作喻體來隱喻植物。詳見表4。

表4 以其他事物為喻的植物名
從表4可以看出:(1)以自然事物為喻的僅有“雪松”“冬瓜”兩個詞。雪松是因其初出的葉子有白粉像雪而得名;冬瓜成熟之際表層上會有一層白粉狀物質(zhì)好似冬天所結(jié)的白霜,故名“冬瓜”。
(2)除了自然事物以外,其他日常用品、食物、衣服佩飾、金銀珠寶都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關(guān)。其中以日常用品來隱喻植物的最多。如“霸王鞭”是因其莖粗壯,上有5個棱且有成行的乳頭狀硬刺而似鞭子;“喇叭花”即牽牛花,花形似喇叭。其他植物名“白茅”“裙帶菜”“玉簪”等命名緣由顯見。但也有些植物命名之由需要進行語源探析,如“大蒜”。“蒜”與“算”“筭”同源,皆有“計數(shù)”之語源義,“算”為動詞“計算”,“筭”為名詞“算籌”,“蒜”因其鱗莖分成瓣狀好似算籌,因而名為“蒜”。
(3)古代社會,金、銀是流通貨幣,玉是傳統(tǒng)文化中君子的象征。漢語中以“金”“銀”“玉”命名的植物名數(shù)量比較多,如常見的“金銀花”“銀杏”“玉米”等。也有以“元寶”“珍珠”命名的,如“元寶槭”“珍珠米”(即玉米)。
3 現(xiàn)代漢語植物名的轉(zhuǎn)喻認知
認知語言學認為:轉(zhuǎn)喻和隱喻一樣,是我們?nèi)粘P袨樯钪械囊环N思維方式,它以經(jīng)驗為基礎(chǔ),遵循一般系統(tǒng)的原則,組織我們的思維和行為,屬于一種認知方式和現(xiàn)象。轉(zhuǎn)喻映射應遵循鄰近原則和突顯原則才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漢語植物命名及植物名的詞義引申內(nèi)在機制就來源于這兩個重要原則。
3.1 轉(zhuǎn)喻的鄰近原則
同一認知域中的兩個范疇(概念)之間存在著密切聯(lián)系的原則就是鄰近原則。
3.1.1 轉(zhuǎn)喻的鄰近原則與植物命名
認知語言學認為,轉(zhuǎn)喻是人們通過一個概念實體來認識另一概念實體,在識解過程之中,目標體和轉(zhuǎn)喻都同時在人的概念世界中出現(xiàn)。人們在認識一種植物并為之命名時,還常常把該植物的功能、生長環(huán)境、來源產(chǎn)地等與該植物聯(lián)系起來,基于這種相關(guān)性的轉(zhuǎn)喻思維方式來命名新植物。
有些植物是根據(jù)其功用命名的:
燈芯草:莖的中心部分可用作油燈的燈芯。
益母草:全草入藥,善調(diào)女人胎產(chǎn)諸癥。
馬醉木:葉有劇毒,牛馬誤食后會發(fā)生醉態(tài)。
有些植物是根據(jù)其生長環(huán)境命名的:
以“山”命名的多生長于山地:山茶、山核桃、山里紅等。
以“水”命名的多生長于水里:水稻、水蔥、水仙等。
以“石”命名的多生長于石上:石蕊、石斛等。
以“地”命名的多生長于地下或貼近地面:地瓜、地栗、地菍、地衣等。
有些植物是根據(jù)其來源命名的:
以“西”命名的多來自于西域:西番蓮、西洋參、西紅柿、西藍花等。
以“洋”命名的多是國外的舶來品:洋白菜、洋蔥、洋槐、洋芋等。
以“胡”命名的多來自于西域等外域外族:胡豆、胡蘿卜、胡桃、胡椒等。
3.1.2 轉(zhuǎn)喻的鄰近性原則與植物名的多義項
事物之間具有普遍的聯(lián)系,由鄰近相關(guān)性原則映射下的植物名詞義轉(zhuǎn)喻有很多。
花卉: ?花草。?以花草為題材的中國畫。
“花卉”本指花草,因為中國畫中有一類畫以花草為題材,并且影響深遠,因而“花卉”就由這種相關(guān)的方式引申出了新的義項。
蒲: ?香蒲。?菖蒲。
“香蒲”與“菖蒲”本為兩種水生植物,因其生長環(huán)境和形狀相似而有了相關(guān)性,故“蒲”具有了兩個義項。
轉(zhuǎn)喻的鄰近性原則還反映在植物名中方言詞的存在,這也是一種相關(guān)性的表現(xiàn),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是在不同地域一些植物往往有不同的名稱。
大豆: ?一年生草本植物…… ?這種植物的種子。?<方>蠶豆。
提子2:?葡萄的一種,原產(chǎn)美國,比普通葡萄的個兒大。?<方>葡萄。
二是不同的事物由于某些共同特征選擇同一名稱來指稱。
糖蘿卜:<方>?甜菜。?蜜餞的胡蘿卜。
3.2 轉(zhuǎn)喻的凸顯原則
人的認知常常更加容易注意到事物中最突出的、最容易理解的屬性,這就是凸顯原則。
3.2.1 轉(zhuǎn)喻的凸顯原則與植物命名
張永言曾說:“每一種客觀事物或現(xiàn)象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或標志,比如一定的形狀、顏色、聲音、氣味等,但是人們在給它命名的時候卻只能選擇其中的一種特征或標志來作為根據(jù),而這種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任意的。”[7]
人們在為植物命名取象時,對其特征的選取顯然不是絕對的“任意”,而是如孫雍長曾指出的“根據(jù)選擇原則”:“客觀事物的性質(zhì)特征并不是單一的,一切認識和感知又總是根據(jù)選擇原則進行的。”[8]這種“選擇原則”,我們認為就是轉(zhuǎn)喻理論中的“凸顯原則”,即植物在某方面的凸顯特征。
刺槐:落葉喬木,枝上有刺,羽狀復葉,花白色,有香氣,結(jié)莢果。
根據(jù)隱喻理論,轉(zhuǎn)喻就是在同一概念的認知域矩陣中的某一域凸顯。植物“刺槐”的特征很多,由這些多個相關(guān)特征域組成了“刺槐”這個認知域矩陣,其中“枝上有刺”則是這一認知域矩陣中的凸顯域,它被人們用來選取作為命名取象。
一個植物有多方面的特征和標志,這就形成了多個凸顯域,這時人們關(guān)注點不同,就會產(chǎn)生不同的名稱,即同實異名。如“鳳仙花”有多個異名:
鳳仙花、金鳳花、鳳草:花形頭翅尾足俱翹然如鳳狀。
旱珍珠、急性子:種子圓如小珠,老的時候容易從種殼中迸出來。
菊婢:鳳仙花極易成活,子落地即可復生,舊時被視為花之賤品,又因與秋菊同開,故名菊婢。
指甲花:紅色花瓣可用來染指甲。
《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版收錄了其中的“鳳仙花”“指甲花”二詞。
3.2.2 轉(zhuǎn)喻的凸顯原則與植物名的多義項
轉(zhuǎn)喻的凸顯是詞義引申的重要產(chǎn)生機制,植物名的詞義引申表現(xiàn)為兩種情況:
一是植物部分與整體的互相替代。
金瓜:?草本植物 ……果實卵形……有十條縱棱。?這種植物的果實。
百合:?多年生草本植物,鱗莖呈球形,白色或淺紅色。……鱗莖可以吃,也可入藥。?這種植物的鱗莖。
“轉(zhuǎn)喻的主要功能則在于指代,即用一個事物來代替另一個事物。……例如在‘部分代整體’的例子中,有很多‘部分’代替了‘整體’。我們挑選哪個部分決定了我們關(guān)注整體的哪個方面。”[9]因為“金瓜”的果實具有明顯特征,所以用整株植物的名稱代指其果實。“百合”凸顯它的鱗莖,引申代替整株百合的義項。
二是植物所指中泛指與特指的轉(zhuǎn)換。
白菜:?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葉子大,花淡黃色。是常見蔬菜。品種很多,有大白菜、小白菜等。?專指大白菜。
茅草:?白茅。?泛指白茅一類的植物。
“白菜”的葉子大是其主要凸顯特征,這種凸顯性使得其中“大白菜”更具典型性,因此用“白菜”特指“大白菜”。“茅草”可專指“白茅”,又泛指白茅一類的植物,這表明基于轉(zhuǎn)喻的凸顯原則,植物名稱的泛指與特指可以相互轉(zhuǎn)換。
語言的認知分析是語言學中最具解釋性和解釋力的分析方法。運用范疇化、隱喻、轉(zhuǎn)喻相關(guān)理論來重新分析植物名的構(gòu)詞特點、命名緣由以及詞義引申機制,這是對植物名進行語言描寫與語言解釋相結(jié)合的一次嘗試,也為傳統(tǒng)語言學名物詞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