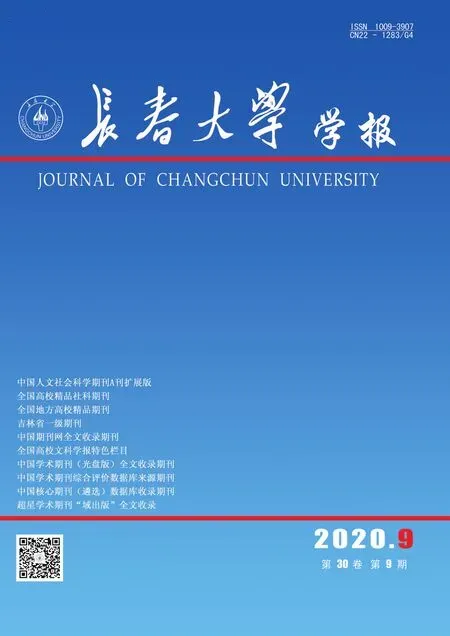從出土文獻(xiàn)看“因”的本義
范桂娟
(重慶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重慶 401331)
1 研究背景
“因”在上古時(shí)期有動(dòng)詞、介詞和連詞等多功能用法,使用頻率高,現(xiàn)代漢語仍在使用。“因”在《廣韻·真部》中釋為“于真切,平真影”,其在甲骨文中的字形為、、等。學(xué)界對(duì)“因”的來源和演化過程一直未有定論,關(guān)于“因”的本義有不同說法,但由于缺乏足夠事實(shí)支撐,這些說法尚難定論。

上述觀點(diǎn)中,《說文解字》的釋義應(yīng)該是“因”后起的引申意義,其他四家主要是根據(jù)字形進(jìn)行的推斷。那該如何判定呢?如果單就字形來看,上述觀點(diǎn)都似乎能說得通。當(dāng)前考察甲金文字用法時(shí),學(xué)界主要根據(jù)文字字形,結(jié)合文獻(xiàn)中的實(shí)際用例,并與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實(shí)情況進(jìn)行印證。上述五種觀點(diǎn)從文字字形來看似乎說得都有道理,但問題在于“因”在甲骨文中的用例不多,不太好驗(yàn)證真?zhèn)危裕诳疾熳中蔚耐瑫r(shí),還可以適當(dāng)結(jié)合出土文獻(xiàn)和傳世文獻(xiàn)的用法進(jìn)行印證。本文擬從出土文獻(xiàn)中“因”的字形演變、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用法及其在傳世文獻(xiàn)中的用法等三方面綜合探求其本義。
2 從字形演變看“因”的本義
學(xué)界提出的關(guān)于“因”的本義的各種看法,多數(shù)是從甲骨文字形來考察的,其中對(duì)“因”的本義釋為“死”或“囚”者居多,判定本義時(shí)主要依據(jù)字形表達(dá)的邏輯意義進(jìn)行推理。如葉玉森謂:“,孫詒讓釋,諸家釋囚……丁山氏曰:‘死本作,象人在棺材之中’。舊釋‘囚’,非也,森按丁氏釋死,其說甚新,惟井囗之象棺材,非生人,則棺與人均不應(yīng)作直立形。先哲造死字似應(yīng)作,象人臥于棺,較為明顯……核之卜辭文意,似應(yīng)仍讀囚也。”[2]92葉玉森主要根據(jù)字形為直立否定“死”義。
上述爭(zhēng)議在沒有充足語料支撐的情況下無法作出準(zhǔn)確判定,我們雖然可以借助字形和一般邏輯進(jìn)行推理,但還存在兩方面的不確定:一方面,字形與意義之間存在一對(duì)多的關(guān)系,字形大多是固定的,而對(duì)應(yīng)的意義卻是無窮的。另一方面,文字的形體和意義之間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并非是客觀世界的簡(jiǎn)單映現(xiàn)關(guān)系。因?yàn)槿说闹饔^認(rèn)知會(huì)作用于客觀世界并反映到字形上,這種主觀認(rèn)知簡(jiǎn)單借助字形往往難以推定,不同時(shí)期的人們對(duì)事物的認(rèn)識(shí)往往是發(fā)展變化的,這種歷時(shí)變化與共時(shí)情況往往存在差異,這就會(huì)給根據(jù)字形推定字義帶來困難。不過,如果我們擴(kuò)大字形考察范圍,并適當(dāng)考察字形的演變,就可以從一個(gè)更長(zhǎng)時(shí)間的字形演變用法中推斷其本來意義,也能大致辨別各家學(xué)說的優(yōu)劣。
考慮到“因”字“人”外面包圍部分隨體佶屈,均不太規(guī)則,如果解釋為“棺材”或“牢房”,其外形應(yīng)該為整齊的四邊形較為合理,其字形也不太可能將規(guī)整的四邊形改為不整齊的形狀,而如果解釋為“墊席”或包裹的“衣服”等,其形狀改換則比較隨意,比較符合字體形狀。所以單從字形上來看,如果解釋為名詞性的“墊席/衣物”或動(dòng)詞性的“在(墊席)上/(衣物)里”都似乎更能與字形契合。
3 從出土文獻(xiàn)的用法看“因”的本義
3.1 從甲骨文用法看“因”的本義
探求詞語的本義,最直接的方法是從早期文獻(xiàn)用例中直接找到其用法。我們搜尋了甲骨文合集、屯南、合補(bǔ)、花東、英藏等甲骨文文獻(xiàn),只在《甲骨文合集》中發(fā)現(xiàn)4例“因”,分別是:
(1)南方曰因,風(fēng)曰微。(合14294)
(3)鼎(貞):尋不因,辛囧,壬午王……(合21374)
(4)□申卜,囗鼎(貞):□子不因。(合21609)

后面一組例(3)和(4)解釋為“南方”顯然不行,似乎“南方”只是“因”的用法之一。趙誠認(rèn)為是借音字,由于“因”字形上似乎與“南方”沒有太大關(guān)系。我們同意這一看法。例(3)和(4)“因”用于否定詞“不”后面,“因”似乎可以判定為動(dòng)詞,但具體為何意,必須結(jié)合上下文才能準(zhǔn)確判斷,可惜上下文沒有足夠信息判定其準(zhǔn)確含義。因此,甲骨文的“因”只能大致判定有兩個(gè)用法:一是借用作名詞,專指“南方”;二是用作動(dòng)詞,但其具體語義還不清楚。前者作為名詞,從詞性和語義上來看,與傳世文獻(xiàn)中的動(dòng)詞、介詞及連詞的意義和用法相距太遠(yuǎn),不太可能為后世用法的源義;后者作為動(dòng)詞與傳世文獻(xiàn)中的用法比較接近,極有可能為“因”的本義。
3.2 從金文用法看“因”的本義
兩周金文“因”的使用頻率也很低,字?jǐn)?shù)不多,主要有如下兩例:
(5)妊氏令蟎事保氒(厥)家,因付氒(厥)且(祖)仆二家。(蟎鼎)
上面兩例,例(5)出現(xiàn)于西周中期,例(6)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晚期。其中的“因”,劉翔等認(rèn)為是表示“於是,就”義的副詞[6],武振玉認(rèn)為是承接連詞[7]。我們贊同武振玉的看法,上面兩例“因”位于無主句句首,承接有因果關(guān)系的前句,從意義上來看,“因”連接前后兩個(gè)分句,可認(rèn)定為承接連詞。例(5)出現(xiàn)于較早的西周早期,表明自殷商甲骨文之后,“因”的語義又發(fā)生了演變,可以用作語義較為空虛的承接連詞。
雖然金文中“因”的承接連詞用法顯然并非其本義,但很有可能由動(dòng)詞用法演化而來,因?yàn)樯瞎艥h語有不少承接連詞由動(dòng)詞演變而來的先例。如“以”本為表“提攜”“攜帶”的動(dòng)詞,后演變?yōu)槌薪舆B詞[8-9];“則”本為“(按照等級(jí))劃分(肉食)”的動(dòng)詞,引申為“法則”“效法”,后虛化為承接連詞[10]。而且從連詞的來源來看,動(dòng)詞和介詞是連詞的主要詞源,名詞演化為連詞的情況比較少見,這也表明“因”的本義很有可能為動(dòng)詞。
綜上,根據(jù)甲骨文“因”有動(dòng)詞用法,我們猜測(cè)“因”的本義為動(dòng)詞義。“墊席”“衣服”主要是承載或包裹人的,其意義與表示空間方位存現(xiàn)的動(dòng)詞義相關(guān)。因?yàn)閺募坠俏淖中蝸砜矗耙颉彪m與墊席或包裹的衣服有關(guān),但其本義不一定就是名詞性的“墊席”或“衣服”義,比如上面4個(gè)甲骨文用例均不能用表事物的“墊席”或“衣服”義進(jìn)行解釋。傳世文獻(xiàn)中“因”就有表“靠近、接近”的動(dòng)詞義,再加上《甲骨文合集》中4例用法中就有2例“不因”單獨(dú)作謂語,也可以據(jù)此推測(cè)“因”可能為動(dòng)詞,如果解釋為名詞“墊席”或“衣服”的話,顯然與文意不符。但如果將其本義確定為“在(墊席)上/(衣物)里”這樣的動(dòng)詞義,可能更符合語料實(shí)際情況,也可以與甲骨文用法相符。
4 與傳世文獻(xiàn)印證
從“因”的早期字形及演變情況來看,“因”形體佶屈,不太可能是“囚”或“死”義,有可能是名詞性的“墊席/衣物”或動(dòng)詞性的“在(墊席)上/(衣物)里”義。從其甲骨文用例來看,“因”有兩個(gè)用法:一是作為名詞的“南方”義,該義與字形無關(guān),多半為借音字;二是表義不明的動(dòng)詞用法。出土文獻(xiàn)具有語料真實(shí)性和年代確定性的特點(diǎn),有助于確定字詞的本義,不過出土文獻(xiàn)中“因”的材料有限,還難以完全確定“因”的本義,下面結(jié)合傳世文獻(xiàn)驗(yàn)證“因”的本義。陳會(huì)兵、胡龍秀根據(jù)“因”在傳世文獻(xiàn)中的“襯墊或覆蓋”義,認(rèn)為其本義應(yīng)為“像墊子(席子)之形”或“會(huì)墊子之意”[11]。但將“因”在多種出土文獻(xiàn)和傳世文獻(xiàn)中的用法相互印證,我們認(rèn)為“因”的本義不太可能為名詞義。
傳世文獻(xiàn)中的“因”雖然有動(dòng)詞、介詞和連詞等多功能用法,由于動(dòng)詞意義比較實(shí)在,它最有可能與甲骨文中“因”的功能接近。整理傳世文獻(xiàn)語料,發(fā)現(xiàn)“因”早期動(dòng)詞義有多個(gè),例如:
(7)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尚書·堯典》)
(8)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離婁上》)
(9)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左傳·定公八年》)
(10)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bào),是以來也。(《左傳·僖公十有五年》)
例(7)漢孔安國《尚書正義》謂:“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nóng)也。夏時(shí)鳥獸毛羽稀少改易。”[12]也就是說,《尚書正義》認(rèn)為這里“因”的意思是去往高地或田地勞作,幫助丁壯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實(shí)際上這里解釋的是“厥民因”整句話的意思,包括句子的隱含意義。如果單就該句的“因”來說,“因”單獨(dú)作謂語,顯然是個(gè)動(dòng)詞,可以理解為“靠近、接近”。例(8)“因丘陵”和“因川澤”的“因”也是“靠近、接近”之義,意為靠近丘陵、靠近山澤。后文“因先王之道”的“因”是遵循先王之道之義,“因”有遵循義。例(9)“因陽虎”意為投靠陽虎,“因”有投靠義。例(10)“出因其資”意為“出行依靠其錢財(cái)”,“因”有依靠義。
總之,上古“因”作為動(dòng)詞雖然有“靠近、接近”、“遵循”、“投靠”和“依靠”義,但總的來看,“靠近、接近”義是更具體和基本的意義,其他意義更抽象,可以認(rèn)定為該義的引申義。而且“靠近、接近”義也與《說文解字》對(duì)“因”的釋義一致。因此,傳世文獻(xiàn)中的“靠近、接近”義可以看成是該類型材料中最早出現(xiàn)的意義,這與出土文獻(xiàn)中的動(dòng)詞義正好契合,表明“因”的本義極有可能是動(dòng)詞義。
5 結(jié)語
出土文獻(xiàn)具有材料真實(shí)和年代確定的優(yōu)點(diǎn),探尋詞語的本義最有效和直接的辦法是根據(jù)早期出土文獻(xiàn)材料進(jìn)行判定。但由于各種原因,出土文獻(xiàn)文字考證復(fù)雜、材料數(shù)量有限,很難厘清某些字詞的意思,這時(shí)候可以借助傳世文獻(xiàn)進(jìn)行相互驗(yàn)證和探求。“因”的本義雖然有“墊席”、“死”、“囚”、“包裹”及“就”等不同看法,但從字形上來看,“因”字中“人”的外面包圍部分隨體佶屈,均不太規(guī)則,如果看成“棺材”或“牢房”皆不太合理;從“因”的甲骨文用法來看,其用法有兩項(xiàng):一是用作名詞,專指“南方”;二是用作動(dòng)詞,但其具體語義還不清楚。前者與“因”的形義無直接關(guān)系,多半為借音字;后者雖然具體語義不明,但和字形結(jié)合起來綜合推斷,“因”的本義有可能是表方位存現(xiàn)的“在(墊席)上/(衣物)里”義。結(jié)合傳世文獻(xiàn)與之印證,傳世文獻(xiàn)早期比較實(shí)在的意義為“靠近”“接近”義,該義與方位存現(xiàn)義存在較大關(guān)聯(lián)性,可以看作方位存現(xiàn)義向位移義的引申用法。因此,綜合傳世文獻(xiàn)早期用法、考慮甲骨文中的詞性及結(jié)合甲骨文字形來看,可以推測(cè)“因”的本義可能為表存現(xiàn)的“在(墊席)上/(衣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