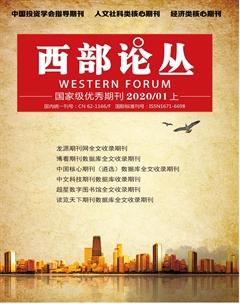周濟詞體論
摘 要:周濟作為常州詞派的重要代表,文學思想頗豐。其中不乏豐富而系統的詞體學思想,并較為集中地體現在《介存齋論詞雜著》與《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兩本詞話中。其詞體學思想有如下三個方面:“詞亦有史”的尊體觀,寄托說與詞體抒情特征及通達的詞體正變觀。
關鍵詞:周濟;詞體論;尊體;寄托說;正變觀
詞作為中國特有的古典抒情詩體,自從晚唐、五代發端,于兩宋達到巔峰,元、明時代陷入沉寂,后又于清代中興。在清代諸多詞派中,中晚期的常州詞派極為重要。不僅承接云間、浙西余韻進一步開拓了詞話理論,而且為晚清詞學的興盛完成了重要的積累。張德瀛在《詞征》中盛贊其為清詞三變之魁首:“茗柯開山采銅,創常州一派,又得惲子居、李申耆諸人以衍其緒,此三變也。”[1](P445)在常州諸家中,周濟對常州詞學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然學界在對其詞學思想的探究中,卻鮮有涉及詞體思想。本文試對其詞體觀予以剖析、梳理。
一、“詞亦有史”的尊體觀
尊體是常州詞派中頗為重要的思想之一。葉恭綽就曾在其《廣篋中詞》中說道:“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緒,力尊詞體,上溯風騷,詞之門庭,緣是益廓,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論清詞者,當在不祧之列。”[2](P121)而常州詞派宗主張惠言在《詞選序》中提出“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詞,故曰詞……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3](P1617)即是詩詞同源的觀點,并以此來尊崇詞體的地位。周濟經由董士錫而宗張惠言,自是認同其尊體思想。但周濟較之張惠言,其自身所發展的尊體思想更為深廣。周濟并未沿襲前人“詞為詩余”的思想,而是從歷史和文學本質這兩個維度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即“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4](P1630)這一思想被后世稱為“詞史”說,它從本質上提升了詞的地位,并成為常州詞派提綱挈領的理論之一。
筆者認為周濟的“詞史”說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詞與詩、文等文體相同,有自身發展演變的歷史,故而不能將其簡單地視作詩的一部分。文等文體相同,有其自身發展演變的歷史,而不能將其簡單地視作詩的一部分。自從晚唐五代填詞發端伊始,詞向來認為是小道,僅為歌舞宴席之上舞風弄月的小技。隨著詞創作的興盛,詞學理論也逐漸豐富,有前代詞論家提出詞是詩之余者。雖其旨亦在提升詞的地位,卻使詞成為詩之補充而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周濟這一觀點正是對詩余說的反駁。周濟始終堅持詞的獨立性,詞是與詩相同的抒情文體。無論是創作手法還是發展歷史,詞都有著獨立于詩的特殊性,對于詞的研究應該將其置于詞的發展脈絡之中整體觀之。這一點在其對姜夔詞作的品評中可探尋一二:“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為外道,由今思之,可謂瞽人捫籥也。稼軒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4](P1634)這一段論述,周濟雖旨在品評姜夔的詞作,沒有局限于具體詞作的點評和對比,也沒有以詩論論詞,從意境、風格等方面評價。而是獨獨選取了北宋詞到稼軒詞這一歷史階段,通過其間詞的發展變化,總結詞作的優劣標準。而后又將姜夔詞縱向地置于這一歷史時期進行論詞,以歷史空間的深遠宏觀論述詞人詞作,充分體現了周濟詞亦有史的理念。其二是指詞的創作與時代興衰相結合,詞同詩一般,也可以反映時代的興衰變化。周濟曾評王沂孫之詞“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4](P1635)“意能尊體”即“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4](P1630)正如前人評杜甫詩為“詩史”,周濟認為不止詩能存史,詞同樣能存史。為證其觀點,周濟列舉了四個例子。其中既有表達了對于未來有備無患的“綢繆未雨”,也有賈誼《新書·數寧》中對救亡天下的高聲疾呼;既提及了對天子與民同苦、重民輕君的贊許,也說到了對個人高潔品行的謳歌和認同。從個人到國家,由眼下到未來,林林種種皆是對于時代興衰之反映 。周濟以此四方面總述詞如何存史,指出了詞與詩截然不同的存史路徑,充分論證了以詞存史的獨特性。在此基礎上,周濟進一步論述以詞存史的獨到之處,即所得的“由衷之言”會受到性情、學問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的詞人會因性情、學問、境地各異,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描繪出紛繁真實的社會圖景,反映出多樣綜合的現實特點。因此優秀的詞作是時代共性和詞人個性的融合,是對歷史的真實反映,從而使得詞史“獨樹一幟”。
周濟的“詞史”說從詞亦有史和以詞存史兩方面,充分論證了詞在自身發展和表達功用上的獨立性,繼而從本質上尊詞體。周濟的詞史論不僅成為了常州詞派的綱領,也對后世劉熙載、謝章鋌的詞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寄托說與詞體抒情特征
周濟“詞史”說的尊體觀是從本質上對詞體特征的論述。此外,周濟還強調從創作上來突出詞體特征——寄托說。這是由張惠言的比興寄托說發展而來的。所謂比興寄托,實是傳統詩文的一種創作手法,可追溯到《詩經》的賦比興傳統,后來被發展成為詩體、文體的特征。而詞作為酒宴娛樂,在發端之時并無比興寄托之意,故多被視為小技。后代詞論家為了尊詞體,逐漸將比興寄托納入詞學理論。周濟的寄托說既繼承了前人尊詞體的思想,又沒有局限于表面,而是從深處挖掘了詞體的獨特審美抒情屬性。其寄托說可分為有無寄托說和寄托出入說。前者是對于初學者詞作提出的詞體特征要求,即“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4](P1630)。而寄托出入說,則是從詞體特征到詞境意趣的總結,即“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5](P1643)綜合有無寄托說和寄托出入說,可探究周濟詞體觀在詞作創作中的體現。
周濟有無寄托說既指明了創作的方向,也指出了詞體的特征。詞作首先要通過表里相宣做到有寄托。何為“表里相宣”?即物情結合。因此詞作并非無病呻吟,而是作家把自己的內心情感,通過寄托在外物上加以體現,突出了詞體的抒情性。無論是寫景詞還是詠物詞,本質都是情感的寄托。寄托情感是詞不同于詩言志、文載道的獨特審美屬性。詞體的抒情特征在周邦彥《蘇幕遮》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他將自己內在的思鄉之情,借助魚郎、輕舟表現得淋漓盡致。將扶搖輕舟的表象同濃烈的思鄉之情融合,以一二小物寄托詞人渾厚的情思。周濟評周邦彥詞為“美成思力,獨絕千古”[4](P1632),正是出于寄托情思的詞體特征。有寄托只是第一步,無寄托是更高的境界。其意并非在創作中放棄寄托,而是指創作過程中應逐漸擺脫技巧的生硬束縛,將自身的情感融入更豐富的藝術形象之中。表現在詞體特征上,即是不刻意選取寄托之物表達情思,不故意賣弄技法渲染情感,而是把主觀情思渾然融入于客觀事物。此時的詞作雖然仍有寄托之意,但所寄托情思多重而不確定,達到了含混的藝術境界。正如其所論述:“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沈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則講片段,次則講離合,成片段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4](P1630)周濟評易安詞“閨秀詞惟李清照最優,究若無骨。”[4](P1636)之所以認為其閨秀詞最優,正是因李清照《聲聲慢》中以黃花這普通一物,達到了含混無骨的抒情境界。
此后,周濟提出了著名的寄托出入說,其中提及的“渾化”更是成為了常州詞派對于詞作的標準和要求。“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謦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舫鯉,中有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5](P1643)在這一段完整的論述中,周濟將無寄托說,進一步發展為不僅僅是詞體的抒情屬性,而是詞人創作手法與詞體藝術特征的統一。周濟承接有其無寄托說,把寄托說融入創作過程,即“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5](P1643)周濟此處強調的是如何將主觀情思與客觀物象融合,即“以無厚入有間”。表明詞人需要將自己的情思巧妙無痕地融入那些物象之中,通過情感與物象的融合,達到無厚入有間的境界,并進一步升華情感。周濟認為這樣的詞作僅僅完成了寄托入的階段,那么寄托出的階段呢?周濟表明寄托出的階段,需要平淡樸素卻蘊藉深遠,感情豐富卻無一明晰,呈現出含混渾化的意境,此時就達到了寄托出的藝術境界。周濟關于渾化多有論述,“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5](P1644)“針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4](P1631)周濟所指的“渾化”是詞抒情特征的最高標準,不僅要做到有限的物像蘊含無限的情思,還要做到單一的話語寄托多重的幽思。以“渾化”為詞作話語的蘊藉屬性,以此體現詞抒情的獨特審美特征。可以看到周濟既把渾化無痕視作詞體抒情特征的集中體現,更把渾化作為詞作抒情最高境界,要求詞作全無寄托痕跡,達到主客渾融的境界。
從有無寄托說到寄托出入說,周濟從詞體特征出發,發掘出詞體渾化無痕的抒情特征,從而將抒情作為了詞體的獨特屬性。而實現詞體抒情特征,就是要從創作上做到無寄托、寄托出。
三、通達的正變觀
正變論原是詩學命題,后被詞學家引入詞學領域,成為詞學史上的經典話題。關于詞體風格何為正變的爭論,早在兩宋時期就有端倪,于明代正式提出,終清一朝的詞派、詞學家,無一不談正變論。作為常州詞派的重要人物,周濟關于詞體正變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正變觀亦是他詞體思想的重要部分。
清初云間詞派以婉麗為正,后浙西詞派提出以清空為正,清朝的正變論可謂繁雜豐富。常州詞派宗主張惠言最早提出了常州詞派的正變論,即以雅正為正。張惠言所說的雅正并非是簡單的詞體風格,更是探源風騷。要以《詩經》風雅為正,并合乎諷諭美刺的文學傳統。反之則為變,而變即是失常。面對諸多詞體正變觀點,周濟提出了更為通達的正變觀。簡言之,以蘊藉深厚為正體,采眾家為正體之次。這一思想在其《詞辨》中有充分體現。周濟依“蘊藉深厚”為詞體之正,在卷一“正”中錄入了溫庭筠、秦觀、歐陽修、周邦彥、吳文英等人;而將李煜、蘇軾、辛棄疾、姜夔等人收錄在卷二“變”中。雖然周濟也是以蘊藉深厚為標準區分正變,但其對于“變體”的態度與張惠言的通盤否定截然相反。周濟在卷二中將李煜列在首位,并稱“南唐后主以下,雖駿快馳騖,豪宕感激,稍稍漓矣;然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厲剽悍之習,抑亦正聲之次也。”[4](P1637)可以看到,周濟只是以蘊藉深厚作為區分正體和變體的標準,并未對變體加以過分貶低,對李煜也給予了駿馳豪宕的評價。周濟稱變體為“正體之次”,即為正體詞的補充,可見他對變體詞的肯定贊許。
但正如潘曾偉在《周氏詞辨序》中所言:“其所選與張氏略有出入,要其大旨,固深惡夫昌狂雕琢之習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張氏之意也。”[6](P312)周濟早年所作《詞辨》仍多宗常州詞派前人思想,而其后期所作的《宋四家詞選》中思想更為成熟。其中言道:“余不喜清真,而晉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抵牾者一年,晉卿益厭玉田,而余遂篤好清真。”[4](P1637)由此可知,周濟思想的形成亦有一個變化過程。在其《宋四家詞選》中,周濟進一步突出了詞體的現實性和抒情性特征,給予柳永較高的評價。“柳詞總以平敘見長,或發端,或結尾,或換頭,以一二語勾勒提掇,有千鈞之力。”[5](P1651)此時周濟在擺脫張惠言的以雅正為正的詞體正變觀后,逐步形成了自己以蘊藉深厚為正的詞體正變觀。這一正變觀較之張惠言、以及之前浙西竹垞、云間臥子都更為通達,對于向來不受重視、贊許的詞人也都能給予客觀的評價。除了上文提到的柳永,對于豪放派詞人蘇軾、辛棄疾周濟也都評價頗高。周濟認為辛棄疾“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4](P1633)對其詞也評為“斂雄心, 抗高調, 變溫婉, 成悲涼”[5](P1643),對于李清照等人不以為然的蘇軾,周濟也高度贊賞“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4](P1633)無論詞家詞作是否符合蘊藉深厚的標準,但凡其詞有獨到之處,能夠存史抒情,那么周濟均視為“正聲之次”給予相應的評價。由此可以充分辨析周濟以蘊藉深厚為正體,采眾家為正體之次的詞體觀的通達豁然之處。
周濟的詞體正變觀與其詞史說、寄托說相輔相成,形成了完整的詞體思想。周濟通過詞史說以尊詞體的現實性,寄托說強調詞體的抒情性,正是建立在詞體現實抒情特征之上,才形成了周濟通達的詞體正變觀。
參考文獻
[1] 嚴迪昌.清詞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2] 葉恭綽.廣篋中詞[M].傅宇斌,點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3] 張惠言.張惠言論詞[M]唐圭璋.詞話叢編:第二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6.
[4]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M]唐圭璋.詞話叢編:第二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6.
[5]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M]唐圭璋.詞話叢編:第二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6.
[6] 方智范,鄧喬彬.中國詞學批評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作者簡介:黃凱琦(1993-),女,漢,遼寧本溪,碩士研究生,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