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jīng)》中的音樂(lè)批評(píng)擷英
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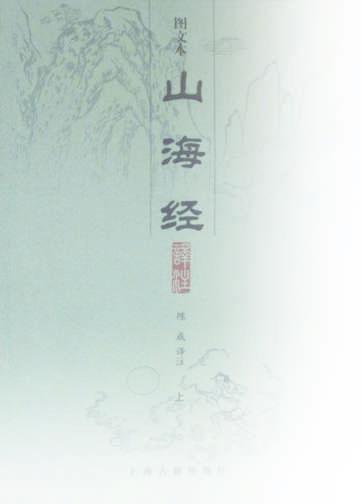
《山海經(jīng)》[1](誕生年份不詳),志怪古籍,被譽(yù)為“荒誕不經(jīng)的奇書(shū)”。關(guān)于作者,古人認(rèn)為該書(shū)是由“戰(zhàn)國(guó)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shū)》《晉乘》以成”;前人認(rèn)為乃禹、伯益,經(jīng)西漢劉向、劉歆編校后傳世。現(xiàn)多認(rèn)為,該書(shū)成書(shū)并非一時(shí),作者亦非一人,可能是由戰(zhàn)國(guó)中后期至漢代初中期楚國(guó)(或巴蜀人)集體成果累積而成。全書(shū)現(xiàn)存18篇,藏山經(jīng)5篇、海外經(jīng)4篇、海內(nèi)經(jīng)5篇、大荒經(jīng)4篇,其余篇章內(nèi)容散佚。
《山海經(jīng)》的內(nèi)容主要是民間傳說(shuō)中的地理知識(shí)(諸如:山川、道里、民族、物產(chǎn)、藥物、祭祀、巫醫(yī)等)與人文傳說(shuō)(諸如:夸父逐日、女?huà)z補(bǔ)天、精衛(wèi)填海、大禹治水等,大量的膾炙人口的遠(yuǎn)古寓言故事與神話(huà)傳說(shuō))。《山海經(jīng)》的版本較多,最早版本為晉·郭璞《山海經(jīng)傳》,最早收錄書(shū)目的是《漢書(shū)·藝文志》。《山海經(jīng)》的書(shū)名,最早見(jiàn)于司馬遷《史記·大宛傳》:“至禹本紀(jì)《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這表明在太史公之前,《山海經(jīng)》的文獻(xiàn)記載早已存在。結(jié)合文本內(nèi)容、語(yǔ)言記述等情形,或許可以發(fā)現(xiàn)史上的諸多“牛人”(諸如:老子、莊子、秦始皇、屈原、《呂氏春秋》作者群體等)都讀過(guò)《山海經(jīng)》。這是因?yàn)椋豪像踉L(zhǎng)期擔(dān)任周朝“國(guó)家圖書(shū)館”的“館長(zhǎng)“,他應(yīng)該閱讀并整理過(guò)《山海經(jīng)》;莊周也可能讀過(guò)《山海經(jīng)》,因?yàn)椤肚f子》篇中大量浪漫主義的想象,靈感應(yīng)該獲益于《山海經(jīng)》中的此類(lèi)記載;秦始皇或許是因?yàn)槭軙?shū)中記載神話(huà)傳說(shuō)的影響,在秦帝國(guó)建立以后對(duì)海外求仙之道,篤信不疑、孜孜以求;《呂氏春秋》里面有大量與《山海經(jīng)》相同的內(nèi)容;屈子辭賦有許多內(nèi)容,也與《山海經(jīng)》一致。
在《山海經(jīng)》中,也有大量的文字記載涉及到上古時(shí)期音樂(lè)活動(dòng)。其中對(duì)音樂(lè)事項(xiàng)的記錄與評(píng)價(jià),都是基于原始音樂(lè)的審美經(jīng)驗(yàn)與價(jià)值取向而進(jìn)行的。
一、《山經(jīng)》中的批評(píng)片段
在《南山經(jīng)》的“山志”中,記載了方圓一萬(wàn)六千三百八十里范圍內(nèi)四十座山,其中有這樣幾段神獸歌唱能力的記載與評(píng)價(jià)的文字: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yáng)之山。其陽(yáng)多赤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niǎo)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niǎo)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niǎo)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jiàn)則天下安寧。
在這里向讀者講述了一種具有歌唱能力的怪獸——“鹿蜀”,這是原始人對(duì)具備超乎于人類(lèi)天性之一的歌唱能力的由衷贊嘆。這種贊嘆,也預(yù)示了人類(lèi)后來(lái)在音樂(lè)方面的進(jìn)化方向,往“仿生”方向發(fā)展的路向。在這座山上,還生存著一種“旋龜”。這種神龜發(fā)出“音如判木”的叫聲,先人對(duì)這些神獸的鳴叫聲的比喻與判斷,均是基于自己日常生活、生產(chǎn)的經(jīng)驗(yàn)所得而給出。這里的“音如判木”的比喻與評(píng)價(jià),就是結(jié)合自己日常勞作中砍木劈柴的音響經(jīng)驗(yàn)所得而出。在這里,還有一種“其狀如雞”的神鳥(niǎo),這種神鳥(niǎo)能夠“自歌自舞”,還是一種吉祥鳥(niǎo)——“見(jiàn)則天下安寧”。對(duì)神鳥(niǎo)的這個(gè)描述性歌舞能力的評(píng)價(jià),是基于作者群體對(duì)原始樂(lè)舞表演中“且歌且舞”的觀賞記憶與批評(píng)經(jīng)驗(yàn)。
《南山經(jīng)》中還有其他山中怪獸鳴叫情形的刻畫(huà)、描寫(xiě)與評(píng)價(jià)的記載,諸如:“柢山”中,有“其名曰鯥”的神魚(yú),“其音如牛”;“青丘之山”中,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的怪獸,“名曰灌灌”“其狀如鳩,其音如呵”的神鳥(niǎo),“其狀如魚(yú)而人面,其音如鴛鴦”的“赤鱬”(魚(yú)類(lèi))。“柜山”中,有“其音如狗吠”的“貍力”;還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痹”的“鴸”。“長(zhǎng)右之山”中,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音如吟”的“長(zhǎng)右”;“堯光之山”中,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音如斫木”的“猾褢”;“浮玉之山”中,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的“彘”;“鹿吳之山”中,有“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的“蠱雕”;“天虞之山”中,有“其狀魚(yú)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的“虎蛟”……。對(duì)南山地區(qū)各個(gè)“山頭”之內(nèi)生存著的神獸所發(fā)出音聲的特征,均結(jié)合自己生活審美經(jīng)驗(yàn),一一作出了比喻性的評(píng)價(jià)與判斷。
在《西山經(jīng)》的“山志”中,記載了方圓一萬(wàn)七千五百一十七里范圍內(nèi)七十七座山,其中也有山中神獸鳴叫情形的刻畫(huà)、描寫(xiě)與評(píng)價(jià)的記載,諸如:“英山”中,有“其狀如鱉,其音如羊”的“鱧魚(yú)”;“鐘山”中,有“其狀如雕而墨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的“大鶚”,一旦有兵亂,山神的兒子“鼓”變身為“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的“鵕鳥(niǎo)”;“泰器之山”中,有“其音如鸞雞”中,有“狀如鯉里,魚(yú)身而鳥(niǎo)翼”的鰩魚(yú);在“槐江之山”中,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之“天神焉”;在“西王母所居”之“玉山”中,有“其音如吠犬”的“狡”;還有“其音如錄”的“勝遇”;在“章莪之山”中,有“音如擊石”之“猙”,還有“音如榴榴”的“天狗”;在“騩山”中,有“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在“天山”中,“有神焉,基狀如黃囊,赤如丹水,六足四翼,渾敦?zé)o而目,是識(shí)歌舞,實(shí)為帝江也”。“翼望之山”中,有“名曰讙”之“獸焉”,“其音如奪百聲”;在“剛山”中,有 “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之“神”;在“剛山之尾”,有“鼠身而鱉首,其音如吠犬”之“蠻蠻”;在“曲之山”中,有“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之“駁”;“邽山”“其上有獸”,“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獆狗”;還有“嬴魚(yú)”,“魚(yú)身而鳥(niǎo)翼,音如鴛鴦”;“鳥(niǎo)鼠同穴之山”上,有“魮之魚(yú),其狀如覆銚,鳥(niǎo)首而魚(yú)翼,音如磬石之聲”。對(duì)西山地區(qū)各個(gè)“山頭”之內(nèi)生存著的怪獸的音聲特征,均結(jié)合自己生活的審美經(jīng)驗(yàn),一一作出了比喻性的評(píng)價(jià)與判斷。
在《北山經(jīng)》的“山志”中,記載了方圓二萬(wàn)三千二百三十里范圍內(nèi)八十七座山,對(duì)北山地區(qū)各“山頭”之內(nèi)生存著的怪獸的音聲特征,結(jié)合自己生活的審美經(jīng)驗(yàn),均作出比喻性的評(píng)價(jià)與判斷。諸如:“其音如梧”“其音如呼”“其音如鵲”“其音如吠犬”“其音如榴榴”“其音如羊”“其音如獆犬”“其音如詨”“其音如鼓柝”“其音如嬰兒”“其音如鳴雁”“其音如叱”“其音如豚”“其音如牛”等。……在《東山經(jīng)》《中山經(jīng)》中,均是如此這般比喻、形容。這種結(jié)合主體生活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批評(píng)對(duì)象聲音特征的文字性描述的做法,是早期原始形態(tài)音樂(lè)批評(píng)的基本做法。
二、《海外經(jīng)》中的批評(píng)片段
在《海外西經(jīng)》中,有“夏后啟”(公元前2084年—公元前2006年,也稱(chēng)夏啟、帝啟、夏后啟、夏王啟,他是禹的兒子,夏朝第二任君王)在“大樂(lè)野”(或“大遺野”)夏朝宮廷組織表演“九代樂(lè)舞”的記載:
大運(yùn)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niǎo)北。大樂(lè)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乘兩龍,云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huán),佩玉璜。在大運(yùn)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刑天與帝至此爭(zhēng)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
這是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批評(píng)歷史文獻(xiàn)所見(jiàn)最早的,對(duì)上古早期樂(lè)舞表演現(xiàn)場(chǎng)展開(kāi)批評(píng)的“現(xiàn)場(chǎng)樂(lè)評(píng)”文本。在這里記載了夏后啟在“大樂(lè)之野”駕馭著兩條龍,飛騰在三重云霧之上,觀看“九代樂(lè)舞”的情形:夏帝“左手操翳,右手操環(huán),佩玉璜”。雖然沒(méi)有樂(lè)舞表演的具體文字記載,但通過(guò)夏帝“乘兩龍,云蓋三層”的“入場(chǎng)儀式”的輝煌氣度,以及手持、身著的配飾刻畫(huà),就從側(cè)面映襯了這場(chǎng)“九代樂(lè)舞”的規(guī)模之恢弘、藝術(shù)之精湛。這是古人樂(lè)評(píng)寫(xiě)作中,以側(cè)面映襯正面、以細(xì)節(jié)反襯整體的處理方法。后面這段“刑天舞”,刻畫(huà)的是樂(lè)舞表演中的一個(gè)場(chǎng)景:身強(qiáng)力壯,體型巨大的上古巨人,炎帝手下大將,被譽(yù)為“戰(zhàn)神”的刑天,手持巨斧、盾牌,與黃帝爭(zhēng)奪帝位,被黃帝斬去頭顱后,不甘失敗的他便以雙乳為眼、肚臍為口,再戰(zhàn)黃帝。這是對(duì)慘烈帝位爭(zhēng)奪戰(zhàn)的直接刻畫(huà)與表現(xiàn)的樂(lè)舞場(chǎng)景,創(chuàng)作者以這種恐怖的舞臺(tái)形象的描寫(xiě),借此營(yíng)造軒轅黃帝開(kāi)拓江山的艱難險(xiǎn)阻與豐功偉業(yè)。
三、《海內(nèi)經(jīng)》中的批評(píng)片段
《海內(nèi)經(jīng)》里有四個(gè)片段,都有重要的上古音樂(lè)活動(dòng)與批評(píng)的信息。
其一:“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鸞鳥(niǎo)自歌,鳳鳥(niǎo)自?xún)悾`壽實(shí)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這是對(duì)“西南黑水之間”“都廣之野”“鸞鳳”之鳥(niǎo)“歌舞”表演情形的記載、描述。
其二:“有鸞鳥(niǎo)自歌,鳳鳥(niǎo)自舞。鳳鳥(niǎo)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jiàn)則天下和”。這段記載是在對(duì)“鸞鳳”“自我”“歌舞”的記載之余,將“鳳鳥(niǎo)”之“文”的四種道德屬性,作出了“德”“順”“仁”“義”的定性評(píng)價(jià)。這種批評(píng)方法,對(duì)于有周一代以后盛行的音樂(lè)道德批評(píng)范式的確立,按下了“啟動(dòng)鍵鈕”。
其三:“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quán)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鐘,為樂(lè)風(fēng)”。這是對(duì)炎帝之孫伯陵“茍且之事”的記載:伯陵與吳權(quán)的妻子阿女緣私通,致使阿女緣連續(xù)三年懷孕,并陸續(xù)生下鼓、延、殳三個(gè)兒子。在這三個(gè)兒子中,殳發(fā)明了箭靶,鼓、延發(fā)明了鐘,并創(chuàng)作音樂(lè)作品,以此引領(lǐng)社會(huì)民風(fēng)。在面對(duì)這個(gè)批評(píng)對(duì)象的時(shí)候,作者卻只是忠于事實(shí)的記錄與書(shū)寫(xiě),不去進(jìn)行道德評(píng)價(jià)。
其四:“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山海經(jīng)》的這段記載,將帝俊(疑為《詩(shī)經(jīng)》里昊天上帝)視為上古眾神之始祖,始祖之后創(chuàng)造了樂(lè)器和音樂(lè)作品:帝俊生了晏龍,晏龍發(fā)明了琴、瑟兩種樂(lè)器,帝俊有八個(gè)兒子,是最早開(kāi)始創(chuàng)作音樂(lè)、舞蹈的人。這是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的起源(樂(lè)器起源、作品起源等)提供的一個(gè)新的觀測(cè)點(diǎn)。
四、《大荒經(jīng)》中的批評(píng)片段
在《大荒東經(jīng)》中,有“少昊”在“大壑”養(yǎng)育后人顓頊帝,并用樂(lè)的記載;還有黃帝在“流波山”得“夔”,以其皮制鼓的記載: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guó)。少吳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wú)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fēng)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在東海以外深不知底的“大壑”,是少昊(姬姓,名玄囂,遠(yuǎn)古華夏部落聯(lián)盟首領(lǐng))建國(guó)的地方,也是少昊在這里撫養(yǎng)顓頊成長(zhǎng)的地方,顓頊幼年玩耍過(guò)的琴瑟還曾經(jīng)丟棄在這里。這是發(fā)現(xiàn)最早的帝王以琴瑟樂(lè)器撫育后代的記錄。“棄其琴瑟”里的“棄”字,是一個(gè)表現(xiàn)主體主動(dòng)行為的動(dòng)詞,片段地映襯出這個(gè)時(shí)代人的音樂(lè)活動(dòng)。在進(jìn)入東海七千里的地方,有座流波山,山上有一種形狀像牛的野獸,青蒼色身體沒(méi)有犄角,僅有一只蹄,出入海水時(shí)就一定有大風(fēng)大雨相伴隨,發(fā)出的亮光如同太陽(yáng)和月亮,吼叫的聲音如同雷響,名叫夔。黃帝得到夔,用其皮蒙鼓,再以雷獸的骨作為鼓槌敲打之,發(fā)出的聲響傳到五百里以外,以此威震天下。這是我們所發(fā)現(xiàn)最早的關(guān)于鼓起源的記錄,這里的“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的文字,全面、細(xì)致地反映出此時(shí)的人們制作樂(lè)器的過(guò)程,以及樂(lè)器的使用方式、途徑等豐富信息。
在《大荒南經(jīng)》中,有“愛(ài)歌舞之鳥(niǎo)”的記載:“有臷民之國(guó)”“愛(ài)歌舞之鳥(niǎo),鸞鳥(niǎo)自歌,鳳鳥(niǎo)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有個(gè)國(guó)家叫臷民國(guó),這里有能歌善舞的鳥(niǎo),“鸞鳥(niǎo)”自由自在地歌唱,“鳳鳥(niǎo)”自由自在地舞蹈。勾勒的“鸞歌”“鳳舞”情形,展現(xiàn)出一派祥和的景象。在《大荒西經(jīng)》中,也記載了“沃之國(guó)”里“鸞鳥(niǎo)自歌,鳳鳥(niǎo)自舞”的“鸞歌”“鳳舞”的祥和景象。
在《大荒西經(jīng)》中,有一段顓頊之孫“處榣山”“作樂(lè)”,向社會(huì)輸出的記載:“有榣山,其上有人,號(hào)曰太子長(zhǎng)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zhǎng)琴,是處榣山,始作樂(lè)風(fēng)”。顓頊的孫子太子長(zhǎng)琴,長(zhǎng)期住在榣山里,以此作為創(chuàng)作基地,創(chuàng)作音樂(lè)作品往世間傳播,而風(fēng)行天下。這是對(duì)音樂(lè)家的創(chuàng)作生活模式、作品傳播途徑、以樂(lè)“移風(fēng)易俗”的記載與批評(píng)。
還有一段記載夏朝二帝——夏后啟,自天帝那里得到賜樂(lè)的情形:“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kāi)(即:夏后啟,漢人為避諱漢景帝名諱,改為“開(kāi)”)。開(kāi)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kāi)焉得始歌《九招》”。這里刻畫(huà)的夏后啟的形象是:耳朵上穿掛著兩條青色蛇,乘駕著兩條龍。他曾三次到天帝的天庭里造訪(fǎng),得到天帝的賞賜的天庭之樂(lè)——《九辯》《九歌》,啟便在“高二千仞”的“天穆之野”表演天帝賜予的大型樂(lè)舞《九招》。這段記錄與《海外西經(jīng)》記載的,夏后啟在“大樂(lè)野”表演“九代樂(lè)舞”的內(nèi)容相互映襯起來(lái)。
《山海經(jīng)》是一部極富浪漫主義幻想色彩的奇書(shū),而音樂(lè),恰恰也是善于表現(xiàn)這種境界的音響形式的藝術(shù)。該書(shū)以奇幻的文字記載方式,魔幻的書(shū)寫(xiě)表現(xiàn)方法,為我們了解上古音樂(lè)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方法、批評(píng)書(shū)寫(xiě)特征,打開(kāi)了一扇奇異之門(mén)。書(shū)中關(guān)于音樂(lè)起源于“天帝”的創(chuàng)造的記載,音樂(lè)起源于“勞動(dòng)”的比附方式,音樂(lè)起源于對(duì)自然世界客觀事物(生存動(dòng)物)的“模仿”的比喻方法,都給人想象力的展開(kāi),提供了啟發(fā)與參照。
注釋?zhuān)?/h3>
[1]《山海經(jīng)》采用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袁氏《山海經(jīng)校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