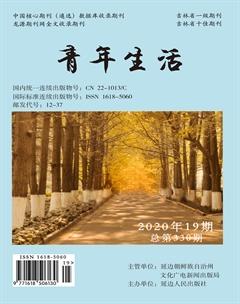我國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法律救濟研究
王馳杰
摘要:當下,我國正處法治政府建設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九大把“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確立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提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審明主體,拓寬監督渠道和方法,針對中國特殊國情,融入對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救濟。通過對《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的完善使得不按法律規定制定、修改和廢除規范性文件的行為也納入到復議和訴訟的范圍內。
關鍵詞:抽象行政不作為;行政訴訟;救濟
一、抽象行政不作為
抽象行政不作為是由抽象行政行為和行政不作為兩個法律概念組成的,而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是一組對應的概念。具體行政行為與抽象行政行為,原來也是學理上的稱謂。1989年《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1條、第12條法條中有對于具體行政行為的法條規定,但并未正面提及“抽象行政行為”。我們知道具體行政行為是與抽象行政行為相比較而存在的,而且行政訴訟法第12條在排除人民法院對某些事項的管轄權時,規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事項中有一項是“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規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定、命令。”可見,上述規定實際是將抽象行政行為界定為“行政機關規定、發布的”的行政行為,而且這種抽象行政行為包括制定行政法規、規章的行為在內。[1]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行政訴訟法第12條第(二)項規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是指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行政規范性文件。2000年的解釋中“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定、命令”,人們主觀的認為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界定。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概念,在法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從目前我國的理論界來講,還沒有形成統一意見,在立法上也沒有形成明確的法律概念。周邦慧[2]認為抽象的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負有法定的制定規范性文件的義務,卻沒有或遲延履行這種法定義務,在行為方式上表現為消極的行為。王世濤[3]也提出了近似的說法:抽象行政不作為是指具有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職權的行政機關沒有或者沒有適時地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或者沒有對不適合現實要求的規范性文件進行修改和廢止。魏波與肖登輝在之前的基礎上提出一點——抽象行政不作為是致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受到影響的行為。綜上所述我認為,抽象行政不作為就是具有法律所規定的特定義務且有作為可能的行政主體,不依法履行其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權的行為以及行政主體不依法修改或廢除與上位法相抵觸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由此對于不特定人或者其他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實際損害的行為。
二、我國的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救濟
依行使救濟的主管機關不同,行政行為的救濟方式分為立法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這三種救濟方式是目前主要的司法救濟方式。立法救濟中,以及《立法法》第九十六條“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關機關依照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的權限予以改變或者撤銷”和第九十七條規定“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權限”。在行政救濟中,《行政復議法》把具體行政行為替換為行政行為,這說明抽象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不作為也應包含在對行政行為的救濟范圍之內,但是有關抽象行政不作為的行政救濟目前還存在爭議。關于司法救濟的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的相關法律規定上。也有學者認為,既然“抽象行政行為”在“行政行為”的理解范圍之內,那么必然包含著擴大受案范圍的解釋可能性。有學者也認為概念的修正一定程度上解決行政行為概念的模糊性,對于抽象行政行為能夠進行司法審查,包括審查范圍的擴張、可訴性也提供了可行性基礎。但是抽象行政行為并未納入到第二章的“受案范圍”之中,只是將其規定在了第六章“起訴和受理”,能夠提起附帶司法審查。我國并未采取預防性或直接性的審查,而是提起訴訟的原告請求法院一并附帶審查。這種不徹底的改革在很多學者看來也是我國必經的流程,未來必將趨于完善。當出現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時候,百姓的最大期待就是被侵犯的權益得以恢復和保障,然而《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明確了司法審查結果只是轉送結果。根據大陸法國家如德國“最高法院如果判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有著普遍的約束力,且最高法院判決行政機關存在抽象行政不作為現實,那么行政機關必須以頒布法規所要求的方式予以修正行為”的準則相比較,就會發現我國目前法院只有建議權而非判決權。這一方面表現的是人民法院對行政權的尊重和司法權,但另一方面也表明附帶性審查不徹底性。
三、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救濟困境
(一)欠缺立法規范
抽象行政不作為具有危害性、隱蔽性、公益性等特點,這就要求相應的立法規范對其進行規制。抽象行政不作為得到本質仍是行政行為,根據法理,有“權利必有救濟”即當有規范性文件制定權的主體怠于行使其制定權或行政主體怠于執法時,公民的合法權益將會受到侵害或社會公益將會受到侵犯。這無疑要求依法行政必須實現“有法可依”,否則,行政主體的執法活動有“違法”或“不作為”之嫌。針對行政違法行為,我國現行的立法主要有《憲法》、《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賠償法》等,然而上述立法均沒有對抽象行政不作為進行界定、規制或者納入立法范圍。以《憲法》為例,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4];國務院可以“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和“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5];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權“改變”和“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不適當的決定[6]。當然,《立法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從上述法律條文看,我們很難找到抽象行政不作為的規范依據,上述立法僅針對“抽象行政行為”和“行政立法”行為做了規定。據此,行政抽象不作為立法仍處于立法空白狀態。
(二)欠缺司法救濟
司法是權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是公平正義的最后實現途徑。無司法救濟的權利只是一種法定權利或自然權利,只停留于法定狀態或紙質文本的權利永遠都是一紙空文。首先,就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救濟而言,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以及《國家賠償法》仍顯得力不從心。以新《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看,單獨對抽象行政行為違法提起司法審查仍被拒之于法律的救濟途徑之外,《行政復議法》對此處理亦大同小異。其次,公益訴訟制度之不完善。目前,我國的公益訴訟受理范圍主要限于環境行政執法領域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亦只限于特定的組織。這無疑增加了抽象行政違法不作為的救濟難度。
(三)欠缺法律監督
其實,行政權力就是一種必要的惡,其原因在于:首先,行政權的擴張或多或少會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針對此種情況,為了保護公民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控權”成了一種趨勢。其次,行政權的“錯位”異常明顯。這里的“錯位”是指行政主體行使職權時,應為卻不為或不應為而為之。抽象行政不作為就是行政權錯位的典型例證。試想,當“野雞大學”“網絡色情”等行為發生時,行政主體真的不知情嗎?再次,行政權的本質決定了執法的難度。行政權力除具有單方性、處分性、強制性等特征外,其還具有專業性的特征。這就使得行政權蛻變為一種居高不下的管理性權利,行政相對人淪為行政權力的客體,其結果就是“管理—服從”式行政仍然居于上風,公民無法參與到行政決定做出過程中。據此,行政主體和相對人之間的關系呈現主從之分,這種不平等加劇了公民監督行政行為的難度,對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的監督就是最佳例證。
四、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法律救濟
(一)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與立法救濟相結合
鑒于抽象行政不作為具有危害性、隱蔽性、間接性、抽象性以及專業性等特征,對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救濟就顯得尤為重要。目前針對研究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救濟,已有一部分學者開始進行研究。有學者認為,抽象行政不作為可以納入行政訴訟進行規范,其理由是,人民法院可以依據憲法相關條文,并可以在吸收、借鑒以及引進國外先進司法審查經驗之基礎上,使之與國內行政復議之經驗相銜接以實現救濟途徑之本土化[7]。有學者認為,當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社會秩序遭受行政不作為侵害時,公民可以在行政復議、立法途徑、行政訴訟等多種途徑中具有選擇權以期實現權利救濟[8]。有學者認為針對違法之抽象行政不作為,科學之立法救濟、高效權威之司法救濟和高效便民之行政救濟是公民不可或缺之維權手段[9]。
(二)完善行政公益訴訟制度
解決行政爭議的主要救濟途徑是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行政賠償。但三者都未將單獨提起的違法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于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救濟可以采取以下兩種思想進路:
1、將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納入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其原因在于,行政主體在行政方面更具專業性和職業化,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則具有隱蔽性、危害性等特征,前者正好是后者的最佳解決辦法;基于行政主體上下級之間的關系,將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納入行政復議之中既有利于發揮上下級間的監督功能,同時亦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最佳手段;其次,借《行政復議法》即將修改之際,可將違法抽象行政行為列入其受案范圍;另外,行政主體在解決違法抽象不作為時擁有自由裁量權,這是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無法比擬的。
2、將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納入行政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中。在我國,基于司法具有被動性、非獨立性和一定程度的非終局性,行政則具有主動性和擴張性;當立法出現諸如違法抽象行政不作為這樣的立法空白時,從比較法視野看,賦予公民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是大勢所趨,中國已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賦予公民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亦是踐行公約的內容。
(三)完善行政司法解釋體制
在我國行政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都是行政法的法源,前者是否屬于成文法淵源或制定法淵源在我國學術界存在分歧;后者則明確界定為不成文法淵源。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二者是否屬于制定法淵源,其對我國的法治實踐無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法院在進行司法審查時,依據法律和法規,參照規章,“援引”司法解釋進行審查。據此,行政司法解釋是有法律效力的,實踐中,“援引”某種程度上亦就是“依據”。
參考文獻:
[1]劉莘:《行政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版.
[2]周邦慧:《論抽象行政不作為》,載《行政與法》2001年04期.
[3]王世濤:《論行政不作為侵權》,載《法學家》2003年06期.
[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
[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
[6]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8條.
[7] 胡圣清,苑大超:《抽象行政不作為之可訴性研究》,載《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11期.
[8]魏波,肖登輝:《論抽象行政不作為的法律救濟——由中國首例公民狀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案引發的思考》,載《湖北社會科學》2004年01期.
[9]韓鳳然,李建波:《論抽象行政不作為及其救濟》,載《河北法學》2007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