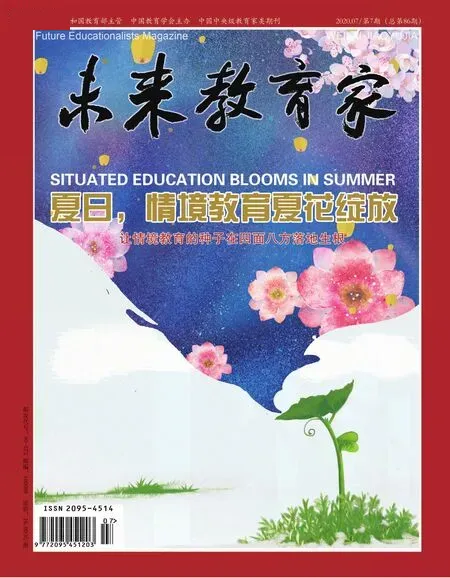李吉林:大寫的人道主義者
馮衛(wèi)東/江蘇省南通大學(xué)情境教育研究院、江蘇省南通市教育科學(xué)研究院
我與李吉林老師認(rèn)識(shí)的時(shí)間不算很長(zhǎng),前后15年,其間接觸較多,有幾年則過從甚密,中間又有一年多在她手下工作,朝夕相處。因而,盡管不是她的學(xué)生、徒弟和同事,但應(yīng)能列入她所親近的人之中。
記得小時(shí)候耳邊常響起毛主席的指示:“救死扶傷,實(shí)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李老師不是“白衣天使”,也不曾聽說她有過救死扶傷的故事,然而,當(dāng)提筆寫這篇文章的時(shí)候,隨即在我的腦海中迸出一句話,“李老師是大寫的人道主義者”。在我看來,在當(dāng)下,沒有任何一句話比這句更能精準(zhǔn)地刻畫李老師的形象和風(fēng)范,更能簡(jiǎn)明地概括李老師的精神與品質(zhì)。
李老師每一天日常生活、每一步教育行走都有人道或人道主義的因素、色彩和印痕,倘若她的精神、觀念世界里沒有它,那定然寫不出“情境教育的詩篇”,定然不能成為一個(gè)著名的兒童教育家。人們做李吉林及其情境教育研究,探源于此,或許會(huì)有“初極狹,才通人,復(fù)行數(shù)十步,豁然開朗”的經(jīng)歷與感受:這或許就是李吉林及其情境教育精神和力量的淵藪之所在。
柔軟的心地和強(qiáng)大的心靈
大凡事業(yè)取得巨大成功的女性都有著一顆強(qiáng)大的心,李老師也不例外。“文革”時(shí)期遭受沉重的打壓和侮辱,她沒有低下高昂的頭顱;進(jìn)行情境教學(xué)實(shí)驗(yàn)之初,有來自多方面的質(zhì)疑、一些人的譏諷和阻撓,她卻愈挫愈勇,奮力向前;憑一個(gè)小學(xué)教師的身份,在學(xué)界與人交往和對(duì)話,既表現(xiàn)出真誠、謙虛與好學(xué),又敢于亮出自己,樂于接受批評(píng)……她矢志不渝、果敢執(zhí)著的品質(zhì)鑄就了她事業(yè)上的輝煌。


2017年,李吉林情境教育展覽館揭牌。
李老師也有極為柔軟的一面——“見不得”貧窮與弱小的人。童年的她是一個(gè)苦孩子,自小失怙,與母親相依為命,飽受生活的艱辛,也因此更能體諒窮人和弱者的不易。“盛名之下,其實(shí)難副”,“難副”的是,李老師待人接物從沒有“名人”的架勢(shì)和作派,尤其在地位卑微的底層人士面前,是一個(gè)讓人親近的“大媽”形象。有一次,在巷子里和清潔女工閑聊,得知對(duì)方比自己小一歲,但樣子卻很顯蒼老,她為彼此同齡而處在不同生活境遇感到心酸不已,眼圈都紅了,之后格外關(guān)注這位清潔女工……類似事情很多,我多次見到她對(duì)身邊的臨時(shí)工關(guān)懷備至、對(duì)食堂工友關(guān)愛有加;她個(gè)人生活十分節(jié)儉,接濟(jì)他人卻非常慷慨。
尤為同情弱勢(shì)學(xué)生。一名已留過兩級(jí)的來自鄉(xiāng)村孩子來插班,她欣然接納并提前提醒全班學(xué)生不可歧視他,并盡力為他創(chuàng)造表現(xiàn)自我、提升自信的機(jī)會(huì),這使他進(jìn)步很快,在作文中的一些細(xì)節(jié)描寫流漾出一個(gè)小“暖男”的溫情,這正是師生真情互激與共鳴的結(jié)果。有關(guān)部門要為她錄制教學(xué)實(shí)況,為了達(dá)到最佳現(xiàn)場(chǎng)效果,對(duì)全體學(xué)生要有所取舍,她則執(zhí)意“一個(gè)都不能少”。課上,這名男生表現(xiàn)突出,憑著農(nóng)村生活的見聞與經(jīng)驗(yàn),對(duì)一名同學(xué)描述自然景物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錯(cuò)漏進(jìn)行了糾正和補(bǔ)充,成了本堂課的一個(gè)亮點(diǎn)。長(zhǎng)大后的他發(fā)展得不錯(cuò),他說:“是李老師給了自己一個(gè)新的生命。”1999年,李吉林老師榮獲“王丹萍教育獎(jiǎng)”,她拿出全部獎(jiǎng)金,為全校家庭經(jīng)濟(jì)條件困難的學(xué)生購買全年的《百家作文》……孩子們?cè)谒睦镎紦?jù)著極其重要的位置,而其中的弱者更是她時(shí)常牽掛和惦念的對(duì)象。
李老師深深憐及教材文本中窮人和弱者的形象,對(duì)之寄予豐富而深厚的情感。她是一位“抒情詩人”,情境教學(xué)以情取勝,以情促智,當(dāng)作品本身帶有一定的悲劇色彩或主人公是一個(gè)悲劇形象時(shí),課堂的情意氛圍更是濃得難以化開,不時(shí)掀起一陣陣情感高潮;在李老師的課堂,這類作品教學(xué)時(shí)幾乎都達(dá)至所有文本教學(xué)的情感巔峰,引發(fā)師生情感的巔峰體驗(yàn)。無論是教《月光曲》(貝多芬為一位盲姑娘和她哥哥彈奏,琴聲仿佛將兄妹倆帶到月光下的海邊),還是教屠格涅夫的小說《麻雀》(老麻雀為了拯救小麻雀,不畏獵狗、勇敢搏斗的情景);無論是《伏爾加河上的纖夫》,還是《賣火柴的小女孩》……這類課都成了李老師教學(xué)中的經(jīng)典課,抑或是經(jīng)典中的經(jīng)典。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面對(duì)窮人和弱者油然而生的同情、憐憫和惻隱之情中,她常常有一種悲劇的崇高感,有一顆博大深厚的仁心。有此人才有此心,有此心方有此情,李老師正是一個(gè)這樣的人,正有一顆這樣的心。
胡喬木把“人道主義”分為兩類,并對(duì)第二類(“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guī)范”)予以肯定與推崇。李老師對(duì)弱者懷揣一顆柔軟的心,這與其強(qiáng)大的心相輔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此種道義之情驅(qū)使她走上扶貧濟(jì)弱、盡可能地使每一個(gè)學(xué)生都獲得公平與和諧發(fā)展的教育之路上。霍爾巴赫將人道主義稱為“社會(huì)道德中的第一個(gè)道德”,我們也可以講,“同情”以及它所內(nèi)蘊(yùn)的人道主義情懷也是情境教育的“第一原理”。
使兒童成為教育活動(dòng)的“自愿助手”
同情心是人道主義的一種重要“構(gòu)件”,沒有同情心的人斷然不是人道主義者;當(dāng)然,有同情心也未必能成為后者,還要善于進(jìn)行更高層次的“共情”,即站在他人、對(duì)方等立場(chǎng)上來思考和行動(dòng)。李老師說,“我,長(zhǎng)大的兒童”,強(qiáng)調(diào)要“用兒童的眼睛去看世界,用童心去感受世界”。這就是“兒童立場(chǎng)”,我曾將之概括為,“回歸童我,以己度人”。成人如果不能“回到”自我已成過往的童年生活情境中,那將無法真切地體察當(dāng)下兒童獨(dú)特的心理世界,與“童心”終究有一層之“隔”。成人的“童心”需要自己尋找和喚回。當(dāng)然,除了“童心”,我們還能感受到李老師真摯的“慈意”。在老子那里,“慈”有另一層意涵——“以百姓心為心”,從這個(gè)角度和高度來理解,她的“共情”“童心”和“慈意”是“以兒童心為心”,進(jìn)而“以百姓心為心”,這與當(dāng)下中國所倡導(dǎo)和弘揚(yáng)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與精神一脈相承,完全契合,因此,可以將李老師身上所內(nèi)蘊(yùn)與表現(xiàn)出來的“童心”視為人道主義情懷的一種具象性表達(dá)和時(shí)代化轉(zhuǎn)換。
關(guān)于李老師和情境教育的兒童立場(chǎng)問題,有不少論述,在此我不一一展開,僅寫意性地說幾點(diǎn):其一,她進(jìn)行教學(xué)實(shí)驗(yàn)與改革,初衷在于反對(duì)不把兒童當(dāng)作人、而當(dāng)作某種工具的種種傾向與行為,她多次和我談到對(duì)中小學(xué)生學(xué)業(yè)負(fù)擔(dān)過重、童年缺少應(yīng)有的快樂等現(xiàn)狀的不滿與擔(dān)憂,事實(shí)上,情境教育的旨?xì)w之一正是歸還給孩子們應(yīng)有的童年幸福;其二,作為“四大課程”之一的野外情境課程,其主要內(nèi)容和表達(dá)方式是自然實(shí)踐,到“藍(lán)天下的學(xué)校”讀“三百頁大自然的書”,李老師是在隱藏目的的活動(dòng)中陶育“自然之子”,這是順性而行、適性而為之舉,孩子們既拓寬了知識(shí)視野,也陶養(yǎng)了與自然、與自我、與他人和諧相處的美好情愫;其三,兒童的天性中也有惰性、劣性以至惡性,問題不在于是否要消除與杜絕,而在于如何引導(dǎo)他們?nèi)ハc杜絕。李老師引導(dǎo)他們朝著正向的價(jià)值走去,“向著明亮那方”飛奔。所以,孩子們不是視學(xué)習(xí)為畏途,而是樂此不疲,有的剛滿10歲的孩子為了把作文寫完,居然不想出去活動(dòng),如此熱情又豈能搞不好學(xué)習(xí)……
烏克蘭一位學(xué)者認(rèn)為,“愜意性原則是蘇霍姆林斯基人道主義教育學(xué)的一條重要原則。愜意性是一系列自然、社會(huì)、教育心理的因素,這些因素決定兒童在從出生到長(zhǎng)大成人前這一階段,在良好的情緒環(huán)境中的生命活動(dòng)。”其實(shí),愜意(性)也是情境教育中的兒童最鮮明、最突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yàn)。有了這種積極體驗(yàn),他們又會(huì)反過來“對(duì)教育過程產(chǎn)生好感”,進(jìn)而使自己“成為我們?cè)诮逃麄冎械淖栽钢帧薄8耵敿獊喼逃野⒛{什維利認(rèn)為,讓孩子們成為如上所述的“自愿助手”,這是“人道主義教育的主要原則”。李老師的孩子們就是這樣的“自愿助手”;另一方面,所有的教育教學(xué)變革,最終都要指向于“自愿助手”的誕生、涌現(xiàn)與發(fā)展。
在渡人中度渡,以渡己來渡人
在《情境教育的詩篇》一書中,李老師說:“一句話即可概括全書,那就是,‘一切為了兒童’。”誠哉斯言。不過,如果把這句話改為“一切為了人”,亦無不妥,甚或更為全面:其一,兒童當(dāng)然不是他自己的完整狀態(tài),他要走向并最終成為“人”,“學(xué)校教育的理想是培養(yǎng)全面和諧發(fā)展的人,社會(huì)進(jìn)步的積極參與者”,“為了兒童”實(shí)質(zhì)上就是“為了人”;其二,情境教育除了指向于兒童的成長(zhǎng),也引領(lǐng)和帶動(dòng)了一大批教師的成長(zhǎng),在李老師所在的學(xué)校內(nèi)外,有一個(gè)龐大的情境教育“專業(yè)社團(tuán)”,有無數(shù)追隨她闊步前行的“情境人”,而情境教育本身就是一所“教師發(fā)展學(xué)校”,它趟出了一條扎實(shí)有效又別具特色的教師教育成長(zhǎng)之路,此方面的“育人”之功不可小覷,也是它使得指向兒童的“育人”行為不再是一個(gè)人的工作,而是一群或一類人的事業(yè)。

李老師對(duì)年輕一代的栽培、提掖與“化育”鮮有人及,也自有人說。作為一個(gè)“后來人”,我是“不幸中萬幸”——未能在更早一些時(shí)候來到她身旁,拜師學(xué)藝;卻在年屆不惑之時(shí)走上教科研崗位,從此有機(jī)會(huì)走近她,學(xué)習(xí)她,進(jìn)而加速了自我成長(zhǎng)與發(fā)展的步伐。我之所以在這十多年中能于學(xué)識(shí)和業(yè)務(wù)上不斷精進(jìn),離不開李老師對(duì)我的不吝指導(dǎo)和傾情幫助:她使我漸漸悟得基于一線教師實(shí)際,建構(gòu)實(shí)用而適合的草根化教科研方法的技術(shù)和路徑,逐步成為一名學(xué)有所長(zhǎng)、研有所擅的“專家”;吸收我參與她所主持的全國教育科學(xué)規(guī)劃“十一五”課題核心組,既產(chǎn)生了一批超越個(gè)人過往水平的成果,也憑借它及其他幾項(xiàng)不可或缺的條件躋身省教科研系統(tǒng)首批教授級(jí)中學(xué)高級(jí)教師之列;充滿信任,將著述《情境教學(xué)策略》一書的任務(wù)交給我和她的一位助手,并堅(jiān)決謝絕我們共同署名的美意,使這本凝聚了她許多心血和智慧的書成了我和她助手的“專著”;創(chuàng)造和提供機(jī)會(huì),讓我到國內(nèi)許多地方推廣情境教育,使我慢慢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人前人后給予我正面評(píng)價(jià)和認(rèn)可,使我這個(gè)書生氣頗濃的人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尊重……李老師似一棵可靠的大樹,使我倍覺安全;似一座堅(jiān)實(shí)的橋梁,使我通往成功;她是我人生的導(dǎo)師,使我心明路正,且行且遠(yuǎn)。沒有李老師,就不會(huì)有如今稍具內(nèi)涵、略有成果的我。而如我一般得益、受惠于李老師的人很多:度人度己,度己度人,這在她那里,妙合無痕,渾然一體。
李老師辭世前沒有交代任何“后事”,她的“生命絕唱”是對(duì)兒女的叮嚀:“要一輩子對(duì)別人好,幫助別人!”質(zhì)樸之至的話語既體現(xiàn)了一名共產(chǎn)黨人的坦白胸襟,也不無宗教般寬大為懷的仁慈心腸,更是人道主義精神的一次絢爛綻放!
“把人當(dāng)人看,使人成為人”
雅斯貝爾斯說:“人道主義基本上是一個(gè)教育問題。它以最純粹的形式和最簡(jiǎn)單的辦法把最深刻的人生內(nèi)容教給青年。”人道主義自成一種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大道至簡(jiǎn),可以用簡(jiǎn)明扼要的話語揭示其精髓與要義。有人把它概括為兩個(gè)基本的方面,“一是把人當(dāng)人看,二是使人成為人”,是的,這些在李老師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證與詮釋:“把人當(dāng)人看”,說到底是眼睛朝下,把窮人、弱者或孩子(未成年人)當(dāng)人看,給他們以眷注、關(guān)懷、憐愛、勉勵(lì)和支持,讓他們體驗(yàn)到人間的溫暖、人生的希望和生活的情趣;“使人成為人”,則是帶領(lǐng)他人向遠(yuǎn)方眺望,往高處攀援,讓人在不斷的“非其所是”的過程中成為新的、更優(yōu)秀的自我。李老師窮其一生做了許多大事業(yè)、大文章,可囊括于這兩句話中。我想套用著名文藝評(píng)論家錢谷融的一句話——“偉大的文學(xué)家也必然是一個(gè)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寫一段發(fā)自肺腑的文字,以此表達(dá)我對(duì)李老師深深的懷念與崇敬:“偉大的教育家也必然是一個(gè)偉大的人道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