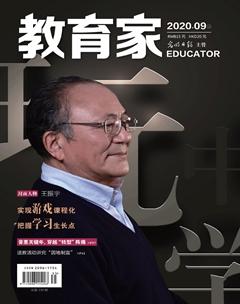為民辦園紓困,如何實現“三贏”
王妍妍 黃碩

目前,學前教育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正在征集中。業內人士對草案中涉及的如何突破幼兒園現有的公民辦兩套投入體制;怎樣解決民辦園總體運營成本與收入的不匹配問題;如果投資者不愿意投入資產變為捐獻資產,是否在立法前給民辦園投資者合理的補償退出機制和退出時間等較為關注。結合這一背景關注“民轉公”話題,似乎能發現某些共性。
針對“民轉公”過程中遇到的實際情況,我們邀請北京市京師(中山)律師事務所教育法律事務部主任龍鏡鋒、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律師肖燕從舉辦者的補償和獎勵、員工的接收和安置、保障民辦園的合法權益等角度建言獻策,真正為疫后的民辦園紓困。
“民轉公”過程中,應如何妥善安置民辦幼兒園的教職工?受轉型影響,幼兒園教職工被辭退是否能給予補償?請列舉一些具體措施。
龍鏡鋒:“民轉公”時,對教職工的處理方式一般有幾種。
第一種,教職工“原班人馬”與轉公后的幼兒園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的主體分別是公辦園和教職工。這是最理想的一種情形,既能夠避免教職工失業,又能夠穩定家長的情緒,更能夠緩解原舉辦者的壓力。
第二種,“民轉公”后,政府委托原舉辦者繼續管理幼兒園,由原舉辦者負責聘用人員組成教職工團隊實施保教工作。這種情形下,因教職工之前都是與原來的民辦園訂立勞動合同,而在“民轉公”時,民辦園已注銷,那么原舉辦者就需要另外設立一個合法的用工主體作為聘用方,重新聘用“原班人馬”,即由教職工與新設立的用工主體建立勞動關系。這種情形下,雖然保住了教職工的“飯碗”,但可能仍會產生工作年限的糾紛。
第三種,“民轉公”后,政府將幼兒園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全部收回,原幼兒園的教職工解散。這種情形下,根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的規定,作為用工主體的原幼兒園應當對解散的教職工支付經濟補償。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減人員二十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后,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用人單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
因此,“民轉公”時,原幼兒園應當依法“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后,裁減人員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并且應當依法向原幼兒園教職工支付經濟補償。對于這種情形,政府部門在“民轉公”時,為了爭取舉辦者的支持和配合,可以負責為幼兒園支付教職工的經濟補償金,這樣可以獲得“三贏”的效果。
對“民轉公”幼兒園的補償,核心問題是物業歸屬問題。但由于歷史原因,部分民辦園物業產權不明晰,如何對這部分民辦園舉辦者合理地進行補償?
肖燕:就我現在所了解的歷史原因導致的民辦園產權不明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物業權屬爭議,二是民辦園產權爭議。而且二者是緊密相連,無法分開的。
物業產權不清晰,是可以查清楚的,也應當查清楚。如果雙方爭議太大,僵持不下,可以考慮通過司法程序確認權屬。但是,司法程序走下來,也有弊端,即時間成本高,可能會影響“民轉公”的推進進度。至于如何補償,如果查清土地使用權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屬于民辦園,應按照市場價格給予回購或者補償;如果土地使用權和地上建筑屬于國家或者集體組織,需要對于加建的建筑物或者教育設施,進行評估,按照評估的價值進行補償;對于確實無法查清產權的民辦園物業,可以考慮采用協商補償的方式,在不超過市場價格的范圍內回購。
“民轉公”的關鍵是物業歸屬或者物業租賃期限問題,但如果民辦園歸屬或者舉辦者身份存在爭議,單純談物業問題的意義就不大了。實踐中有一類幼兒園,由社會主體運營,自負盈虧,但是登記的舉辦者為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或者集體組織。這一類幼兒園由于產權不清晰,在“民轉公”的過程中容易出現爭議。對于這一類幼兒園,我建議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標準做出判斷,確定舉辦者身份。確定舉辦者身份之后,按照既有的規則和當地的政策補償即可。
一些民辦幼兒園管理不甚完善,辦學資金緊張,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借款、擔保等問題。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應如何解決呢?
肖燕:幼兒園“民轉公”,從邏輯上存在兩個步驟,一是民辦幼兒園的注銷,二是公辦幼兒園的設立。由于債權具有相對性,因此不論是借貸產生的債務還是擔保產生的債務,都只會影響作為合同當事人的民辦幼兒園,與新設立的公辦幼兒園無關。但是,如果民辦幼兒園(一般性質為民辦非企業法人)債務沒有履行完畢,是無法完成注銷手續的。如果無法完成注銷手續,必然影響“民轉公”的進度。
這種情況的最好結果是民辦幼兒園及其舉辦者積極履行債務,債務履行完畢之后,注銷民辦幼兒園,順利完成具體民辦幼兒園的轉公程序。但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在存在較大債務的情況下,舉辦者的償債意愿和民辦幼兒園的償債能力都不可能太強。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區分不同情況,循序漸進,著力推進。
第一,幫助民辦幼兒園查清債務的真實性及產生原因。對于借款,重點查清借款的資金是否用于民辦幼兒園的經營,是否存在虛構債務的情況,是否存在利息約定過高的情況。對于擔保,重點審查擔保的合法性及責任方:非營利性的民辦幼兒園是不允許擔保的,簽署了擔保協議也是無效的;若擔保無效,承擔過錯責任后要考慮是否可以向債務人追償。
第二,引導資不抵債、無力辦學的民辦幼兒園走破產清算程序。《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五十八條明確規定:“因資不抵債無法繼續辦學而被終止的,由人民法院組織清算。”人民法院組織民辦學校破產清算,參照適用《企業破產法》規定的程序,并依照《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的順序清償。對于資不抵債、無力辦學的民辦幼兒園來說,走破產清算程序還債,公辦幼兒園接收和安置學生,是一個可行性較高的思路,一舉兩得,既解決了民辦幼兒園的經營困境,也完成了“民轉公”任務。
第三,合理設置并簽署“民轉公”協議。作為“民轉公”推進部門的行政機關,在設置和簽署“民轉公”協議時,要求民辦幼兒園的舉辦者清理債務,明確民辦幼兒園的債務與公辦幼兒園無關,可以考慮將履行完畢債務或者注銷民辦幼兒園作為支付補償款的條件。
民辦園轉型成公辦園后,有人表示,原舉辦方可以取得的僅是“參與辦園管理”權,而不再享有《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的民辦教育舉辦者權利。對此您怎么看?
龍鏡鋒:除了部分捐贈辦學的舉辦者之外,大部分民辦學校的舉辦者舉辦教育都有一定的經濟利益訴求和動機,其主要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2002)》關于“取得合理回報”的規定實現經濟利益訴求。
《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改后,民辦學校需實行分類管理,對于非營利性民辦學校,舉辦者沒有辦學收益權,也沒有剩余財產分配權;對于營利性民辦學校,舉辦者享有辦學收益權及剩余財產分配權。而“民轉公”后,幼兒園的主體法律性質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即改成了以政府為舉辦主體的非營利性的公辦園,原民辦園的舉辦者對轉型后的公辦園當然沒有辦學收益權及剩余財產分配權了。
部分地區在“民轉公”后,可能會委托原舉辦者繼續“參與辦園管理”,但這種模式實質上是一種委托代理合同關系,雙方可通過合同約定原舉辦者可以獲得一定的代理報酬,但該報酬與修法前的“合理回報”及修法后的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辦學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質。所以,轉型后,原舉辦者繼續“參與辦園管理”的,仍享有一定的管理權利,但已不能享有辦學收益權及剩余財產分配權。不過,原舉辦者可以與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約定比較高的管理報酬或者辦學效益獎勵。
在“民轉公”背景下,如何保障民辦園的合法權益,順利推進改革進程?
肖燕:“民轉公”的順利推進,民辦園及其舉辦者的配合和參與至關重要。我認為,激發民辦園及其舉辦者的積極性,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合理補償舉辦者。民辦幼兒園在辦學的過程中,舉辦者投入了時間、精力、資金或者資產,形成了一定的教育品牌,具有一定影響力,舉辦者有繼續承辦和獲利的心理預期。民辦幼兒園轉為公辦幼兒園,舉辦者存在直接或者間接損失,補償合情合理。補償金額的確定,建議綜合考量班級數量、物業價值(租賃物業的剩余期限)、幼兒園等級、教育設施凈殘值等方面的內容。可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補償標準,這是快速推進“民轉公”的前提。
解除民辦園注銷的后顧之憂。民辦幼兒園的注銷,可能導致出現退費、終止員工勞動合同和提前解除場地租賃合同三個方面的后果。從我了解的情況來看,民辦幼兒園終止與員工的勞動合同產生的賠償或者補償問題,是舉辦者顧慮最多的一點,特別是辦園時間長的民辦園舉辦者。因此,可考慮由當地財政來承擔因民辦幼兒園注銷產生的債務(終止勞動合同的補償金、提前解除租賃合同的違約金),解除舉辦者的后顧之憂,對于激發民辦園及其舉辦者的積極性意義重大。
設立進度獎勵機制。對優先完成“民轉公”手續的民辦園舉辦者設置一定獎勵,能有效發揮激勵作用和示范作用。可以考慮以民辦園的補償總金額為基數,按照不同的時間節點,設置獎勵比例,時間越早,獎勵比例越高。
龍鏡鋒:“民轉公”后,法律屬性必然發生改變;在利益實現上,原舉辦者不能取得辦學收益和剩余財產,利益主體必然發生改變。因此,在“民轉公”過程中,部分民辦園的原舉辦者出現了“不理解、不接受、不配合”的消極對待情形。如果國家能出臺兼顧原舉辦者利益的配套法規,讓原舉辦者能在辦學過程中得到比較合理的利益回報,那么,一方面可以繼續激發他們的辦學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其他社會力量參與整個學前教育的改革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