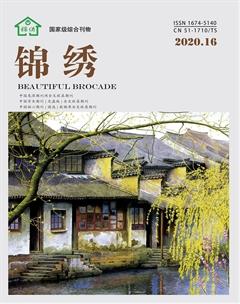文字高壓與文人書寫
摘 要: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統治者在政治上采取高壓政策以期完全掌控人民。作為政治高壓的衍生手段之一,文字高壓備受歷代統治者的“青睞”,中國歷史上的“筆禍史”淵源由此而來。在這種文字高壓下,歷代文士即使悲憤苦悶,在詩文中卻不能書寫一毫一厘。但部分士子身處黑暗社會之中對現實和社會有深刻的認識,于是借用“奇聞異事”來間接地達到諷刺政府的目的。本文將從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出發,進一步探討文字高壓下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的內涵與目的。
關鍵詞:文字高壓;蒲松齡;《聊齋志異》
文字高壓作為封建統治者加強君主專制的一種手段,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據《漢書》記載,楊惲因《報孫會宗書》而使“宣帝見而惡之”,遂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之刑。可見文字高壓自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就已初見端倪,隨后文字高壓歷經歷代政治局勢的轉變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至清代發展到頂峰。 清代統治者借助文字高壓大興文字獄,借此掃除了不服從其統治的漢族文士,達到了震懾人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在文學創作方面更加保守。然而一部分士子卻不甘滿清政府的統治,在親眼看清科舉之弊害、政府之腐敗、社會之黑暗后,于憤懣悲傷中以“奇形異事”的傳奇式文章來表達自己對于社會和現實的不滿與諷刺之情。其中,尤以蒲松齡的文言小說《聊齋志異》最為著名。
一、“才非干寶,情類黃州”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自序》中說:“才非干寶,雅好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意思是說,他的才能雖不如干寶,但和干寶一樣喜歡神鬼故事;他的性情和謫居黃州的蘇軾相近,一樣喜歡和人說神鬼的事情。
漢代儒學家董仲舒繼承《春秋·公羊傳》的“災異說”,提出了“天人感應”一說,強調“天人合一”,即天意與人意相通。簡單理解為天子在位期間若政通人和則感應祥瑞,若政治黑暗則感應災異。所以,民間百姓以天子執政時發生的災害多少來作為衡量天子是否圣明的標準。
干寶,西晉和東晉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傳聞中,他因有感于兩件異事而撰寫了志怪小說《搜神記》,以此來“發明神道之不誣”。一是,其兄干慶驟死,其友吳生認為其命不該絕,遂同死,其鬼魂至地府和閻王辯論,二人皆死而復生;二是,其父之婢女在父墓十年而不死。聯系干寶生活的時代背景,正是西晉、東晉交替之時,司馬氏家族自執政以來,出現了賈氏亂政、八王之亂以及五胡亂華等一系列事件,加上西晉皇帝自身無能,導致西晉社會一片黑暗。干寶生活在動蕩不安的西晉,借“天人感應”一說,通過神鬼靈異故事來諷刺西晉統治者之殘暴、政府之腐朽、社會之黑暗。
蘇軾因文字獄“烏臺詩案”而被貶黃州,而在黃州謫居的幾年蘇軾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心態,在其詩文創作中皆有所反映。無論是《念奴嬌·赤壁懷古》還是《赤壁賦》等,都表達了蘇軾曠達豪邁之情。然而蘇軾作為一個真實的人,在官場受挫之后的心情真的如他的詩文創作中所反映的一樣嗎?事實恐怕不是如此。深層剖析這“曠達”之情的背后,抒發的依舊是被貶之后的苦悶憤懣的情緒。為實現精神救贖,他一方面終日在安國寺“焚香靜坐,深自省察”[1],另一方面熱衷于和山野村夫、市井商販談論鬼故事,在談笑間排遣因政治失意而帶來的憂愁和痛苦,從而實現自我救贖。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干寶的《搜神記》、蘇軾“喜人說鬼”的癖好從表面上看是在寫鬼怪,實則是在寫政治,借神鬼故事從側面抒發對于政府的不滿情緒。生活在亂世的干寶親眼目睹西晉政治之黑暗,對于政府的不滿日益高漲,若直言不諱則可能會帶來殺身之禍,故借神鬼故事來諷刺統治者和政府;蘇軾因文字獄“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他深知“口業”過盛會招致災禍,所以他沒有將貶謫之后的消極情緒寫入詩詞,而是借莊禪哲理和“喜人談鬼”來作為精神救贖的途徑,以此來排遣政治苦悶。
二、花妖狐女,寄托人世之理想
滿清政府作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政權之一,自入關起便十分注重對于漢民族的掌控,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實行高壓統治。以文字獄作為排除異己的主要手段,以程朱理學、八股取作為控制文人士子思想的重要途徑。但滿清所提倡的程朱理學實際上是對理學的閹割和歪曲,一味宣傳倫理道德和三綱五常向人民和臣子灌輸其統治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一部分知識分子看穿了滿清政府的丑惡嘴臉,不愿與之合作,俯首稱臣,但迫于政治高壓,他們無法直接書寫自己內心的所感所想,便采取了一種消極的不抵抗不合作的態度。具體表現為對心學的提倡。心學起源于明中葉王陽明心學,強調心即是理,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但“由于強調心內求理,客觀上卻為否定天理,反對封建禮教打開了道路。”[2]心學進一步發展的,晚明時期公安三袁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性靈說”。他們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文學創作上提倡真情實感、直抒胸臆,具體為“將表現個體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容。”
回歸蒲松齡生活的年代,此時正是清朝日益加強封建專制統治的時期。清政府為加強統治所玩弄的手段蒲松齡心知肚明,同時他身處下層社會親眼目睹了政府的黑暗、官吏的無形、人民的苦楚,奈何面對高壓統治他卻無法言說心中的憤懣之情。在清政府的步步緊逼之下蒲松齡無法反抗,但在思想意識上卻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合作態度,于是《聊齋志異》應運而生。在理學為正統的背景下,蒲松齡遵從自己的本心,以談神論鬼的喜好進行文學創作的目的,正是反映了他對于滿清政府的不滿和消極抵抗情緒,同時也寄予了他注定無法實現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進而表現出了一種近乎天真浪漫的形態。
《聊齋志異》中的“狐女”形象陽光浪漫、熱情奔放,象征著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以彌補現實生活的遺憾,它注定是無法實現的。如《嬰寧》一文中塑造了一位天真爛漫、無拘無束的狐女形象,她勇敢追求心中所愛,最后與所愛之人王子服喜結連理。然而《嬰寧》并非只是純粹的愛情主題,嬰寧身世凄慘卻依舊笑對人間,在庸俗瑣碎的世事中表現出了一種超脫世俗、寵辱不驚的人生態度,這正合了“嬰寧”之名。蒲松齡對嬰寧的贊美正是寄予了他對復歸自然天性的老莊哲理的向往[3];
三、秋墳鬼唱,慨身世之多艱
清人王士禎在《題聊齋志異》一詩中評點道:“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點明蒲松齡之所以作《聊齋志異》是因為“厭作人間語”,即厭倦了寫人而去寫花妖狐怪,因為花妖狐怪比人更加可愛。事實真正如此嗎?答案是否定的。生活在極其重視思想文化控制的清代,蒲松齡的創作是不自由的,稍有不慎便會卷入政治刑事。但內心愁苦無以抒發只能更加痛苦,無奈之下他便只能借用“秋墳鬼唱詩”來排遣人生失意的憤懣,重點嘲諷滿清政府的殘暴與黑暗。
回到蒲松齡本人,他一生科場蹭蹬,屢試不中,面對黑暗的現實人生滿懷孤憤之情。尤其是在親眼目睹滿清政府的殘暴無形以及官場黑暗現狀后,他雖不能吶喊出聲,卻將力透紙背的憤慨借用陰司地獄呈現在世人面前。《聊齋志異》中除卻“花妖狐女”之外,還建構了一個筆調苦寒、壓抑凄涼的幽冥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蒲松齡將自己在現實人生中無法言說的懷才不遇的孤憤和有感于社會黑暗現狀的憤懣全部傾注在其中。
《葉生》一文中的主人公葉生一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場。”葉生其人才華橫溢卻一直懷才不遇,直至抑郁而終仍然不忘考舉,令人可笑的是在其死后魂魄授學于于公的兒子,于公子拿著葉生以往的所作文章高中進士,而葉生在于公子的幫助下才勉力中舉。葉生的遭遇正是蒲松齡一生的真實寫照,兩人都是才華橫溢卻次次考場失利,究其根本無非是封建科舉制度黑暗,考官昏聵;《考弊司》中描述考弊司堂下兩塊石碑刻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卻做著“不必有罪”,“例應割髀肉”的勾當,除非“豐于賄者”才可免除。蒲松齡正是以陰司冥間作為對照將人間的污穢不堪擺在了世人面前,將現實人間官府的黑暗渾濁和官吏的貪婪殘暴一針見血的撕裂出來。
蒲松齡生活在清朝初期,此時正是滿清政府打擊漢人士族集團、鎮壓地方起義的時期,并且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清朝已經是強弓末弩之時,所以在一步步加強專制統治的同時,政府內部組織已經開始出現問題。蒲松齡一生從科舉失利到坐館幾十年,親眼目睹滿清政府統治下滿目瘡痍的現實社會,在文字獄的威脅下他無法直接吶喊出聲,便只能借談神說鬼來諷刺康熙政府的黑暗。看似在寫狐鬼,實際在寫現實社會。在“花妖狐鬼”的世界中,一方面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另一方面在表達自己懷才不遇的孤憤之情的同時譏諷統治者的殘暴、政府官吏的貪贓枉法以及科舉制度的種種弊端。
參考文獻
[1]王水照 崔銘.蘇軾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171
[2]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53
[3]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73.
作者簡介:李潔(1998-),女,漢族,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本科,西北民族大學,古代文學,指導老師:孫守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