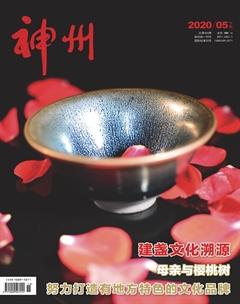炎涼世態中的一棵解憂草
蔡萍
摘要:《風箏誤》是清代文學家李漁創作的傳奇劇,作品從門當戶對的婚姻、女性低微的命運與險惡的仕途三方面為我們揭示了一幅世態炎涼的人生百味圖,但其卻受到了廣大市民的喜愛。文章就《風箏誤》的寫作旨趣入手,分析《風箏誤》被勾欄瓦舍接受和推崇的原因。
關鍵詞:李漁;風箏誤;美;情欲;解憂
引言
李漁在《風箏誤》的結尾寫道:“惟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他說自己寫《風箏誤》是為了讓讀者笑,但是細細品味之后,又有許多引人深思的地方,往往是在笑得最開心的時候襲來一陣悲涼之感。這部傳奇劇獲得了大團圓的結局,也一直被解讀成是愛情喜劇,但幽默情節掩蓋下的炎涼世態卻是真實可見的。明末清初,市井俗人多喜看識趣閑文,而這樣一部展現千瘡百孔的炎涼世態的戲劇為何在勾欄瓦舍會有如此大的市場?僅僅是因為幽默風趣嗎?這是筆者想探索的地方。
不若《牡丹亭》,雖生而死,死而生的故事情節離奇怪誕,但其揭示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追求性愛與自由這一具有本質意義的真實。《風箏誤》以編織貌似平常,其實離奇的故事情節為手段,結合大團圓式的結局,給人一種在表達虛幻不實的審美理想的錯覺。這恰恰是李漁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中國戲曲史上,王實甫、湯顯祖、徐渭、洪昇、孔尚任等戲劇大師均通過劇作把個人對人生、社會的思考及意義的探求傳達給觀眾,希圖以劇文為媒,在觀眾中尋求知音,甚至是能解決問題的智者。而對于李漁來說,賣書刻文是他主要的經濟來源,這使他不得不透徹地分析各個階層讀者的閱讀取向并且有意迎合之以獲得好的銷量。也就是說,《風箏誤》不是為自己而寫,而是為觀眾而寫,尤其是市井平民。
經歷了明清易代的時代劇痛之后,長期混跡于市塵,對市民階層文化訴求有著深刻體驗的李漁認識到“近日人情喜讀閑書,畏聽莊論”,那些深刻反映社會嚴酷現實的劇作固然能引發人們的深思,但嘲弄風月,反映虛幻理想狀態下才子佳人的戀愛經過和姻緣故事更能為經歷了動亂之苦的民眾所需。《風箏誤》以淺顯、機趣、適合舞臺表演、老嫗皆解的語言,描繪為百姓感興趣、能理解的故事內容,抒發切近普通百姓的人倫情感,營造出一種歡樂世俗的氛圍,恰恰為市井平民提供了消遣、解憂的良方。雖然炎涼不公的世態貫穿整個戲劇,但他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客觀真實地敘述社會現象,而不是極力展示自己的憂患意識并且希望與觀眾產生共鳴,他恰恰在為我們提供一種消除憂愁的方式,既然現實如此殘酷且無法改變,那我們就改變自己。對世俗情趣、對人正常欲望的肯定就是他給我們種下的解憂草。
市民運動的興起,工商階層和中小地主的運動,伴隨著經濟結構和社會風習的動蕩,釋放出自由、體認人性的精神能量。文學藝術領域形成一股浪漫主義思潮,與瀕死而頑固的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程朱理學發生劇烈沖突。李漁的《風箏誤》應時而生。這部劇未能達到情與理的合一,卻達到了情與欲的合一,體現了對世俗情趣的張揚,偏重塑造情欲美的理想人格,一方面表現在人物對“美”的執迷中。《風箏誤》中,幾乎人人都好色,情欲昭彰。丑公子戚友先公然好色,尋花問柳,娶了丑妻立刻就想納妾或者勾引小姨子。美公子韓生既喜功名又好美色,選妻講究才、韻、姿。中狀元后,騎馬巡街以色挑妻,語言十分苛刻;羞羞答答隨戚友先逛妓院又怨無國色。丑小姐愛娟好美男,為情欲和色欲所燃燒;美小姐淑娟懷春思春而寫和詩,鄙視丑男而想嫁俊美才郎。另一方面表現在人物身上有貼近普通百姓的人倫情感,散發著濃厚的市井氣息。如封建家長詹烈侯,一改官員嚴肅、冷峻的形象,李漁抓住其“長于治國,短于齊家”的特征,將這個在戰場上奇策迭出,在家中卻是“一日之中,吃得八九個時辰和事”,并且無奈周旋于兩個夫人之間的老頭兒寫的親切、可憐;詹家大小姐愛娟也一反傳統閨秀知書達理、嬌羞矜持的形象,而是蠢笨、丑陋,粗俗不自知。李漁雖然以達官貴族作為劇文敘事的主體,但他為我們展示的是貴族圈中與平民相一致的世俗情趣,消解了雅和俗的階級局限,給市井平民一種親切感和去追求真實欲望的沖動。對世俗情趣和情欲美的追求,正是對篤信“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的堅決批判,是對傳統審美趣味的消解與重構,也可以看出李漁為了使戲曲從普遍詩化、雅化、文人化走向平民化而做出的積極努力。這些融合市民審美趣味而塑造出來的具有世俗情趣的人物,他們超越了與各自身份相應的思想意識的約束,直接大膽地抒發個人真實情欲的做法,是性靈思潮脫離復古思潮而獨立發展的體現,是李漁在炎涼的世態中為民眾提供的消解憂愁的良藥,這也是在勾欄瓦舍的人們最為拍手稱快的地方。正因為如此,李漁雖未能在文學史上占據顯赫地位,但卻成為當時婦孺皆知的戲曲作家。
在這場喜劇所呈現的社會真實中“需要門當戶對才能結婚的觀念、女性低微的命運與險惡的仕途”,李漁讓我們看到了清初炎涼、不公的世態,但這不是他寫《風箏誤》的根本目的,他是想為我們提供一種消解憂愁的方式——不論是達官貴族還是市井平民,他們都有追求美和情愛的欲望,都有追求個人真實情欲的自由。當然,這也不失為是一種反抗炎涼、不公世態的方式,市井平民或許感知不到,但是,他們會嘗試去改變自己。
參考文獻:
[1]鄒皓羽.李漁作品的“智慧娛樂”——基于《風箏誤》中科諢使用的分析[J].四川戲劇,2018 (11):47-50.
[2]王思錦.淺談李漁《風箏誤》的喜劇性[J].戲劇之家,2017 (05):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