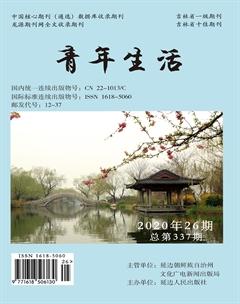劉震云的底層書寫與民間意識
摘要:近年來,底層書寫成為文學界關注的熱點。劉震云是一位長期堅持書寫底層的作家,他以平視的視角關照底層,對底層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機給予關注,并且上升到對整個鄉土中國的關照。本文通過描述社會動蕩不安、物資極其匱乏、權力被肆意濫用來展開討論底層人的生活之難,反映底層人的生存危機,分析底層人精神的孤獨與異化。從多重視角的表現方法、“擰巴”式的敘事手法和他平民化的語言風格三方面探討劉震云的寫作手法,展開了對劉震云作品中書寫風格的詳細分析。
關鍵詞:劉震云;底層人物;底層書寫;民間意識
現今,底層人民成為作家重點關注的對象,底層書寫成為文學界創作的一大熱潮。身為知識分子的劉震云,雖然已經脫離底層人的身份,但是他依然以平視的眼光關注著底層人的現實生活。陳曉明曾這樣評說劉震云的作品:“把都市和故鄉重疊在一起,把過去、現在與未來也混淆在一起。所有在都市發生的故事都是關于家鄉的故事,都是對故鄉的一種隱喻。”①劉震云對故鄉有強烈的歸屬感,他的創作多以故鄉為背景,以小人物為描寫對象,展現最真實的底層生活,表達了對底層人的關懷和對生命的反思。
一、底層人的生存危機
1958年,劉震云出生于河南省延津縣,在他八個月時被送去姥姥家,在鄉村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劉震云在年幼時險些被餓死,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使他認識到農村生活的貧乏困窘給底層人民帶來巨大的威脅和傷害。劉震云在作品中描寫社會混亂、物質貧乏下人民的生存困境,表達對權力的強烈批判。
劉震云筆下的底層人物,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但他們卻有著共同的生活目標:改變自身生存的困境。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正處于經濟改革時期,在那個物質資源極其匱乏的年代,人的生存受到了極大的威脅,為了生存只能奔波勞累。《單位》、《一地雞毛》等小說都是以這一時代背景來展開敘述的,在這樣貧困的物質環境下,底層人民生活的尷尬、痛苦又沒有尊嚴。《單位》的主人公小林由于職務低、工資低,只能和妻子過著蝸居的生活,因為窮困,他們不道德的偷水、買廉價處理的菜、每天擠四小時的公交車上下班,這樣的生活令他煩躁、痛苦又無奈。社會底層小人物的辛酸與苦悶在小林身上完整而充分地顯現出來,困苦的生活久像是一個無底洞,咒罵、悲痛過后還是要繼續生活。底層的人要何去何從,找不到答案,也沒有答案。
二、底層人的精神困境
(一)難以言說的窘境。“文學作品善于將神秘的社會意圖掩藏或滲透在審美詩意世界中,并賦予這種審美詩意世界以多重解讀的可能性。”②新世紀以來,劉震云一直關注著人的精神困境,在歷史和現實的交錯中,劉震云感受著生活的支離破碎、人性的墮落自私,他運用荒誕戲謔的手法制造了一出出的鬧劇,在擰巴、無厘頭的表面下,是對人精神的拷問,并且深入地揭示了人內心世界難以言說的孤獨和絕望。
(二)人性的異化。“‘異化是一個哲學和社會學范疇的概念。異化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③劉震云的創作多數都是以生活困頓為故事背景的,故事主人公多是主體意識消散,精神異化的人。生命主體對物質的畸形崇拜和追求,使人的精神發生了質的改變。在《故鄉天下黃花中》這部作品中,人性的異化更是達到了令人恐懼的地步。日軍在村子里進行了大屠殺后,村子里血流遍地。但是,現在見這村埋人,又有許多人拉了一些白楊木薄板棺材出來售。一時村里成了棺材市場,到處有人討價還價。扭曲的畸形物欲使人變得麻木不仁,主體意識已經瓦解,個人價值意識已不復存在。劉震云在表達“人的精神困境”時,將“困境”具體為一個個的“怪圈”,將人物命運與之密切的聯系在一起,人們忙于奔波勞累,看似在不斷前行,實際上卻是在原地打轉。
三、劉震云之底層表達
(一)多重視角的表現方法。劉震云是以農民身份出身的作家,他的創作扎根于底層生活,心系底層的困苦民眾。作者在作品中常采用不同的敘述視角,如零聚焦敘事視角、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視角、第三人稱內聚焦敘事視角等多種敘述手法。在作者早期的作品《塔鋪》、《新兵連》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稱內聚焦的敘述手法,用“我”的視角來審視周邊的人,凸顯小人物在“我”的視角下卑微的生存狀態。作品《一地雞毛》采用了第三人稱敘述和零聚焦敘述相結合的表述手法,展現主人公小林的心路歷程。
(二)“擰巴”式的敘事手法。“擰巴”是劉震云小說的主要描寫方法,更是劉震云民間詼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擰巴指人不僅和自己過不去,還和別人過不去。所有的人和事都別扭著,而更令人別扭的是,所有人都對這個“別扭”無可奈何,還得按照這個“別扭”繼續下去。《一句頂一萬句》中,劉震云用“擰巴”式的語言描寫兩代人費盡曲折尋找“說得上話的人”,一代一代的人在出走,在尋找,可是這種孤獨就像是個圓,讓人看不到盡頭也找不到終點。這不是一個人的孤獨,而是一群人,一城人,一代人的孤獨。劉震云用他繞來繞去的“擰巴”語言道出了他對人的生存的思考。
劉震云始終堅持在底層書寫的道路上行走,他時刻關注著底層人的生存困境,展現時代背景下物資貧乏和權力濫用給人的生命所帶來的扭曲和異化,他的書寫帶有明顯的批判意識。劉震云深入挖掘底層人的精神異化和有話難言的孤獨,通過對社會弊端進行的深刻批判,體現出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人文關懷,為當代作家進行底層創作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指引。
注釋:
①陳曉明.現代性的幻想——當代理論與文學的隱蔽轉向 [ M ].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00.
②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 [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8.
③張翼.文藝傳播亟須強化人文理性精神[ J ].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1(2):54-56.
參考文獻:
[1]姚中旺.劉震云新寫實小說的出路[J].時代文學,2007,9(2):23-39.
[2]白浩.新世紀底層文學的書寫與討論[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7(6):25-29.
[3]王光東.20世紀民間文學與中國文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16.
[4]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59.
[5]鄭鵬.中國當代文學的主體性[M].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65.
[6]羅素.權力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2011:67.
作者簡介:侯靜宇(1995-),女,漢族,河南林州人,碩士,單位:黑龍江大學,研究方向: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