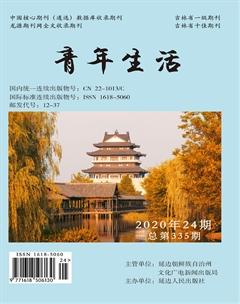被想象的晚清
孟培圓
在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一書中,王德威先生以一篇《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為綱,對晚清小說重新清理和挖掘,欲重新對晚清文化的進行定位。相較于傳統觀點中所認為的,以“五四”為現代文學的高潮,對晚清的定位只是傳統的尾聲亦或是現代的先兆;他認為晚清文學才是現代文學的高潮,而“五四”則壓抑了晚清的“現代性”,晚清的眾聲喧嘩被“五四”感時憂國所摒除,彼時作者求新、求變的努力,被自命現代、實則傳統的讀者所忽略,“五四”成為了現代文學的收束,甚至是某種程度的背叛。
王德威從眾聲喧嘩的角度出發,對當時晚清的各類小說逐一進行介紹,結合廣泛的文本和細密的論述,從一些文學價值或高或低的作品中,描繪了當時的晚清文學活動之盛,晚清對于欲望、正義、價值、知識的推陳出新。在這一方面,王德威可以說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但在我們合上這本論著之后,重新回到這篇導論《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我們仍要思考幾個問題:
晚清時期的眾聲喧嘩,是否能夠真正帶給我們“現代性”?這些喧嘩背后是否隱藏著南轅北轍的危機?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王德威對于“晚清”的現代性期待是一種空中花園式的理想?
而所謂的“現代性”,真的是如同王德威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自覺的求新求變意識,一種貴今薄古的創造策略”?而這種“求新求變、打破傳承”到底是一種手段,還是一種目的?如果不是他所闡釋的那種,那真正的“現代性”又是什么?
因此,本文將從這幾個問題出發,去探討這本書所真正想要傳達的真正目的,以及在王德威的所站的立場之上,他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盡量全方位的把握對于“晚清”和“五四”,“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真正關系。
空中花園中的喧嘩
上文已經寫到王德威在書中對四類小說進行了闡述,并且列舉了具體的作品,從作品中找尋“現代性”的蛛絲馬跡。在王德威所列出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對男歡女愛和才子佳人的顛覆、對所謂的法律正義和詩學正義的闡釋,還是對價值的重新判定、或者是對知識的某種追尋,其實都可以其實都可以在晚清之前的文本中得以找尋。如《桃花扇》中李香君的悲劇命運,《水滸傳》替天行道的大旗,還是《笑林廣記》中的諸多笑話等,都可以看做是有“現代性”的痕跡。
如果我們這樣討論下去,就會陷入到了是在晚清的文本中尋找“非現代”,還是在晚清之前的歷史文本中尋找“現代”的無聊游戲。且如此說法,未免有詭辯之嫌。那到底如何算“現代”,又如何算“非現代”?
筆者在這里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李約瑟曾有一個論斷,風箱和水排雖然是中國發明的,但卻無法產生蒸汽機,就如同在晚清小說之中,雖然有現代性的痕跡,但其仍舊不是現代的。蒸汽機的發明需要以熱力學和真空理論為基礎,而這些理論并不可能在當時的中國產生,所以蒸汽機也是無法被中國發明的。晚清小說中的各種應用型的實驗文本,它們只是一些相對零碎的事物,就如同風箱和水排之于蒸汽機的作用。如果我們陷入從“晚清”文本中尋找“風箱”和“水排”,而對“真空理論和熱力學”不去探討,這本身便是偏頗的。而現代性的文學,需要作為基底的現代社會思想,但這并不是當時的中國所能夠產生的。所以哪怕“晚清”文學真的能夠繼續發展下去,最后的結果可能也并不是王德威所想要的。
但其實它也并不想要任何一個結果,他所看重的是那種“求新求變”的過程,他認為這樣一個過程其實就是“現代性”的,且是衡量“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標準。這其實也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他所認為的“現代性”是什么?
被改寫的“現代性”
當王德威把“晚清”稱為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時,他也許能夠想到啟蒙運動時,啟蒙主義者手持現代性的旗幟,對前現代社會進行了激烈的抨擊,那種集權至上,集體大于個人的傳統社會,成為了被反對的對象。他們所代表的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成為了現代性的注腳。但現代性是合乎目的的,他們有相對明確的追求,有一整套完整的價值理念。“求新求變,打破傳承”只是作為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存在。而王德威所提倡的“現代性”,卻把它更多作為了一種終極標準,他所反抗的,并不是“晚清”之前的文學形態,而是“五四”,在王德威眼中的“五四”是一個不再耀眼的文學形態,它開始偏離軌道,朝著一元化的遠方奔去。這時候的“五四”仍舊具有“現代性”的光輝,只是這種光輝已經沒有“晚清”時候噴薄而出的景象了。“晚清”那種多元化的時代已經開始衰落,這種余暉的景象也正是王德威所慨嘆的。
我們通常所理解西方的“現代性”是一種具有理性、科學、民主、平等的價值理念,它對于傳統的那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進行抨擊和反抗,之后想要建立一個更合理和崇高制度的社會理想。王德威所提倡的“現代性”,其實更像是一種后現代的理論。
現代和后現代雖然都具有反抗性,但現代所反抗的是傳統的不合理,它只是重構,卻并不消解,當它重新構建了一個合乎現代性的制度之后,現代的目的也便完成了。但是在后現代看來,當現代所構建的這種制度形成之后,作為“勇士”的現代便替代了封建和宗教,重新成為了長滿堅硬鱗片的“惡龍”,也重新壓抑了多元化的思想,成為了專制的另一種代言人。
這些想法我們可以在王德威這本著作中發現許多,如他對“被壓抑的現代性”所指陳的三個不同方向:它代表一個文學傳統內生生不息的創造力(不斷的反抗性)、“被壓抑的現代性”指的是“五四”以來的文學及文學史寫作的自我檢查及壓抑現象(現代對于多元的壓抑)、“被壓抑的現代性”亦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來,種種不入流的文藝實驗(現代對于不符合現代性標準的壓抑),由此也可以發現他所受到后現代理論的影響之深。
當我們理解了王德威對晚清所持有的是一種后現代的觀念,那么“后現代晚清”是否能夠對晚清前的文學形態進行顛覆,而具有現代性的“五四”又是否能夠壓抑“后現代晚清”?
讓我們回到這本書的名字《被壓抑的現代性》以及導論的題目《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王德威的尷尬之處:晚清所具有的氣質也許有著一定的后現代性,但是這種后現代性并不能在晚清那個時代就可以被建構出來,后現代是在現代的基礎所發展而來的,如何從傳統直接跨越現代,直達后現代。因此,如果王德威把晚清定義為后現代的,那這本書似乎就存在了立論的問題。于是他盡力去粘合后現代與現代之間的縫隙,如將“現代”的意義定義為求新求變,打破傳承,如將晚清的新變置于國際的視域中去,以區別于之前晚明,唐代等等的一系列革新。這些行為其實都是對于現代性的改寫,只有這樣才能夠將晚清和五四連接起來,從而構建某種在傳承中或收束,或壓抑的錯覺。
想象中的晚清
王德威在自己的這本書中對于晚清做出了一個極為“樂觀”的想象,這種想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種具有因果邏輯的“無常”可能性。但遺憾的是,這種因果邏輯也并不是那么高明。他的確發現了“五四”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的局限性,但他所作出這樣的觀點只是為了把他“現代性”的理念前置到晚清時期的文學,這恰恰反映了他對晚清理解的局限。
王德威的書中有這樣的主張,他認為文學的“現代性”有可能因應政治、技術的“現代化”而起,但并無形成一種前后因果的必然性。他用這樣一句話加上一個十分武斷的注釋避重就輕的繞開了這個問題,但這也印證了他不僅對于晚清文學理解的有不小的局限性,也對80年代之后中國文學的理解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他用8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去印證晚清文學的某種“現代”合法性,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局限。
這種局限所存在的問題便是晚清文學是否脫離政治、技術、文化環境獨立發展,這種脫離并不是指文化在這些因素化學反應中會提前或延后的產生,而是真正的與其斷裂。但顯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晚清并沒有能夠脫離當時的文化桎梏,最終還是走向了消亡。這些留下的文本用我們現代的眼光看的確是有著某些反抗性的色彩,但這種反抗性也許本身就不是從現代或者后現代出發的,它只是一種屬于中國的,一直流傳至今的文化。
當然,王德威的真正目的并不僅止于將晚清文學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所闡釋的文學世界觀,所想要證明的是哪怕是“五四”這樣的現代文學,也并沒有真正把中國帶入現代,而是重新落入了利維坦的陷阱之中。他期望用文學這樣一個因素,去闡釋這個多元化的世界。但說實話并不成功,他不僅沒有成功的將兩者進行融洽的接合,反而沉浸于那五花八門的各色文本之中,這也許是某種文人的“刻意進取”所造成的偏離。
參考文獻:
[1]白鵬. 對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的質疑 -- 評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 -- 晚清小說新論》[J]. 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3).
[2]張濤. 是 “起源”, 還是 “過渡”?—— 王德威的 “被壓抑的現代性” 芻議 [J]. 文藝爭鳴,2015 (6):91-94.
[3]汪衛東. “晚清現代性” 的悖論與盲區 —— 以《被壓抑的現代性 —— 沒有晚清,何來 “五四”?》為中心 [J]. 中國文學批評,2017 (04):100-109.
[4]江臘生. 什么 “現代性”, 如何 “壓抑”—— 評王德威的 “被壓抑的現代性”[J]. 中國文學批評,2017 (04):109-115.
[5]黃海浪. 再談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J]. 學理論,2013 (8):178-179.
[6]劉成勇.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與中國現代文學起點問題 [J]. 吉首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8, 29 (6):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