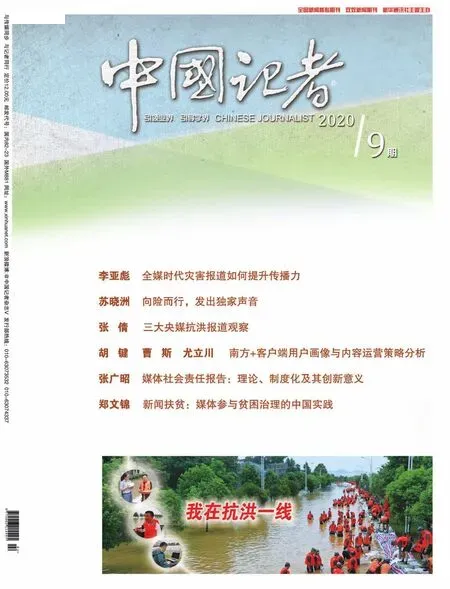向險而行發出獨家聲音
今年7月上旬至8月中旬,長江發生流域性特大洪水。在水利界公認“江湖水系最復雜、防汛抗洪最困難”的湖南,持續暴雨傾盆,河湖水位猛漲,堤壩管涌、滲漏、翻沙鼓水等險情頻發……環洞庭湖區和湘江、資江、沅江、澧水流域的萬里“洪線”上,打響了持續時間近兩個月的抗洪搶險大會戰。
在此期間,我和同事組成的“融合報道突擊隊”,“向險而行”先后轉戰環洞庭湖區沅江市、南縣、大通湖區、安鄉縣、漢壽縣、津市市、華容縣、岳陽縣,還深入武陵山區的石門縣、保靖縣、永順縣等地,采寫了大量來自一線的抗洪新聞報道,取得了媒體最高采用500多家、絕大多數報道在新華社客戶端獲得了瀏覽量“百萬+”的報道成效。通過不斷轉換報道視角和戰場,延長前線報道周期,我對在防汛抗洪“浩如煙海”的報道中,如何以時效報道、獨家報道和創意報道發出“特別之聲”,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體會。
“聞警而動”要精選出擊時點
地處長江中游的湖南,擁有吞吐長江的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和湘江、資江、沅江、澧水四條大河。龐大、復雜的水系,使得“水情成為湖南省最大的省情”。黨中央明確指示湖南防汛壓力大、責任重,要把責任扛起來,把防汛各項工作做好。
貫徹上級指示,我們近年來聚焦洞庭湖防汛抗旱問題,在前輩長期抗洪報道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未雨綢繆”對湖南防汛形勢開展了持續密切跟蹤和研究。這些前期積累運用于今年的報道實踐,發揮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從今年6月底開始,湖南各地特別是澧水流域普降暴雨,河湖水位一路上漲。從準備水位、警戒水位,漲到超警戒水位、保證水位……防汛抗旱指揮機構的應急響應,也從四級、三級,一路上調至二級……
何時全面啟動一線抗洪報道?
我們通過前期調研了解到:經過長期水利事業建設,湖南省由排澇泵站、撇洪渠、調蓄內湖和排澇涵閘等構成的排澇體系,裝機容量達90.9萬千瓦,排澇流量9599立方米每秒,這相當于一條大型河流汛期流量,對持續強降雨形成的內澇,具有一定抗擊能力;而主要堤防如洞庭湖區堤防,設防標準總體是按1954年城陵磯最高水位34.4米控制。湖南境內長江干堤、環洞庭湖及“四水”很多主要堤防,絕大多數達到了三級堤防以上水準;較高的設防標準,使湖南的防洪體系面對普通洪水,稱得上“固若金湯”。
在此背景下,我們此次防汛前沿報道,將出擊時間預設為“超警戒水位密切關注,超保證水位重點出擊”。
7月上旬,受長江“頂托”、來水“彪悍”、暴雨“瓢潑”等影響,南洞庭湖與西洞庭湖結合部沅江市南嘴鎮、南縣武圣宮鎮等地出現超警戒乃至超保證水位。獲悉水情,我們多支蓄勢已久的“融合報道突擊隊”,連夜出發,頂著撲面而來的狂風暴雨,在次日凌晨抵達了洞庭湖區水位最高的部分防汛抗洪一線。
在沅江市南嘴鎮目平湖大堤等地,在密不透風的雨點中借助探照燈光,我和同事陳澤國看到堤內村莊二層樓房屋頂,與堤外風急浪涌的洞庭湖面高度幾乎持平,“懸湖”之勢令人觸目驚心。在大堤邊的防汛棚里,我們采訪了當地防汛經驗豐富的專家,了解到今年防汛“要打大仗、硬仗”的嚴峻汛情;在物資儲備點、一線防洪大堤、涵閘泵站,我們見證了湖區黨群齊上陣“斗”洪魔的生動場景,將這些情況匯聚起來,結合其他方面素材,我們推出了《八百里洞庭戰“懸湖”》,報道被200多家媒體采用。
根據歷年來的經驗,一旦遭遇大汛,洞庭湖區可能出現生物災害。如湖洲被淹會導致原本棲息在湖洲中的東方田鼠等“鼠輩”穿越湖灘、越過大堤,成群結隊地內遷侵入田園。在發現沅江市、南縣等地“一線臨湖”鄉鎮出現相關問題后,我們適時推出了報道《洞庭湖畔剿鼠患》,成為本輪汛情關于生物災害的首發報道。
今年汛情期間,恰逢湖南大力發展的早稻進入收獲季節,而優質大米主要來源——晚稻正進入插秧季節,有“魚米之鄉”美譽的洞庭湖區,面臨搶收早稻、搶種晚稻、搶險護堤的“三搶”壓力。我和同事們深入湖區,在堤外洪水洶涌、堤內稻浪翻滾的環境中,采訪與汛情、暴雨抗爭的糧食保衛戰。從萬眾一心搶險情拯救受淹稻田、見縫插針抓糧食生產兩個層面,推出了《洞庭湖畔打響糧食保衛戰》《中國南方汛情對糧食供給影響可控》等報道。
面對主要河流高洪水位導致洞庭湖區一些內湖排水受阻出現險情,我們及時趕到險情最為嚴峻的我國最大溪水湖之一——毛里湖畔,見證當地干部群眾全力以赴巡堤除險,“做最壞準備、盡最大努力,誓死捍衛毛里湖”的狀況,推出報道《西洞庭打響毛里湖抗洪“生死戰”》。

□ 7月16日中午,蘇曉洲(左一)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采訪一起管涌險情處置情況。(譚暢/攝)
隨著國家防總將防汛Ⅲ級應急響應提升至Ⅱ級,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對進一步做好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華社湖南分社領導帶領我們從聞“汛”而動筑防線、鏖戰洪魔勇擔當、洪水無情人有情三個層面,采寫了《戰汛情勇擔當——黨員干部奮戰抗洪一線故事》,在抗洪搶險關鍵時刻推出,被500多家媒體采用,起到了鼓舞人心、昂揚斗志的強大作用。
提前預判報道時點,搶抓事件苗頭推出報道,使得我們本輪汛情中很多重要時效報道,實現了首發,較好履行了國家通訊社“消息總匯”的職責。
“向險而行”要優選發力重點
根據近年我們針對洞庭湖區防汛抗旱所做的“功課”,我們了解到湖南防汛戰線很長,光是洞庭湖地區自身防洪工程就主要包含堤防和蓄洪垸兩部分,共有堤防10591公里,其中一線防洪大堤總長3471公里。
今年汛期,洞庭湖區幾乎全線“告警”。如此漫長的“洪線”,不可能均衡用力,必須抓關鍵點和出險點。
在水利界,有“長江之險在荊江,荊江之難在洞庭,洞庭之憂在安鄉”的說法。位于西洞庭湖畔的安鄉縣,一線大堤有420公里長,由于其地理位置北連長江、西接澧水、南通洞庭湖,在湖南防汛抗洪這盤“大棋”中至關重要。
我們在汛情最緊急的時候,迅速趕到了安鄉縣。傍晚時分進縣城,就馬不停蹄直奔當地防汛抗旱指揮部,在他們的指引下趕到了超保證水位的松虎洪道一線防洪大堤。當時見到的情景,是堤外洞庭湖、澧水、長江洪道洪水水面,高出大堤內村莊、城鎮足足有七八米。洞庭湖浩渺煙波間,錨泊的大輪船都成了渺小的黑點。滔滔洪水與低垂的雨云幾乎連為一體,空氣中四處彌漫著水腥味。
現場看搶險隊伍開挖導浸溝,處置“翻沙鼓水”“沙眼”等險情,走訪轉移群眾安置點,聽干部群眾講述處置管涌等重大險情的經歷,我們堅守抗洪報道“戰位”。從汛情最危險時刻,一直堅持采訪到高洪水位開始一厘米、一厘米地退卻。在人們奔走相告“水又退了一厘米!”的喜悅歡呼聲中,我們推出《目擊洞庭抗洪“風向標”挺過第一波攻擊》,產生良好報道效果。
汛情發生后,湖南群山蒼莽、溪谷縱橫的湘西地區,山洪、地質災害頻發。聽聞7月上旬發生在石門縣南北鎮潘坪村雷家山的山體滑坡,規模巨大。我和同事譚暢等人立即從洞庭湖平原啟程,驅車六七個小時,抵達位于“湖南屋脊”——壺瓶山區的事發現場。當地人士說,由于山高路遠、沿途泥石流和山洪頻發,很少有媒體記者進入現場。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末日山崩”的景象:一座巨大的山體近一半坍塌,300多萬立方米滑坡體挾著泥石流沖下山溝,沿途摧毀了山林、茶園、房屋、公路、電站。我們抵達現場時,坍塌的山體依然不斷有土石滾落。
采訪就在滑坡現場和不遠處險情處置指揮部展開。北斗衛星高精度地質災害監測預警系統多次成功預警、當地組織事發地居民緊急提前避險搬遷、山崩前提前一小時關閉湖南、湖北之間一條繁忙的省際交通線等關鍵細節,被我們全面掌握;從當地干部群眾口中,我們還聽到他們在一些房屋的裂縫處貼上紙條,觀測變化。隔段時間看,有紙條崩斷,就顯示“房屋位移了”;觀察山間泉水,發現水突然變渾濁,顯示山體進一步松動了;進而發現平時難得一見足有“兩粒米長”的大螞蟻,從山間巖縫里競相爬出來四散奔逃,顯示“麻煩要來了”等鮮為人知的細節。
運用這些鮮活生動的“第一手素材”,我們抓緊時間推出報道《一場“山崩”是如何被預知的?》。報道內容完全跳出了當地“情況通報”,播發后引發了網友熱議。人們驚嘆“北斗神器”驚人的準確,也點贊基層工作人員高度負責的工作態度。呼吁全國各地學習“石門經驗”,運用“高科技”結合“土辦法”,盡量避免山洪和地質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本輪抗洪搶險報道,我們把洞庭湖水系中地理位置處于防洪要沖的地方,作為“主攻選點”;把低標準堤防和等外堤防,當成“重點對象”;把“迎流當沖堤段”“堤基、堤身滲漏堤段”“穿堤建筑物嚴重破損”“地質災害高發地”等“險工險段”,看作“主要戰場”。既通過氣象和水文信息資料,提前選準“突擊隊”的戰場;又不以山河為遠追逐突發險情現場,力求“見人所未見、聞人所未聞”,成就了不少獨家新聞。
“脫穎而出”要巧選關注視點
抗洪搶險,是個專業性比較強的“技術活”。抗洪報道作為“技術新聞”要獲得輿論關注乃至成為熱點,創意非常重要。
創意,需要有準備的大腦。
我和同事們在洞庭湖區抗洪一線采訪,發現到處都能遇上名字里帶“水”的“抗洪人”,比如“洪”“濤”“波”等。
這種現象,很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一番走訪發現,他們這么取名,浸潤著“湖畔人家”關于洪水的記憶,也表現出他們的父母守衛河湖安瀾的壯志豪情或殷切希望。
選定目標,我們開始不但尋找名字里帶“水”的“抗洪人”,更尋找這些身上有故事的人。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津市市一個搶筑子堤的搶險現場,43歲的白衣鎮黨委書記劉波介紹,他生于洞庭湖畔。“童年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家鄉發大水,父親用一根扁擔挑起兩個籮筐,一個籮筐里坐著我,另一個籮筐里坐著我弟弟。”劉波說,“爸爸挑著我們兩兄弟,走了二十幾公里上山躲水。他給我取名劉波,給弟弟取名劉泳。希望遇洪平安、逢災無恙。”
除了挖掘到劉波和劉泳的故事,我們還采訪到堅守大堤幾十個晝夜、把抗洪一線當做“干部教育最好課堂”的沅江市南嘴鎮鎮長劉洪;“困了就打自己幾耳光”堅守崗位的防汛中隊長王洪波;見證水文測量從人工到智能化的“水利世家”劉洪流……從他們口中,我們了解到洞庭防汛抗洪的滄桑之變。在此基礎上,我們采寫的《不負其名守安瀾——洞庭“守堤人”名字里的洪水印跡》,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媒體同行一致好評。有心人發現,此稿作者蘇曉洲、袁汝婷、蔡瀟瀟,名字里竟帶了四個“水”,一時之間,“三湘四水”寫名字里帶“水”的“抗洪人”,傳為美談。
創意,需要有樂觀的心態。
抗洪報道,需要克服蚊蟲叮咬、濕氣熱浪、風吹雨打的煎熬,面臨血吸蟲病、皮膚病等健康風險威脅,著實是個“苦差事”。但我們從一線抗洪大軍身上,經常能感受到凡事向好處看、堅信“洪水終將退去、大地一定能保住”的豪邁樂觀精神。把這種精神運用于報道實踐,往往能催生出人意料的創意。
在抗洪一線,我們發現在防汛日益機械化、信息化甚至智能化的今天,一些“水利前輩”傳下來的“秘器”依然非常實用,有的甚至是一線抗洪隊員們的“標配”。
如竹梆子,汛情險情出現,梆子聲是警報器;一切安然無恙,梆子聲是安眠曲。如尼龍手絹地圖,防水、抗皺、便攜、耐用。如沒有扶手、沒有靠背的木凳,讓守堤人能短暫休息但又不至于倒頭睡去誤事;如驅趕蚊蟲的蚊香,如夜晚用來照明的馬燈……我們將這些所見所聞集納起來,將其分別命名為“傳音梆”“蟬翼圖”“醒腦凳”“斷魂香”“暖心燈”,以《“抗洪俠”的“獨門秘器”》推出報道,獨特的視角,清新的文風,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特別是其中關于“斷魂香”(蚊香)的描述被很多讀者在評論中引用:這種長得“土里土氣”的燃燒蚊香,一尺來長十分粗壯,點燃后煙味重、燒得久。它散發出來的氣味,對蚊蟲來說簡直就是“含笑半步癲”,一熏就蔫。
創意,需要有問題意識。
本輪防汛報道,我們了解到一些地方出現超歷史記錄的洪水,導致今年成為汛期文物受損十分嚴重的一年。我們搶抓湖南省張家界市永定區馬頭溪風雨橋被洪水沖毀這一新聞事件,結合全國70多座“文物橋”被洪水沖毀背景,推出深度報道《古橋如何抗洪》;報道從問題和現象入手,通過采訪權威專家,剖析古橋這類“古建活化石”存在的汛前排查和搶救性維修保護不力、過度人類活動擠占古橋生存空間等保護軟肋,提出了為保護立法、就修繕調規、幫管理定向等對策建議。
在此次抗洪搶險報道中,我們還推出《“小沙眼”頻釀大險情,去洞庭“心腹之患”須治“軟腳堤壩”》,指出洞庭湖防洪體系中,沙質“軟腳堤壩”普遍存在堤身、堤基滲漏嚴重等問題,是防汛抗洪的突出“軟肋”。通過采訪多地水利專家,提出了啟動吹填壓浸、高噴灌漿等治理工程,升級換代這類堤壩,努力消除洞庭防洪“心腹之患”的系列建議。
一位“老水利”就抗洪“黑科技”報道接受我們采訪時說:“防汛抗洪中很多東西都變了,可土地沒變,河流沒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永遠不會變。”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們也要秉持“老水利”這種精神,在堅守、傳承中不斷追求發展和超越,把防汛抗洪報道推向新的境界,更好推動社會事業發展和進步,更好服務于黨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