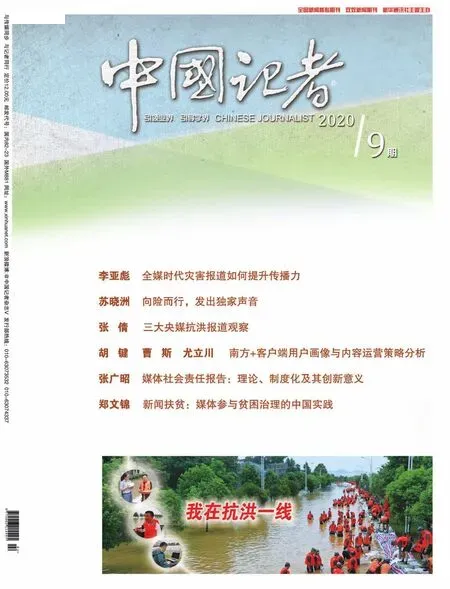細處著眼,隨時隨地有“新”聞
8月20日六點,拖著因疲憊而沉重的腳步,我終于回到家。站在陽臺上,借著天邊一縷晨曦,可以看到嘉陵江水浩浩蕩蕩,磁器口正對岸的順水寺岸標燈塔在岸邊閃著警示光。
8月20日凌晨2點開始,“嘉陵江2020年2號洪水”過境沙坪壩區磁器口,洪峰水位194.29米,超過保證水位8.65米;向前回溯兩個月,6月22日,我在綦江見證了1940年綦江流域重慶段有水文記錄以來最大洪水。
作為重慶日報跑區縣的記者,我對口聯系的區縣中,沙坪壩、綦江是全市最易受洪水侵襲的區縣。今年洪澇災害頻發,作為重災區的跑口記者,如何及時將一次次洪峰過境前后的報道寫出新意,曾一度讓我焦慮。
在一次經驗總結中,我發現只有通過增強“四力”,在抗洪一線找典型、挖細節、“抓活魚”,既能印證抗洪面上報道,也能更好地反映災難中黨和政府“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
一、洪災報道引發的“焦慮”
汛期,往往也是我工作“焦慮期”。對重慶來說,汛期洪澇災害幾乎年年有、月月有。重慶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境內山地面積占總面積的3/4;長江橫貫境內同時,嘉陵江、綦江等集雨面積較大的江河也在此匯入長江。這樣的氣候、地形地貌決定了這座城市容易遭受洪澇災害襲擊。今年4月,重慶提前入汛。至8月20日,長江、嘉陵江分別有5個、2個編號洪水過境,綦江最易受災的城區則前后經歷了8次洪峰過境。
與平原地區相比,重慶的地形地貌也決定了洪澇災害發生時間短,危害大,新聞采寫的機會也稍縱即逝。如綦江“6·22”特大洪災,從正式發布預警到洪峰抵達綦江城區,前后只有4個多小時。記者必須盡快趕到現場、及時找準抗洪典型采訪,否則新聞采寫“窗口期”稍縱即逝。
與此同時,突發性自然災害報道,往往是讀者關注的焦點、地方新聞中的重點,有大量媒體扎堆報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競爭。作為省級黨報,必須在遵循新聞規律的基礎上,既要反映群眾的日常抗洪生活,也要反映黨員干部在洪水中所做工作,讓報道“有血有肉”、既見“故事”又見精神,難度很大。
如何抓住這類“程序性”的報道特點,體現時效上的“新”,同時又凸顯每次抗洪救災的“新”?這一度讓我絞盡腦汁。
二、追趕洪水“搶”新聞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每次突發性事件發生時,我要求自己盡量能趕到現場作為“目擊者”。
受預測預報水平影響,很多次洪災發生時,我都必須與洪水“賽跑”。其中,最緊迫的洪澇災害報道,是綦江“6·22”特大洪災。這也是市水文監測總站發布的綦江流域重慶段首個紅色預警。
6月22日12時許,報社跑市水文監測總站的記者龍丹梅告訴我,她正在采寫綦江重慶段紅色預警信息,洪水將于下午三點半左右抵達綦江城區。
此時我所在的重慶大學城正下著瓢潑大雨,低洼地帶積水而造成多處道路擁堵。平時,我都是坐更為迅捷的高鐵去綦江。但這次我擔心高鐵晚點錯失報道時機——在今年6月22日前,綦江出現過4次洪峰,但由于水位不高、回落迅速,我趕到現場時往往只能看到清淤的場景。

□ 2020年7月2日,在重慶市黔江區金溪鎮金溪社區,應急救援人員在清掃淤泥。洪災過后,當地政府部門組織開展生產自救和災后恢復工作。(新華社/發 王安彬/攝)
為避過擁堵路段,我開車繞道繞城高速往綦江進發。進入蘭海高速巴南山區后,不時下起陣雨:有的路段路面干爽,有的路段則需將雨刮開到最大,才能勉強看清路面。
下午兩點五十分,我趕到綦江城區時,綦江大橋已禁止通行,部分沿江路段也禁行,狹窄的道路上擠滿了調頭的車輛和準備到岸邊圍觀洪水過境的人群。在這種情形下,我判斷自己無法開到宣傳部與媒體約定的地點,便將車停到距約定地點兩公里外的車庫,盡可能沿江步行,一邊走一邊觀察沿岸的干部群眾搶險救災情況。
雖然沒能及時趕到指定地點采訪到區相關部門領導,但我在沿線通過觀察,挖掘到了古南街道文昌宮社區干部張亞和王定國、沱灣社區書記成紹軍等“為大家舍小家”的典型,寫成《綦江打響限時撤離戰——提前預警,通知到戶,確保零傷亡》的稿件。稿件發表后,部分中央媒體還跟進采訪了在雨中忙著警示居民撤離、自己家卻遭洪水淹的王定國。
三、用“好腳力”減少報道“盲區”
記者不僅是腦力勞動者,更是體力勞動者。記得剛剛參加工作時,我跟著一位年近五十的報社前輩去酉陽武陵山區貧困村采訪修路。由于“腳力”不佳,3.5公里的上山路,我走了不到兩公里就體力不支,最后尷尬地被鄉干部“架”下山。此后,我將練好體力作為搞好采訪的基礎,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能爬坡上坎就盡量不坐車、坐電梯。
在這次報道嘉陵江兩個編號洪水過境期間,我每天都要去磁器口古鎮“刷街”:沿街步行,觀察基層干部、居民、商戶的變化,與他們“擺龍門陣”了解最近兩天迎戰洪峰所做的事,做到“有新聞寫新聞,沒新聞混個‘臉熟’”。我每次去磁器口都會戴同一頂帽子,既可以遮陽,又可以提高自己的“辨識度”。
8月14日嘉陵江2020年1號洪水過境這天,我早中晚到磁器口采訪了三次,寫出了《沙坪壩磁器口防汛32小時》。當8月20日嘉陵江2020年第2號洪水過境前,已有不少基層干部、居民認出我、和我打招呼,有的居民、店主在寒暄中成為我的“信息員”。

□ 2020年7月2日,在重慶市黔江區鵝池鎮南溪村,應急救援力量在疏通被山體垮塌阻塞的行洪渠(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黃偉/攝)
8月18日下午,我從外面采訪趕到磁器口路上時,便接到熱心居民李顯利的電話,說水漲得很快,社區書記蔣世佳挽著褲腳趟水去了磁南街2號解救被困居民。
一邊向街道宣傳委員核實,我一邊趕緊趕到磁南街2號,正好見證了為救需要吸氧的肺部重癥患者王平,街道和社區干部合力調發電機、最后將病人成功轉移出來送上救護車的全過程。后來,根據所見所聞及時寫成鮮活的新聞特寫《沙區金蓉社區 被困老人急需吸氧 洪水中緊急救援》,被多家媒體轉載。
新聞前輩常說:“好新聞是用腳底板‘走’出來的。”在對嘉陵江兩次編號洪水過境的報道中,我也深有感觸。在洪峰到來前發生的諸多事件中,具有較高新聞價值的事件被淹沒在現場諸多事件中成為“小概率事件”,只有極好的運氣可以一次性“撞上”。但如果能通過不斷地選址觀察,并在此基礎上與采訪對象建立起良好的聯系,則可以讓自己不斷地減少“盲區”,及時發現一些突發性的好線索。
四、練出“好眼力”抓現場新聞
在突發事件面前,往往會出現一段時間的“無序”:交通堵塞,無法及時到目的地;所有的人都在忙碌,沒有時間接受采訪;頭緒繁多,不知道從何處開始采訪……這時候,最需要的是根據新聞規律練就“好眼力”。
8月13日中午,我接到跑口記者龍丹梅的信息:嘉陵江上游已形成2020年第1號洪水,14日下午洪峰抵達沙坪壩區磁器口。
當我找到磁器口街道應急辦主任趙家平時,他雖然接待了我,但手上電話幾乎一直不斷,同時表示洪峰下午過境,現在是他最忙碌的時候。
“真是對不起,今天太忙,確實沒辦法陪你。”趙家平婉拒了采訪。
我笑著說:“沒關系,我可以陪著趙主任——只是跟著走走看看,不會耽誤你。”

▲ 本文作者羅蕓(左)在重慶沙坪壩區磁器口受災現場采訪。
就這樣,我成了趙家平的“尾巴”,跟著他一路去勸導還不愿搬遷的商戶,去檢查防汛物資倉庫,去調配洪水來臨時卡點的值守人員……他走過的地方,往往都是防汛的重點,因此只需通過觀察,就可以了解到許多重要情況。有時遇到自己實在想即時了解的信息,我會就地停留,采訪完后再聯系上他,跟上他走下一段路程。
就這樣,依靠在移動中不斷的觀察,我在對趙家平采訪有限的情況下,依然寫出了《再苦再累,黨員也要沖在前面——磁器口迎戰洪峰黨員群像》。
8月19日深夜至20日凌晨,在嘉陵江2020年第2號洪水來臨前夕,磁器口古鎮的居民、商戶幾乎全部撤離,平時建立的“信息網”一下“癱瘓”。這時,觀察成為重要的收集新聞素材的重要手段。通過仔細觀察,我在古鎮平日繁華的磁正街發現了水位加速上漲的跡象,見證了白日里各級干部挨家逐戶勸離的成效,目睹了街道為留守居民“留一盞燈”灑下的溫暖……在寫作時,將洪水的無情與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形成對比,在采訪對象有限的情況下,完成了《夜探磁器口古鎮應急值守》。
五、多用“腦力”探尋“隱藏”的新聞
許多好的新聞往往“藏在”不經意之處,只露出些許“蛛絲馬跡”,需要通過觀察、分析、判斷,才能挖掘出背后有價值的信息。在今年的兩次采訪中,有兩條稿件就是通過我“不經意的一瞥”,多想了想,幸運地挖到了背后有意思的新聞。
6月22日下午3點一刻左右,綦江史上最大洪水將要來襲。我走在綦江城區中山路街上,臨街一家商鋪門口椅子上有個黃澄澄的物體“晃”進我的眼睛。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面銅鑼。水都淹到門口了,這個時候誰還會有心思玩這個?我有些納悶,在匆忙走過這家店鋪后,又折回來好奇地詢問老板。店鋪老板解釋,這是來借用廁所的社區干部的東西。
正在此時,中山路所屬的文昌宮社區綜治專干張亞上完廁所出來。她向我解釋這是上午預警時用的工具。“雖然這個東西很原始,但很管用!”張亞還頗有些得意。我留下她的電話,約定傍晚等她稍微不那么忙后再來采訪她。傍晚,她聯系上我,將文昌宮社區干部冒雨預警、在電喇叭“熄火”后采用傳統方式警示居民的動人故事挖掘了出來。
8月14日,在磁器口古鎮迎來嘉陵江2020年第1號洪水時,我正好在磁器口古鎮內采訪,恰好看到一位阿姨提著滿滿一袋菜走過。根據經驗,洪峰過境時許多人是往外搬東西而不是往家里搬。對于這個“反常”,我跟上去和這位名叫賀蜀君的阿姨閑聊,獲得了很有趣的信息:賀阿姨是嫁到磁器口來的,最初在洪水過境時總是提心吊膽;而她的婆婆則長居于磁器口水邊,對洪水習以為常。在長年與洪水斗爭的過程中,婆婆認為水文部門預測不準,一直以洪水淹到家門口作為搬家標準,這讓她家在1998年洪峰到來時十分被動。隨著近年來科學進步,洪水預測越來越準確。正如賀阿姨說的那樣:“現在洪水過磁器口,就像熟人過路,好久來、好久走、來好大個陣仗,都提前說得一清二楚。”賀阿姨的故事雖然只是磁器口居民生活中一個小的變遷,但反映的是中國大型江河洪水預測水平的提高。在查找了相關的資料后,我將賀阿姨的故事寫成了《科技防洪讓我心里更穩》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