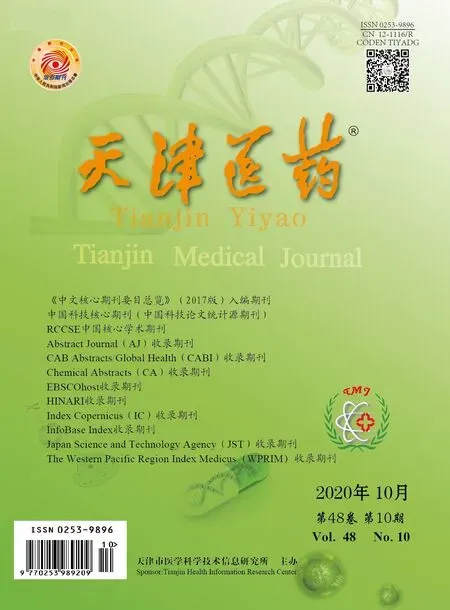幽門螺桿菌感染對糖尿病外周動脈硬化及10年心血管事件風險分層的影響
辜建偉,李蕓,辜小琴,楊云鳳,柳彌,吳碧華,劉菊華,2△
心血管疾病在糖尿病(DM)患者中具有較高的發生率和病死率,DM患者出現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是非DM患者的2~4倍,而早期有效地減少或控制危險因素可使DM患者心腦血管事件的發生率至少降低10%[1-2]。此外,DM患者因長期代謝紊亂導致多系統損害,更易合并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調查顯示,約75%的DM人群可能合并Hp感染,同時DM人群Hp根治成功率也低于非DM人群[3]。Hp感染除與胃癌、胃潰瘍的發生相關外,還與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4-6]。臂踝脈搏波速度(baPWV)對診斷動脈硬化有著較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臨床上常用于動脈硬化的早期篩查[7]。有研究報道Hp感染人群baPWV較正常人群明顯加快[8-9]。目前有關Hp感染對DM人群外周動脈硬化及心血管事件風險影響的研究尚少,同時缺乏大樣本的臨床數據支撐[10]。本研究以無心血管疾病史的DM人群為研究對象,比較合并Hp感染和未合并Hp感染人群外周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風險評分及危險分層差異,通過大樣本臨床數據揭示Hp感染對DM患者外周動脈硬化及心血管疾病風險的影響。
1 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以2015年1月—2019年12月于川北醫學院附屬醫院體檢中心行13C呼氣試驗檢查確認是否Hp感染的DM人群為研究對象。所納入研究對象均符合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糖尿病診斷標準。根據檢查結果分為DMHp+和DMHp-組。排除標準:(1)年齡>80歲。(2)有冠心病、心肌梗死、腦梗死、外周動脈硬化伴支架植入等心腦血管疾病史者。(3)惡性腫瘤、肝腎功能衰竭、嚴重精神或軀體疾病無法配合體檢者。
1.2研究方法
1.2.1一般臨床數據收集 基本臨床資料包括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BMI)、收縮壓(SBP)、舒張壓(DBP),吸煙史、高血壓病史及高脂血癥病史。同時收集體檢當日的總膽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紅蛋白(HbA1c,采用高效液相色譜法檢測)結果。
1.2.2Hp感染測定 患者檢查前1個月內未服用抗生素、鉍制劑、質子泵抑制劑等Hp敏感藥物,檢查須在空腹狀態或者餐后2 h進行。采用廣州華友明康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HY-IREXB型13C呼氣檢測儀檢測呼氣卡收集呼出氣體樣本,經紅外光譜儀檢測得到超基線值(DOB)。檢測時先收集第1次呼氣樣本,然后口服尿素13C沖劑,靜坐30 min后,此時間段禁食禁飲,收集第2次呼吸樣本,前后2次DOB差值>4則為Hp陽性。
1.2.3baPWV測定 檢查前患者平臥位,安靜狀態下休息15 min開始檢測。使用脈搏波傳播檢測裝置測量baPWV。測量時將四肢血壓袖帶縛于左右上臂及下肢踝部,將心音麥克放于第2肋間胸骨上,雙手腕處安裝心電電極并使其同時自動充氣,連續測量2次,每次間隔10 min,取2次測量值的平均值,mean baPWV為雙側baPWV的平均值。外周動脈僵硬度根據baPWV分為4度:baPWV<1 400 mm/s為正常,1 400~1 599 mm/s為輕度增加,1 600~1 799 mm/s為中度增加,≥1 800 mm/s為重度增加[11]。
1.2.4Framingham危險評分(FRS)模型評估 參考文獻[12]納入的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TC、HDL-C、SBP、吸煙,分別對上述因素進行相應的評分賦值,根據對象的總體得分來評價其10年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概率,本文將患者的風險等級分為低危(<10%)、中危(10%~20%)、高危(>20%)3級。
1.2.5國人缺血性心血管疾病(ICVD)發病危險簡易評估模型評估 參考相關文獻[13]納入的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SBP、TC、BMI、吸煙和DM。對10年心血管疾病風險進行評分及風險分層:低危組(<5.0%)、中危組(5.0%~9.9%)、高危組(≥10.0%)。
1.3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和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2組間等級資料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DMHp+和DMHp-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檢查結果比較 見表1。共納入研究對象6 767例,年齡20~79歲,平均年齡(46.07±11.50)歲,男 2 903例(42.9%),女 3 864例(57.1%)。6 767例患者中DMHp-組3 978例,DMHp+組2 789例,DMHp+組年齡、男性比例、SBP、DBP、FBG、HbA1c高于DMHp-組(P<0.05),BMI、HDL-C低于 DMHp-組(P<0.05),2組人群的高血壓比例、高脂血癥比例、吸煙史、TC及LDL-C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blood biochemical indictors between DMHp+group and DMHp-group表1DMHp+和DMHp-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檢查結果比較
2.2 DMHp+組及DMHp-組動脈僵硬度及分布情況 DMHp+組左側、右側及mean baPWV值均較DMHp-組顯著增高(P<0.01),見表2。6 767例患者中,mean baPWV正常1 193例,輕度增加1 646例,中度增加1 309例,重度增加2 619例。DMHp+及DMHp-組的動脈僵硬度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DMHp+組baPWV重度增加比例高于DMHp-組,動脈僵硬度正常、輕度及中度增加比例低于DMHp-組,見表3。
Tab.2 Comparison of peripheral arterial stiffness between DMHp+group and DMHp-group表2DMHp+和DMHp-組人群外周動脈硬化指數的比較 (mm/s,±s)

Tab.2 Comparison of peripheral arterial stiffness between DMHp+group and DMHp-group表2DMHp+和DMHp-組人群外周動脈硬化指數的比較 (mm/s,±s)
組別DMHp-組DMHp+組t或χ2 n 3 978 2 789右側baPWV 1 559±234 2 002±523 47.113**左側baPWV 1 553±238 2 022±565 46.771**Mean baPWV 1 557±228 2 032±525 50.636**

Tab.3 Different stages of arterial stiffness distribution in DMHp+and DMHp-groups表3 不同動脈僵硬度在DMHp+及DMHp-組的分布例(%)
2.3 DMHp-和DMHp+組FRS評分及10年心血管事件風險分層差異 FRS的心血管危險因素中,2組年齡、TC、HDL-C、SBP及吸煙史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DMHp+組FRS總分高于DMHp-組(P<0.01),見表4。所有對象經FRS模型評估10年心血管事件發病風險,低危2 135例,中危2 884例,高危1 748例。DMHp+及DMHp-組心血管事件風險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DMHp+組低危及中危人群所占比例均低于DMHp-組,高危人群所占比例高于DMHp-組,見表5。

Tab.4 Comparison of FRS between DMHp+group and DMHp-group表4DMHp+和DMHp-組FRS評分比較 (分)

Tab.5 The risk distribution of 10-year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FRS model of DMHp+and DMHp-groups表5DMHp-和DMHp+組FRS模型10年心血管事件發生風險分布 例(%)
2.4 DMHp-和DMHp+組ICVD評分及10年心血管事件風險比較 DMHp+和DMHp-組年齡、BMI、SBP及糖尿病等因素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TC及吸煙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DMHp-組ICVD總分低于DMHp+組(P<0.01),見表6。ICVD模型10年心血管事件風險分層結果顯示,低危1 930例,中危1 291例,高危3 546例。DMHp+及DMHp-組心血管事件風險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其中DMHp+組高危人群比例高于DMHp-組,中低危人群比例低于DMHp-組,見表7。

Tab.6 Comparison of ICVD between DMHp+group and DMHp-group表6DMHp+和DMHp-組人群ICVD模型評分比較(分)

Tab.7 Differ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stratification according to ICVD in DMHp+and DMHp-groups表7DMHp+和DMHp-組人群ICVD 10年心血管事件發生風險分布 例(%)
3 討論
外周動脈硬化是DM人群出現心腦血管并發癥的病理基礎,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Hp感染是血管硬化獨立危險因素,其產生的炎癥因子可促進外周動脈粥樣硬化進展[14]。在普通人群中,Hp感染人群的baPWV及心踝血管指數比未感染Hp人群的明顯增加[6,15]。但是,有關Hp感染與DM人群外周動脈硬化的報道相對較少,一項納入160例DM人群橫斷面研究顯示,Hp感染可增加DM人群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16],但目前仍缺乏大樣本的臨床研究支撐Hp感染可影響DM患者外周動脈硬化進展。本研究共納入研究對象6 767例,發現DMHp+組外周動脈硬化的進展速度較DMHp-組明顯加快,其外周動脈硬化的嚴重程度也高于DMHp-組。分析其原因:Hp感染可使機體的氧化/抗氧化系統失衡,加重血管內皮損傷[17-18];Hp感染可促進炎癥介質釋放,研究證實Hp感染者糞便中glmM和16 S rRNA基因表達水平與血清腫瘤壞死因子(TNF)-α、白細胞介素(IL)-1水平呈正相關[19];此外,Hp感染后可導致動脈粥樣硬化,降低大動脈彈性,加速外周血管硬化進展[20]。
本研究還證實Hp感染可增加DM人群的10年心血管疾病的發生風險。FRS是美國Framingham心臟研究中心建立的針對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評估模型,主要對10年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進行預測,識別高危人群,其對預測缺血性心臟病、腦卒中和外周血管疾病的發生有著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12]。然而,我國一項納入11個省3 021例研究對象為期10年的隊列研究顯示,FRS評分可能過高估計了我國人群發生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其原因可能與我國心血管疾病譜、危險因素流行情況及人種與美國人群存在差異相關[21]。為評估中國人群10年心血管疾病風險,我國學者建立了國人ICVD 10年風險評估模型[13]。在本研究中,無論是基于FRS評估模型或國人ICVD10年風險評估模型,DMHp+組的心血管風險評分均顯著高于DMHp-組,在10年心血管疾病危險分層中,DMHp+組高危風險的患者比例顯著高于DMHp-組,提示Hp感染可增加DM人群的10年心血管事件發生風險。
綜上,本研究通過大樣本臨床數據證實Hp感染可加速DM人群外周動脈硬化進展,增加其心血管事件風險。但是,影響DM人群外周動脈硬化進展的因素除了Hp感染外,還有很多,如他汀類調脂藥物等均是外周動脈硬化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本研究為一項回顧性研究,時間跨度較大,無法收集患者體檢時降糖藥、降壓藥以及調脂藥等藥物的使用情況,因此在后續研究中將進行前瞻性對照研究以觀察根治Hp感染對外周動脈硬化進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