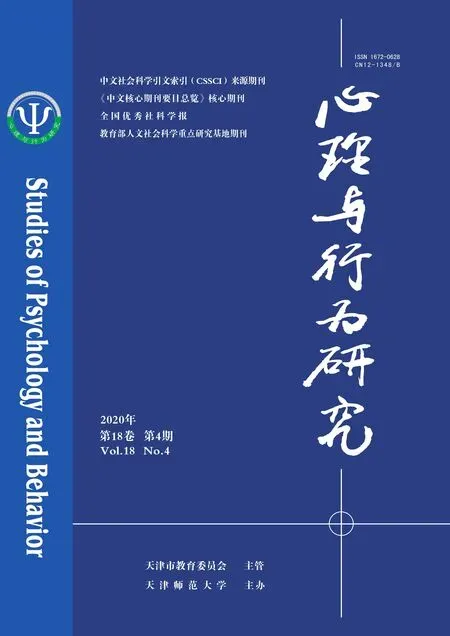小學生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績、生活滿意度的關系:學業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
刁春婷 周文倩 黃 臻
(1 湖北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武漢 430065) (2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3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1 引言
成長型思維模式(growth mindset)是個體對智力或能力的一種基本信念,認為智力或能力是可以隨著人的經歷和學習而不斷發展和變化的。與之相對應的是固定型思維模式,即認為智力或能力可以被證明,但很難改變(Dweck, 2006, 2008;Zhao et al., 2018)。現實生活中,兩種思維模式都會存在。盡管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個人發展有益且可以培養,但在實際生活中很難長久保持。當面對挑戰、接受批評,或與他人相比表現不佳時,個體很容易陷入不安全感或防御心理,出現固定化思維模式。
研究發現,兩種思維模式會對學業和情感體驗產生重大影響,使個體在面對成功、失敗和挑戰等情境時表現出不同的“認知-情感-行為”反應,進而影響到個體的學習行為、學業成就、學習動機、學習投入以及心理健康情況(蔣舒陽, 劉儒德, 甄瑞, 洪偉, 金芳凱, 2018; 田宏杰, 2019; 余芝云, 連榕, 2019)。固定思維模式者認為,智力是先天決定的、有限的和無法改變的,一旦遭遇失敗,就會反過來質疑自己的能力、低估自己的心理彈性和學習能力。成長型思維模式者則認為,能力是可以不斷發展的,優秀的個人素質是可以習得或培養的,所以,他們會表現出持久的學習意愿,將失敗看作自我表現的暫時性反饋,而不是對自我人格、潛能或價值的評判(Dweck, 2006)。可見,培養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小學階段課業負擔不重,是行為習慣教育的關鍵期,小學生各方面都處于發展階段,教育的空間很大。因此,探討小學生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習和生活的關系及其影響機制,對個體的成長以及當前的教育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1.1 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績
在基礎教育階段,學業成績是反映學生學習情況的重要指標。研究發現,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學生的學業成績具有重要影響。一項對46項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具有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學生更有可能在特定科目(語言和數學)和整體成績上取得更高的分數,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績之間的關系不受性別的調節,但受其年級的影響(Costa &Faria, 2018)。對學生進行成長型思維模式訓練,可以提高其學業成績。成長型思維模式能夠促使學生對所犯錯誤進行積極補救,提升課堂參與度,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進而提高其學業成績(Blackwell, Trzesniewski, & Dweck, 2007; Yeager et al., 2019)。
然而,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并不穩定,可能會存在區域和文化上的差異。亞洲和大洋洲的學生報告了成長型思維模式和學業成績之間的正相關,而歐洲顯示了固定型思維模式和學業成績之間的正相關,北美則顯示了固定型思維模式和學業成績之間的負相關(Costa & Faria,2018)。固定型思維模式者渴望得到好成績以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成長型思維模式者并不十分看重成績,認為成績好是對學習的熱愛所帶來的副產物(Dweck, 2006)。所以,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可能存在著復雜的心理機制,且存在文化差異。而在中國,學業成績是學習效果的重要體現和反饋,受到家長和學生的普遍重視。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小學生的學業成績具有正向預測作用。
1.2 學業自我效能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績關系中的中介作用
學業自我效能感是指個體在學業領域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任務目標的信念與判斷。研究表明,學業自我效能感可以直接預測學業成績,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量。對小學生和中學生進行同時研究發現,學業自我效能感是其學業成績最一致、最有力的預測因子,并在課堂練習、父母教育期望等因素與小學生學業成績的關系之間起到中介作用(郭筱琳, 何蘇日那, 秦歡, 劉春暉,羅良, 2019; Cleary & Kitsantas, 2017; Kriegbaum,Jansen, & Spinath, 2015)。
本研究推測,成長型思維模式可能通過個體內部穩定的學業自我效能感起作用。McWilliams(2014)對九年級的學生進行訪談,發現具有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學生都傾向于內部歸因,對自己有較為清楚的認識,且有著很強的學業自我效能感。研究者以因存在閱讀障礙而接受特殊教育的六到八年級的學生為被試,對實驗組進行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干預,發現這一干預可以顯著提高實驗組的學習動機水平,但在自我效能感和學業成績上,實驗組與控制組沒有顯著差異。這些被試的學業自我效能感更多地受制于閱讀障礙本身,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干預雖然使他們具備了更強的學習動機,但短暫的干預并不能帶來學業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因此也不能提高學業成績(Rhew,Piro, Goolkasian, Cosentino, & Palikara, 2018)。前人研究結果的不一致可能是因為沒有充分探討學業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小學生的成長型思維模式能夠正向預測學業自我效能感,學業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預測學業成績,且在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績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1.3 成長型思維模式、學業自我效能感與生活滿意度
生活滿意度是個體基于自身設定標準對其生活質量做出的主觀評價,屬于主觀幸福感的認知范疇。本研究以小學生整體上自我感知到的生活滿意度水平作為其生活方面的測量變量。以往研究發現,學生的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幸福感呈正相關,有利于提高其生活滿意度(Chan, 2012; Yeoun &Seek, 2018)。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幸福感的積極情緒、參與度、人際關系、成就等維度呈正相關,而與抑郁和焦慮維度呈負相關(Kern, Waters,Adler, & White, 2015)。本研究推測,成長型思維模式或許可以通過影響認知,讓個體用更積極的方式對待挫折,進而擁有更好的情感體驗。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成長型思維模式可以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已有研究證實,兒童青少年的學業自我效能感是影響其情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郭筱琳等,2019; 劉在花, 2017)。高學業自我效能感能夠使青少年獲得更高的生活滿意度(Cikrikci & Odaci,201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4:學業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并在成長型思維模式與生活滿意度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考察成長型思維模式和學業自我效能感與小學生學業成績、生活滿意度的關系,探討學業自我效能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學業成績、生活滿意度的預測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參見圖1)。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對廣東省5所公立小學的1352名四、五年級的小學生進行問卷測量,有效問卷1161份,有效率85.9%。有效被試具體構成為:四年級287名,五年級874名;男生629名,女生532名;被試平均年齡10.32±1.42歲。
2.2 研究工具
2.2.1 思維模式問卷
采用Dweck(2006)的思維模式問卷,問卷包括4道題目,如“你的智力屬于你比較基本的特質,很難做出很大改變。”讓學生從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進行6點評分,前兩題反向計分,總分越高越表明學生具有成長型思維模式。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1,驗證性分析擬合良好(χ2/df=12.57, RMSEA=0.07,GFI=0.97, NFI=0.97, IFI=0.97)。

圖1 假設模型圖
2.2.2 學業自我效能感問卷
采用Lee,Yin和Zhang(2010)修訂的學習動機策略量表中文版中的學業自我效能感分量表,共7個條目,如“和班里的其他同學比起來,我認為自己會做得很好。”采用5點計分,得分越高表示學生的學業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該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是0.83,驗證性分析擬合良好(χ2/df=23.61, RMSEA=0.08, GFI=0.93, NFI=0.92,IFI=0.92)。
2.2.3 生活滿意度量表
采用 Diener,Emmons,Larsen和 Griffin(1985)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的中譯版,由香港大學Mantak Yuen教授于2002年修訂并翻譯(Wang, Yuen, & Slaney, 2009),該量表反映的是整體的生活滿意度,包括5個條目,如:“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7點評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滿意度越高。該量表已經被翻譯為26種語言版本,在世界范圍內應用廣泛,在我國也廣泛用于測量各個年齡群體的生活滿意度(范航, 李丹丹, 劉燊, 方圣杰, 張林, 2019)。一項法國的研究表明,該量表對8~16歲青少年兒童也具有良好的測量效果(Bacro et al., 2020)。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是0.80,驗證性分析擬合良好(χ2/df=8.77, RMSEA=0.08, GFI=0.98, NFI=0.98,IFI=0.98)。
2.2.4 學業成績
五所小學處于同一轄區,同年級期末考試試卷相同,本研究中的學業成績由小學生參與本研究的學期期末的語文、數學和英語成績分別標準化后,z分數相加得到的。
2.3 測試過程及數據處理
由經過培訓的主試向被試說明問卷填寫的注意事項和鏈接,采用電子問卷的形式進行調查。本研究采用SPSS20.0和AMOS17.0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統計檢驗(周浩, 龍立榮, 2004),共提取出4個因子,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3.49%,低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中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矩陣
相關分析表明,小學生的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自我效能感(r=0.18,p<0.01)和學業成績(r=0.22,p<0.01)呈顯著正相關,學業自我效能感與生活滿意度(r=0.29,p<0.01)和學習成績呈顯著正相關(r=0.35,p<0.01),參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
四年級和五年級的小學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t=-2.07,p<0.05)、學業成績(t=4.14,p<0.001)兩個變量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在其他變量上差異不顯著。具體表現為:成長型思維模式,四年級(4.30±1.42)顯著低于五年級(4.49±1.30);學業成績,四年級(1.61±1.22)顯著高于五年級(1.25±1.31)。
男生和女生在學業成績上存在顯著差異(t=-4.83,p<0.001),女生的學業成績(1.53±1.06)顯著高于男生(1.17±1.45),在其他變量上差異不顯著。
3.3 中介效應分析
通過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學業自我效能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績、成長型思維模式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中介效應(方杰, 溫忠麟,2018),結果顯示模型擬合良好,參見表2。然而,對各路徑的回歸系數檢驗后發現,假設模型中的成長思維模式-生活滿意度的路徑系數不顯著,p=0.083,刪除路徑,建立實際模型(見圖2),數據擬合良好,見表2。

表2 假設模型和實際模型比較結果

圖2 實際模型圖
如圖2所示,成長型思維模式直接預測小學生的學業成績,也通過學業自我效能感間接預測學業成績;學業自我效能感可以預測小學生的學業成績和生活滿意度。具體而言,成長型思維模式顯著正向預測學業成績(β=0.16,p<0.001)、學業自我效能感(β=0.19,p<0.001),學業自我效能感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學業成績(β=0.32,p<0.001)、生活滿意度(β=0.29,p<0.001)。然而,成長型思維模式不能預測小學生的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證實了假設1、假設2,部分證實了假設4。
進一步使用Bootstrap方法(抽樣次數為2000)對學業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進行檢驗。學業自我效能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和學業成績之間的中介效應為0.13,95%的置信區間為[0.05, 0.10],不包含0。因此,學業自我效能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和學業成績之間具有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應。標準化的總效應為0.32,直接效應為0.19,間接效應為0.13,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比值為40.62%。模型中的變量解釋了學業自我效能感3.4%的變異量,學業成績21.3%的變異量,生活滿意度8.6%的變異量。
4 討論
4.1 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小學生學業成績和生活滿意度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小學生的成長型思維模式顯著正向預測學業成績(β=0.16,p<0.001),與以往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結果一致。成長型思維模式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系數為0.05,且不顯著,不能預測生活滿意度,與假設3不符,說明成長型思維模式對小學生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不大。本研究中測量的是小學生整體上的生活滿意度。調查顯示,小學生的生活滿意度主要是家庭、友誼、學校的滿意度,且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習興趣、同伴關系、師生關系、學校氛圍、校內外課業負擔等多個因素有關(杜玲玲, 2018; 郭碧芳, 黃海,2017)。當前中國普遍重視素質教育,小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可能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成長型思維模式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不高,且不能預測整體生活滿意度也是合理的。可能在研究中考察小學生的學業滿意度會更有針對性。成長型思維模式需要在個體的生活與成長經歷中慢慢培養,因而不能過分寄希望于短期的成長型思維模式干預,更不能夸大這種干預的效果。
4.2 學業自我效能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與學業成績間的中介作用
成長型思維模式除了直接促進學業成績外,還通過學業自我效能感的部分中介間接促進學業成績。這與以往研究的結果一致(Blackwell et al.,2007)。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學習任務,這是取得學業和個人成功的基礎(McWilliams,2014)。Dweck(2006)認為成長型思維模式在學生遇到挫折時更能夠發揮其作用,當學生學業成績不佳時,具有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小學生更可能反思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能力進行重新評估,繼而付出更多的努力。學業自我效能感一直都對學業成績有較穩定正向預測作用(Costa & Faria,2018),本研究說明良好的成長型思維模式需要穩定內化的學業自我效能感,才能對個體發展產生更長久的影響。
4.3 小學生的成長型思維模式要通過學業自我效能感影響生活滿意度
本研究發現小學生的成長型思維可以預測學業自我效能感,且學業自我效能感可以預測生活滿意度。Dweck(2006)認為,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個體傾向于穩定的內部歸因,長期的內部歸因加上成功的經歷會不斷提高個體的學業自我效能感,而學業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又會使小學生面對生活難題時更加積極,進而提升其生活滿意度。在具有挑戰性的學習環境中,成長型思維模式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保護因子,有助于維系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Blackwell et al., 2007; Schroder et al.,2017)。成長型思維模式有助于小學生正確看待學業過程中的挫折和壓力,在客觀評價自己的基礎上,擁有更高的生活滿意度(余芝云, 連榕, 2019)。雖然成長型思維模式不能直接預測生活滿意度,但其可以通過個體在學習中不斷獲得學業自我效能感來進行強化,使得個體在客觀認知自己的基礎上提升生活滿意度。
成長型思維模式的提出者Dweck(2008)明確表示成長型思維模式是能夠培養的,固定型思維模式也能夠轉化為成長型思維模式,并且已有一系列研究證明這一點(Blackwell et al., 2007; Cooley &Larson, 2018; Dweck, 2008),但成長型思維模式想要穩定發揮作用還需要借助學業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因此家長和老師可以通過培養小學生成為自我激勵、自我指導的成長型思維模式者,引導他們進行正確的內部歸因,提升學業自我效能感,進而達到提升學業成績和生活滿意度的目的。同時,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本研究收集的是橫斷數據,不足以了解成長型思維模式的積極作用是如何縱向進行發揮的;另一方面,本研究均為小學生的自我報告,未來的研究可以綜合家長和學校老師的視角,進一步探討外在環境對個體的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影響。
5 結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成長型思維模式能夠正向預測小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業自我效能感在成長型思維模式和學業成績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成長型思維模式可以預測學業自我效能感,學業自我效能感可以預測生活滿意度。可見,小學生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優勢發揮依賴于學業自我效能感的獲得,在培養小學生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同時,要積極幫助其獲得學業自我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