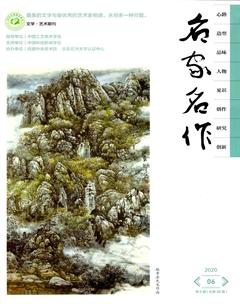跨界文化生態下電影敘事的游戲化策略
杜子棟
[摘 要]隨著互聯網的繁榮發展,網絡游戲方興日盛,它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著電影的影像敘事,電影與游戲的跨界互融已成為當下最值得關注的電影現象。
[關鍵詞]跨界文化;電影敘事;策略
電影與游戲的跨界互融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為游戲電影化。主要是指對游戲進行電影化改編,集中體現在影像視聽方面的大突破,其中不乏對好萊塢電影中大場面、大景別的移用,快速蒙太奇的節奏置換等電影技術營造出虛幻場景和震撼的視聽效果。此外還表現在對敘事層面的強調,在游戲中增添情節設計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畫。其二則是電影游戲化,游戲元素的加入打破了“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的真實性原則,利用電腦合成技術把天馬行空的畫面和千奇百怪的想法運用到電影文本內,模擬出更為立體的虛幻空間以打破電影固有的時間和空間界限;敘事線索也打破了傳統的線性結構,按照非理性的思維進行影像表達,以游戲的娛樂化消解電影的嚴肅性。值得說明的一點是,游戲電影化的范疇指向為游戲,而電影游戲化的立足點仍為電影。本文將在游戲化策略下對電影本體和電影產業的發展變化做簡要評述。
一、虛擬化的視覺風格
電影與游戲之所以能相互轉化,存在一個根本的前提條件:即兩者均強調感官上的視聽滿足。游戲對場景及音效的追求與電影的奇觀化表達可謂殊途同歸。
1.電影場景的虛擬化呈現
電影游戲化最突出的一個表征就是借助對游戲場景的模擬,創造一個全新的夢幻樂園,主要表現為對異域空間的探索,如《生化危機》中“生物工程實驗室”,以及《流浪地球》中維度空間的虛擬化成像等,在拓展影片的背景空間之外也滿足了觀眾在心理層面求新求異的情感訴求。電影本身就充滿夢幻色彩,是一個造夢機器,觀眾在封閉幽暗的影院中逃離現實,進入自身的假想世界。互聯網塑造了一個巨大的“無形空間”,游戲也同樣構筑了一個與現實相背離的世界。游戲不只是實際的現實化,一種模擬現實,還是一種象征性的現實化,是一種神秘。它可以以某種不可見的、不現實的東西帶來美的、實在的、純凈的形式。電影時空的虛擬化不僅為故事提供了廣闊的異域場景,增添了多樣的故事內容,更重要的是通過虛擬化的營造,觀眾能在其中拋棄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尋求獲得性的滿足。
2.后現代的拼貼風格
多媒體的快速發展使我們步入了視覺文化的今天,天馬行空的文字想象能有效轉化為視覺表達。美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游戲改編電影的熱潮,廣受關注的有《最終幻想》《生化危機》《古墓麗影》《寂靜嶺》《殺手47》等口碑與票房兼收的影片。在游戲化的電影影像中呈現出拼貼化的風格特征:《生化危機》和《古墓麗影》利用電腦合成技術把真人與游戲場景拼貼在同一畫面中…,真人拍攝與CG( computergraphics)技術的相互融合體現了電影與游戲兩種不同娛樂形式的融合與共生。影像拼貼除了表現為真景與虛景的融合外,不少影視作品在影片中時常穿插動畫鏡頭。《誰陷害了兔子羅杰》《愛麗絲漫游仙境》《博物館奇妙夜》等代表影片均采用真人與動畫人物雙角色的共同出演,展現了人與動物無阻礙。
電影在視覺表達上成功借鑒游戲元素,對異域空間的虛擬呈現以及通過不同風格樣式的拼貼形成獨具一格的美學范式,拓展了電影地域的空間,增強了電影的畫面表現力,虛擬化場景實質上為觀眾提供了真實想象。
二、多元化的敘事結構
1.通關式的劇情線索
游戲的終極主題就是“通關”。玩家根據人物的特征與技能進行人物挑選,任何關卡的設置都依靠自己的能力決定成敗。徐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把電影當游戲通關打怪那樣拍。他將《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的臥底行動與電子游戲的打關任務相類比,無論是基于原著小說還是之后京劇、老版電影等藝術形式的改編都把“打虎上山”作為一個隱喻手段以表現楊子榮上山之路的艱難。[2]而徐克對原故事進行了個人化風格的詮釋:在楊子榮臥底之旅的關卡中,第一個關卡設計就是楊子榮經歷一番努力去說服隊友,讓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和實力承擔上威虎山的重任。那第二個關卡障礙就是大自然,楊子榮要沖破多重自然挑戰,老虎和雪山成了成功之途的絆腳石。最后一個關卡則是涉及生死命運的危難關頭,楊子榮如何獲得座山雕的信任成為影片的終極挑戰。徐克對“智取威虎山”的改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戲化元素對影片劇情的功能性參與,對電影敘事的結構性輔助。
2.扮演類的角色設定
在眾多游戲類型中,角色扮演類絕對是無法忽略的一個重要類型。角色扮演游戲的核心在扮演,玩家扮演一個角色在一個寫實或虛構的世界中活動。而玩家所扮演的這個角色在結構化規則下通過一些行動令所扮演的角色發展。在一些影視作品中,不乏角色扮演類影片。片中主角通過對另一人物身份的扮演,體驗不同的人生處境以達到對自我內心的審視以及對精神的放逐。馮小剛在他的喜劇電影中善于利用角色扮演來促進劇情發展,無論是《甲方乙方》還是《私人定制》都是在“圓夢”的故事架構中上演人與人之間的位置對換,由于對自身現實生活的不滿激發出他們對理想生活的期待,《甲方乙方》中板兒爺對巴頓將軍的崇拜,廚子愿守口如瓶;以及《私人定制》中司機對金錢物欲的抵制, “最俗導演”對高雅的追求,清潔大姐向往有錢人的生活。 “角色扮演”在很大程度上來講就是一種游戲,導演馮小剛通過對底層平民人生的游戲化書寫從而對社會存在的貪污腐化、趣味低俗的現狀進行批判,由此表達現代人生活的焦慮與不安。“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互相了解;也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認識了我們自己。”在電影游戲化創造的假想空間中,主角通過凝縮自身的情感訴求并移植到扮演角色中去,對之施加必要的行動。可以說,故事中人物是扮演者乃至觀影群眾意志的外化表現,“我”的思維意識投射到角色當中,在潛意識中完成“我”與角色的雙向認同。
游戲化的敘事模式為角色對現實的情感接受提供了更多的遐想與回味,他們仿若置身于夢幻情境之中,憑借自身的感觀經驗對社會現實走向充滿理想化的幻想。導演正是運用游戲手段使影片內容更加貼近生活,以荒誕化形式使角色和觀眾宣泄不滿情緒,進而展現更加真實的生活。
三、游戲IP改編延伸電影產業鏈條
1.游戲改編電影的出路
隨著電影在影像呈現方面的不斷突破以及游戲在敘事層面的強化,兩者逐漸走向互融趨勢。不少游戲改編為電影在大銀幕上映,也有電影的同名游戲線下發行。我們不難發現:游戲改編成電影能獲得良好口碑和收益,與此相反,電影改編為游戲則很難在市場上形成氣候;國內與國外的制作水準更是存在巨大反差。從改編較為成功的《寂靜嶺》《生化危機》《侏羅紀世界》《最終幻想》等來看,國外熱衷對大型格斗、冒險類游戲進行改編,且較為成功;而國內此類型電影極其缺乏,根據兒童社區游戲《洛克王國》改編的系列電影在同質化的市場下脫穎而出,但未能引起足夠反響。究其原因,縱然在互聯網時代下電影與游戲相互融合,但仍舊屬于兩種不同的娛樂形式。電影是導演制造的一場夢境,是虛構性的存在;而游戲是設計者研發的一次探險.是虛擬化的營造。觀眾對電影與游戲的接受目的也不盡相同,他們對電影抱以期待以達到對自己的想象認同,而在游戲中卻是以通關能力佐證自己。電影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而游戲則在互聯網時代下應運而生,傳統工業與新型元素的不兼容也是導致兩種不同形式無法實現轉化的重要原因。在科技當道的今天,電影藝術向前發展離不開對其他形式的取長補短,而更好地實現兼容還需要對電影本體的不斷探索。
2.聯合發行,共同營銷
國外電影與游戲之間的相互轉化呈現出蔚然可觀之勢,由游戲改編的電影在市場上收益頗豐。反觀當下國內電影市場,根據游戲改編的電影寥若晨星,反而是電影改編成游戲IP在業界掀起風浪。據《北京商報》的不完全統計,2014年國內共有311部電影在院線上映,其中59部電影有同名游戲,包括32部國產電影及27部海外電影。但是接受調查的觀眾超過八成對同名游戲持懷疑態度。其中對《痞子英雄:黎明升起》的同名游戲,有玩家表示該游戲其實只是一款借了電影外殼,游戲內容與電影并無太大關聯的普通消除類游戲。[3]電影同名游戲制作不良,難以在市場上贏得好聲譽。還有一部分電影以文本故事參與游戲研發,趙薇導演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與熱門手游《找你妹》結合在一起,游戲中設置了以“致青春”為主體的青春版關卡,并在該版塊中增添了主角的漫畫頭像,電影場景中出現的道具成為游戲的基本元素。同樣以元素符號參與游戲的還有《單身男女2》與騰訊手游《天天來塔防》的跨界合作,套用并延續了影片中的劇情,以影片男女主人公作為游戲的闖關者與守護者。國內電影市場電影與游戲似乎形成了捆綁式合作,《心花路放》《分手大師》《爸爸去哪兒》等也相繼推出跑酷類益智游戲。
盡管將電影中的影像元素幻化成游戲情節,緊密切合電影的主題,有效地為影片做了積極宣傳,同時也擴大了游戲的影響力,但值得說明的是,倘若研發商沒有在游戲中注入創新思維,而是對同類型游戲的簡單效仿,那么此游戲的生命力不會長久,更不具備核心競爭力,只會成為一個個“現象游戲”在市場上曇花一現。
綜上所述,電影和游戲在互聯網迅速發展的新形勢下呈現出視覺主導下對敘述追求的新趨向。在游戲化因素參與下,無論是影像風格還是敘事策略,電影都產生了新形式的變化;游戲與電影的雙向營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資源整合,便于實現跨文化的有效互通=但是國內市場上粗制濫造、品牌不精的創作現狀令人擔憂,多數制作公司以“利益至上”為原則參與電影與游戲的跨界合作,某種程度上擾亂了市場秩序,中國電影產業化道路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荷]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10.
[2]盧揚,鄭蕊.電影游戲超八成淪為市場炮灰[N].北京商報,2015-01-09.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話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