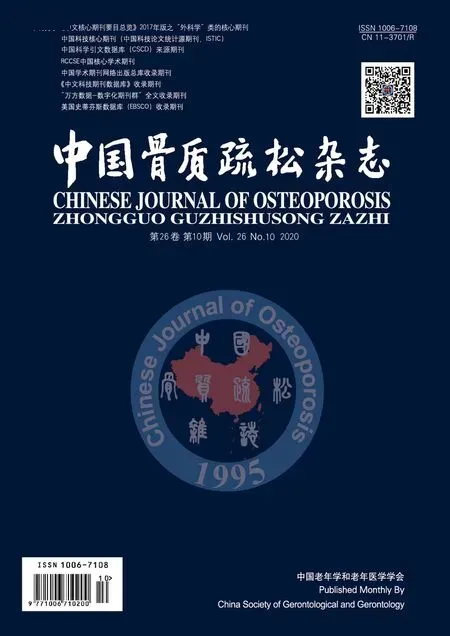持續運動鍛煉對絕經后女性骨密度影響的追蹤研究
王晶晶 郭彥君 項云
1. 上海體育科學研究所,上海 200030 2. 上海體育學院,上海 200438
老年人骨骼隨年齡增長出現增齡性衰退,表現為骨量流失、骨密度下降、骨強度降低。骨密度的持續降低可能發展為骨質疏松癥。隨著全球老齡化問題的不斷加劇,骨密度降低發生率及骨質疏松患病率隨之增加,相關疾病負擔也因此加劇[1-3]。增齡和絕經同為誘發骨質疏松癥的不可控危險因素[4]。絕經后女性因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骨量加速流失,骨組織微結構損壞,骨密度持續降低。相較于男性,女性在50歲以后骨量下降迅速,骨質疏松發病率急速增長[5],進而因骨質疏松性骨折而造成更高的疾病負擔[6]。
體力活動已被證實可以有效改善成老年人骨骼健康[7]。對于絕經后女性,規律的包括運動在內的體力活動可以改善骨密度水平或延緩其流失,預防或改善骨質疏松,并有效減少骨質疏松性骨折的發生[8-9]。多數研究關注于幾個月的短期運動鍛煉對骨密度可能產生的影響,但12個月或更長時間的持續運動鍛煉或許才能對絕經后女性的骨密度產生明顯的改善作用,因此關于運動對骨密度的中長期功效研究仍需增加[10-11]。本研究對社區絕經后女性骨密度進行12個月的追蹤研究,比較不同運動鍛煉參與程度者的骨密度差異、以及骨密度水平在12個月間隨時間變化的趨勢,為持續運動鍛煉對骨密度可能產生的中長期功效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在上海市楊浦區五角場、平涼兩個街道招募志愿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了解招募對象的基本健康情況,之后對符合納入條件者進行知情告知,并簽署知情同意書,采集其基線骨密度數據。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為:50~69歲女性;閉經2年以上;有獨立生活能力;無先天、遺傳性疾病(如先天性心臟病、聾啞、癡呆、精神異常等);近期(1年內)無確診的代謝類疾病(如糖尿病、甲狀腺疾病、甲狀旁腺疾病等內分泌系統疾病);無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近期(1年內)未服用過激素類藥物;從不吸煙;自愿參與本研究。
通過問卷調查結果將納入的研究對象按照體育人口劃分標準[12]分為鍛煉量達標和不達標組。其中鍛煉量達標組需滿足鍛煉量達到主述每周參與至少3次、每次至少30 min的中等及以上強度有氧運動;不達標組進一步根據運動參與情況分為不鍛煉亞組(從不鍛煉)和偶爾鍛煉亞組(參與鍛煉,但是鍛煉的頻率、時間或強度未達到經常鍛煉標準)。之后對各組別研究對象進行12個月的追蹤研究,每周記錄研究對象體育鍛煉參與情況,并在6個月、12個月追蹤采集其骨密度參數。12個月間鍛煉量達標組中斷鍛煉1個月及以上者,從不鍛煉組參加鍛煉1個月及以上者、或偶爾鍛煉組鍛煉量達到經常鍛煉標準超過1個月者,以及追蹤期采用營養補劑或藥物手段干預骨密度者均不納入統計。
研究在基線招募符合條件的受試者103人。經過12個月的跟蹤,未退出研究、且維持原有體育鍛煉參與情況未改變者為82人。最終納入研究對象基本情況見表1。各組間基線年齡、閉經年份、身高、體重和BMI差異均無明顯的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研究對象基線參數Table 1 Demographic and anthrop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t baseline in the
1.2 方法
采用定量超聲(QUS)檢測法測量跟骨骨密度,儀器為GE Achilles InSight超聲骨密度儀,采集指標包括T值、Z值、超聲傳導聲速(SOS)和超聲寬帶衰減(BUA)。并提取測試結果中的骨質疏松發生風險數據,以T≥-1.0為可能存在骨質疏松低度風險;-1.0 采用問卷形式采集研究對象的性別、年齡、閉經年份、體育鍛煉參與情況等數據。采用國產健民牌Ⅱ型國民體質測試系列身高計、體重計采集身高和體重數據。根據身高體重計算BMI。 采用SPSS 22.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所有描述性統計數據均表示為均值±標準差,采用例數(百分比)描述各組內不同骨質疏松發生風險水平的檢出情況。采用K-S檢驗對各組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各分組內各指標時間點間的比較采用單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采用兩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比較鍛煉量達標和不達標兩組在12個月間T值水平隨時間變化的時間效應、組間效應及交互效應,對不滿足Mauchly球型假設檢驗的數據,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進行校正。對存在交互效應者,進一步分析各因素的單獨效應。基于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對與T值存在相關的變量進行控制,分析控制混雜變量后兩組間T值變化隨時間變化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統計學顯著性水平為P<0.05。 各組跟骨骨密度各指標在12個月間的變化情況見表2。可見,鍛煉量達標組各時間點的各指標水平隨時間變化不大,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達標組骨密度各指標水平隨時間出現下降,除SOS值外,鍛煉量不達標組T值、Z值、BUA水平隨時間變化均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劃分不達標組的亞組后可見,兩亞組骨密度各參數水平隨時間的下降幅度不同,不鍛煉亞組隨時間的降幅較偶爾鍛煉亞組更大。 表2 各組跟骨骨密度指標12個月間變化Table 2 Changes in the BMD parameters during 12 對鍛煉量達標和不達標組T值隨時間變化的組間差異統計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T值隨時間變化的差異具有明顯的統計學意義(F=6.378,P=0.004),對比檢驗結果發現呈線性關系(F=8.707,P=0.004);鍛煉量達標組和不達標組的組間效應存在明顯的統計學意義(F=4.268,P=0.042);時間×組間存在交互作用(F=5.702,P=0.007),兩組間T值隨時間變化的幅度不同,鍛煉量不達標組T值下降幅度較大,達標組T值幾乎無變化。進一步統計分析顯示:基線時,鍛煉量達標組和不達標組間T值差值為0.42,差異不存在明顯的統計學意義(F=1.784,P=0.185);6個月和12個月后兩組間T值差值分別為0.64(F=4.963,P=0.029)和0.74(F=6.814,P=0.011),差異均具有明顯的統計學意義。 表3 鍛煉量達標與不達標組T值隨時間變化的組間比較統計學結果 由于T值變化水平與年齡(r=0.307,P<0.05)和閉經年份(r=0.231,P<0.05)均具有一定統計學意義的線性相關。表3同時列出了分別控制了年齡和閉經年份后鍛煉量達標和不達標組T值隨時間變化的兩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可見,在分別控制了年齡和閉經年份后,T值的組間效應、時間效應和交互效應均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所有研究對象在12個月間,發生骨質疏松高度風險的人數比從18.3 %增長至23.2 %,低度風險的人數比從36.6 %降低至30.5 %。劃分鍛煉量是否達標后,兩組不同骨質疏松風險發生等級的分布情況在12個月間的變化見表4。可見鍛煉量達標組12個月間骨質疏松風險各等級人數分布基本維持穩定;不達標組,低度風險等級人數比在12個月間逐漸減少,高度風險人數比逐漸增加。 表4 鍛煉量達標與不達標組12個月間骨質疏松風險等級分布變化[n(%)] QUS檢測法因其與公認診斷金標雙能X線吸收(DXA)檢測法結果的高度相關,以及便攜、無輻射、節約時間、低成本等優勢,常被推薦用于人群的骨質疏松風險篩查和骨折風險預測[13-14]。在評價運動干預對骨密度的改善效果時,采用DXA法進行重復短間隔多次測試可能涉及到增加輻射暴露、增加成本等問題,可以采用QUS法追蹤運動對各年齡段人群骨健康參數隨時間變化的影響[15]。本研究中有8名流失的研究對象是因其參考基線QUS法測得的中高度風險結果至醫院進行DXA法診斷并進而采用藥物治療后退出本研究,側面提示了QUS法對篩查社區女性骨質疏松或骨量降低發生風險的可行性。 SOS和BUA是QUS法用于評價骨密度水平的主要參數,分別指超聲信號在骨骼中的傳導速度,和超聲信號通過骨骼時因骨組織的吸收和散射而發生的超聲能量信號衰減,二者均與骨密度水平呈良好正相關。T值和Z值分別指骨密度水平相較同性別健康人群骨密度水平峰值和相較同性別同齡人骨密度平均水平的標準偏差。T值是預測骨量減少和骨質疏松發生風險的常用指標,基于QUS法測得的T值對絕經后女性骨質疏松及骨折的發生風險具有較好的預測效果[16]。本研究最終納入的研究對象總體在基線存在骨質疏松高度風險的人數比為18.3 %,其中50~59歲為11.0 %,60~69歲為27.0 %。這一結果總體略低于張智海等[17]基于DXA的我國人群骨質疏松發生率的文獻分析結果。這可能與本研究納入了較自然人群更多的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者有關。進一步劃分鍛煉量達標與不達標組后,不達標組骨質疏松高度風險人數比為20 %,并在12個月后增長至30 %,這一結果與報告的我國人群骨質疏松發生率水平基本一致,一定程度上提示QUS法可以用于輔助預測絕經后女性骨質疏松的發生風險。 運動對骨骼健康的促進作用,從生物力學角度講是由于運動的機械應力對骨骼造成的良性刺激,從生物化學角度講是由于運動誘導激素變化、調節骨代謝信號通路,進而對骨代謝產生積極作用所致[18]。運動作為公認的非藥理干預手段,可用于延緩中老年人骨量流失[19]。本研究各個時間點的測試結果中,鍛煉量達標組骨密度的各指標水平均優于不達標組,同時達標組骨質疏松低度風險人數比相較不達標組更高,高度風險人數比更低。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是否控制年齡和閉經年份等骨密度影響因素,達標組和不達標組的T值水平差異始終存在顯著的統計學意義。這些結果均提示了規律的運動鍛煉對絕經后女性骨密度有積極的改善作用。 不同的運動類型、運動頻率、運動持續時間、運動量等對于骨密度可能產生的影響并不相同[9]。通常認為,運動類型方面,身體負重的中等強度以上有氧運動或抗阻訓練有利于絕經后女性的骨量維持[20-21];時長方面,平均每天鍛煉時間大于30 min的老年人骨密度水平明顯優于不鍛煉和少于30 min者[22];頻率方面,每周至少2次的體育鍛煉才能對骨密度產生積極影響[23];運動量方面,相較中等運動量(150 min/周),大運動量(300 min/周)女性骨密度水平更高[24]。本研究中,盡管基線時不鍛煉組骨密度水平略高于偶爾鍛煉組,但12個月后,不鍛煉組骨密度各指標水平降幅更大、降速更快。提示不同程度參與運動鍛煉可以不同程度地維持絕經后女性骨密度水平或延緩其增齡性流失,即使體育鍛煉參與程度并未達到經常鍛煉水平,但偶爾參與,也可能因每次鍛煉時長、頻率或類型等達到一定劑量,而對絕經后女性骨密度水平產生積極影響。 規律運動有益于促進包括骨骼健康在內的老年人身體健康[25]。長時間參與運動鍛煉,對絕經后女性骨密度具有積極改善作用[26],并且可持續長達16年[27]。目前對于可有效改善骨密度的鍛煉持續時間的觀點并不一致,有研究認為,干預時間超過12個月的有氧鍛煉能更好地改善骨密度[12];也有研究認為持續7個月、頻率大于2次/周的規律運動是改善絕經后女性骨密度的最短時長[28]。 總體來講,本研究各組SOS值和BUA值水平均在12個月間出現了下降,提示了不論參與鍛煉與否,絕經后女性的骨密度水平均會隨年齡增長逐漸下降。但不同分組的下降程度有所不同。相較鍛煉量不達標組,鍛煉量達標組在12個月間骨密度各指標水平只出現極小程度的下降。進一步劃分亞組后,不鍛煉組下降幅度高于偶爾鍛煉組,提示規律運動對于絕經后女性的骨量維持并延緩其流失有良好的作用效果。另外,盡管組間無明顯統計學差異,但本研究中鍛煉量達標組平均年齡比不達標組稍大,理論上骨密度水平可能更低。然而實際測試結果顯示達標組骨密度各指標水平不僅在基線就略高于不達標組,且12個月間骨密度水平基本維持不變,而不達標組T值、Z值、BUA水平均隨時間呈現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顯著下降,SOS水平亦出現下降。另外,達標組Z值水平始終大于0,即骨密度水平優于同齡人;不達標組Z值從基線的略高于0下降至小于0,即骨密度水平由接近同齡人水平下降至低于同齡人水平。盡管不能排除個體差異和未知混雜因素,但這些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提示了規律鍛煉可能在延緩絕經后女性骨量流失中發揮重要作用。基于T值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是否調整年齡和閉經年份,鍛煉量達標組與不達標組間隨時間變化均有顯著的時間效應和組間效應,提示盡管骨密度水平會隨時間出現增齡性下降,但持續規律的參與運動鍛煉可以有效延緩絕經后女性骨密度的增齡性流失。 后續研究計劃選擇基于精準測定的DXA檢測法,更有針對性、樣本量更大的社區絕經后女性進行更長時間的持續追蹤觀察,以彌補現有研究不足,并觀察更長時間周期內不同運動鍛煉參與程度女性骨密度水平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不同程度參與運動鍛煉可以不同程度地維持絕經后女性骨密度水平或延緩其增齡性流失。不同鍛煉量水平的絕經后女性,骨密度在12個月間隨時間變化并不相同,不鍛煉者骨密度隨時間下降幅度最大,偶爾鍛煉者骨密度的增齡性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緩,經常鍛煉者骨密度水平基本維持穩定。持續參與運動鍛煉對絕經后女性骨密度增齡性流失具有積極的改善作用。1.3 統計學處理
2 結果



3 討論
3.1 QUS法追蹤骨密度隨時間變化的可行性
3.2 運動鍛煉對絕經后女性骨密度的影響
3.3 持續參與運動鍛煉對絕經后女性骨密度的作用效果
4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