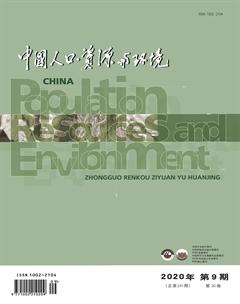生態問責制度對政商關系轉型的影響分析
程宏偉 胡栩銘



摘要?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點在于探索行之有效的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力求規范企業污染并監督地方治理主體,打破政企環境套利空間,因此轉變政商關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當前研究前沿重點。以2015—2018年中央環保督察組完成首輪31省區市巡視問責為契機,研究針對各省區市不同入駐時間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以可能產生污染的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了生態問責對政商關系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①地方政府在經歷生態問責后發放政府補助時會更加謹慎,尤其減少軟約束性補助,但不會降低對公司環保創新的扶持。②生態問責同時具備了強政治壓力與環境規制執法的雙重影響,細分研究發現其中生態問責的政治壓力作用強于環境規制作用。③進一步的,企業政治聯系中產權性質與聘用具有政治背景高管均會影響生態問責效力。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能夠避免生態問責影響。因聘用具備政治背景的高管而獲得的財政補貼在生態問責下難以保持。④地方對企業的高財政依賴會抵消生態問責效力,但在面對政治壓力時地方財政影響無效。⑤對污染治理投資結構優劣不同的地區生態問責的作用存在著顯著差異。該研究表明生態問責迫使地方政府將地區環境納入維持政治穩定的考量,削弱了地方以往建立的政商關系,并約束地方的任意性行為,優化地方資源配置,開始樹立新型政商關系。
關鍵詞?生態問責;政府補助;環境規制;政治壓力;政商關系
中圖分類號?F205;F812.4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20)09-0164-13??DOI:10.12062/cpre.20200416
以往研究中關于我國經濟增長的主流觀點之一是政企合謀通過犧牲環境等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1-3]。利益會滋生地方政府與企業間的機會主義,致使資本裹挾生態,López和Mitra[4]就曾指出政企合謀會導致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拐點提高。因此轉變政府與企業合謀的經濟發展方式,既是社會發展新階段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具備轉型基礎的現實需求。環境的破壞源于企業的不良生產運營,更源于政府對自然這個公共物品管理保護的不力。如果中央政府不能約束當地執政者就會造成事實上的“新自由環境主義”局面[5],使得他們享有高度的自由和靈活性來管理自己的能源消耗,導致環保政策的執行效果無從保障。因此把責任歸于當地政府和公司,所采取的行動將更有效率[6]。自2015年起我國逐漸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導向,以產業升級為契機,以技術創新為核心,以生態問責為手段,加大官員晉升考核的環保風險因素,試圖對以往的政企合謀發展方式進行根本矯正,從而樹立風清氣正的新型政商關系。至2018年我國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反饋共責令整改28 407家企業,罰款7.1億元,約談3 695人,問責6 219人,同時首次出現亞邦股份和輝豐股份兩家上市公司因環保問題違規而被實施“ST”。地方政府與企業長期博弈中形成的環境經濟利益關系,在面對生態問責的政治壓力時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嵌入政治問責的高壓執法使得環保問題成為上市公司必須重視的重要風險因素。基于中央環保督察組2015—2018年對全國31省區市開展的首輪巡視督察,選取上市公司樣本,研究檢驗了生態問責下政治壓力與執法強度對政商關系的影響及其影響因素。生態問責下政商關系是否會被削弱,代表了生態問責后企業與地方政府是否會謹慎對待利益結構中的環境問題。因此問責期間政商關系的轉變直接反映了我國特有背景下生態問責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再至企業的傳導有效性,而政府補助資源配置的變化則體現了政府治理重心的改變。
1?制度背景及理論分析
1.1?生態問責制度背景
在我國“十一五”規劃期間的環保規劃研究中就有學者指出,在形成生態紅線管理范式的同時,需要建立嚴格的績效評估機制,以衡量地方政府對環境法律和政策的執行情況[7]。各級政府及有關機構之間需要加強生態管理合作,同時更要明確界定各級政府對資源和環境管理的責任[8]。2015年1月,被稱為“史上最嚴環保法”的新修《環境保護法》開始實施,同年《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印發施行,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開始邁入問責制度構建階段,生態監管和環保執法體系得到重構。同年成立中共中央環境保護督查委員會,督察組于2015年年底入駐河北省,并于2018年完成首輪31省區市巡視工作。巡視期間接受群眾舉報,約談、問責大量官員并對違規企業進行嚴厲處罰,為地方政府與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環境政治高壓與執法強度。全文所提生態問責均指代2015年后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地方開展系列工作的事件。
地方政府可能會因為財政分權、金融開放、競爭等因素導致環境規制失靈[9]。問責前的環保執行體系中以環保部為核心,地方環保廳、局根據企業排放指標監測控制企業環境污染,但存在的突出矛盾在于其人事財權受制于地方政府,缺失了獨立性,使得環保部門執法力度存疑。同時地方政府與企業在考慮經濟利益的導向下對環境進行的控制與補償不足,由此產生了環境套利空間。隨著生態問責制度的逐步確立,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合謀空間被打破。環保部不再是問責制度的核心,生態問責體系下中央環保督察組依據地區綜合環境質量直接追責地方政府,直接影響地方政府官員政治生涯,擠壓了政企之間的合謀套利空間。
1.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生態問責具有政治壓力與環境規制的耦合性,因改變地方考核風險因素與資源分配方式而影響政商關系。
首先生態問責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問責與反腐敗相關研究。在經典文獻中政治問責主要以契約理論[10]、委托代理理論[11]、代表理論[12]等作為理論基礎,其核心概念在于政府需要就治理政策對民眾進行回應[13-14]。反腐敗的基本性質是對基于黨政領導干部經濟、政治、作風犯罪行為的懲戒,近年來眾多學者已在刑事考量[15]、審計[16]、反腐成效[17]上進行了諸多探討。雖然環境惡化某種程度上的確是一種政策失敗的結果[18],腐敗會降低環境規制的嚴格性也已被證實[19],但官員犯罪并非是生態問責的必要前提,生態問責的核心在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生態治理能力、社會治理能力與地區執政能力的考察,對生態亂作為或不作為進行追責。因此值得關注的是,即便官員未曾腐敗犯罪,其公共職權下的環境表現仍然對其政治生涯具有“一票否決”的影響。我國建立了由上至下的黨政領導責任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環保考核風險,使得當地政府對污染企業的環保執行力度得到有效保證。
其次,十九大指出社會主要矛盾由物質需求轉變為社會需求與心理需求,需要著力于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良的政商關系便會導致政府資源分配的不平衡與不充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變革需要全面建立新型的“親”“清”政商關系[20],而官員政治生涯預期的改變與激勵機制的重塑必然要求官員改變與企業的交往方式。與此同時地方GDP增量進入平緩時期,使得地方政府以犧牲環境換取的經濟利益小于在生態問責下所面臨的政治風險,政府面對企業的態度與投資行為或許將變得更為謹慎,政府補助資源的分配得到重新考量。
政商關系的變化與政府主導的產業發展方向在企業年報中體現于政府補助、稅收優惠等指標,尤其是從政府補助總額、分項內容與性質等能夠更加細致地進行解讀。企業所享有的財政福利、優惠補貼始終是建立政治聯系、達成隱性契約的最直接結果[21]。政府補助通常旨在提高社會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但也可能會成為企業尋租的對象[22]。通過政府補助項目能夠獲知政府與企業的合作行為以及產業發展方向,從而進一步觀察生態問責的執行效果。因此下文主要以政府補助作為研究生態問責下的政商關系變化的切入點。
在以往研究中,政府補助通常根據效率理論觀與尋租理論觀開展研究。效率理論正面觀點認為政府補助作為國家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能夠有效避免企業落入僵尸困境[23],促進企業創新[24];而負面觀點則認為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政府補助越多其投資效率越低[25],IPO公司政府補助越多其市場業績越差[26]。尋租理論則主要結合政治聯系進行討論,由于政府補助沒有嚴格律法標準,留給地方政府的自主空間大且界限模糊[21],企業具有強動機與政府達成合謀以獲取政治影響優勢下的利益[27],因此在企業擁有政治聯系時尋租行為更容易發生。政治聯系還會導致政府補助運作效率低下[28]。但政治問責能夠減少尋租[29]與機會主義行為[30],意味著政企之間的非合理聯系在生態問責下也可能減少。綜上,提出假設1。
H1:生態問責會使以往的政商關系被削弱。
進一步的,生態問責在向下傳導的過程中既對企業執行了環境規制也對地方政府施加了政治壓力。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政治力量的介入對避免資本壟斷、維持生態穩定具有重要作用[31-32]。環保監督使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新的博弈模式,生態問責帶來的政治壓力由于主體明確有效糾正了“權責不一”現象[33],促使政府提高其履責水平。另一方面,觸發企業環境主動性的基本因素是環境動機[34],這些動機主要體現為商業導向和可持續導向的動機[35],分別強調經濟績效和道德法制要求。而中小企業考慮環境問題的主要動機是滿足立法要求,道德責任其次[36],可見環保執法才是規范污染終端的直接手段。因此執法力度與政治壓力都可能會影響地方政企雙方對待環境問題的處理方式。政治壓力從根本上擠壓了政企環境套利的空間,規范政府行為才是保障執法的前提。因此,提出假設2。
H2:生態問責中的政治壓力對政商關系的影響強于環境規制執法的影響。
財政分權理論[37]認為地方政府競爭能夠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38],但也會產生政府的無效率競爭和企業尋租行為[39],為謀求經濟績效而枉顧生態損害。如果進一步討論政府補助的性質,則政商關系中的尋租空間多通過任意性的政府補助與投資實現,步丹璐和王曉艷[40]就曾將政府補助分為硬約束類型和軟約束類型,約束性弱的補助類目更容易被地方政府進行不合理操控,流向資源配置效率低但財政依賴度強的產業。因此環保督察帶來的中央生態問責壓力或許能適當地規范資源配置,并且約束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間的不當競爭。
有學者指出對政府問責會導致官員的避責與不作為等消極行為[41-42],也有地方政府在面臨利益沖突與復雜生態壓力時會采取臨時性的短期措施[43-44]。環保督查會導致被監督地區企業減產,而企業的環保投資并未顯著增加。這表明地方政府在被問責后可能會產生 “一刀切”行為,直接關停部分企業或減少政府支持,以不作為或少作為來避免 “多做多錯”的風險[45]。相對于有明確法規標準與目的用途的補助,被問責的地方政府易于首先選擇減少軟約束性補助中的不合理部分。但中央環保巡視的目的不僅僅是打擊政企環保套利,更重要的是優化地方環保治理的政治生態和執法環境。因此從提高資源效率、產業轉型與長期發展的角度出發,即使總體上政商關系因生態問責而削弱,綠色創新型產業仍然應當得到保護與發展。綜上,提出假設3。
H3a:生態問責會約束政府任意性行為減少軟性補助。
H3b:生態問責會促進綠色創新型產業發展,增加環保創新類補助。
2?研究設計
2.1?研究模型
由于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入駐每個省區市的時間點不同,因此借鑒Beck等[46]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Multiphase DID),構建以政府補助為因變量,生態問責為主要觀察變量的基本模型(1)進行檢驗。
其中,Subsidy為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變量,Xp,t和Ei,t分別為一系列隨時間變化的區域特征變量和公司特征變量,Ai與Bt分別表示公司和年份啞變量用來控制公司個體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EAp,i·T是主要DID估計量,同時反映了i公司所在p地生態問責系列變量以及被問責的時間T。T是基于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分別進駐各省區市的時間啞變量,被問責之后的時期T取值為1,否則為0。
具體而言,為了驗證假設H1,在基本模型基礎上構建了如下的檢測模型(2):
模型(2)中定義EcoAccpi·T為是否接受生態問責,當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在t期入駐i企業所在地區p并開展督查并接收環境問題舉報時,則當期及以后年度EcoAccpi·T為1,否則為0。控制的其他宏觀變量和企業特征變量為:Pollu為p地區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為了減少內生性與經濟效應滯后性對數據進行滯后一期處理;Deficit為地區財政赤字變量,地方赤字越大則能夠提供給公司的政府補助資源越少,定義為(財政支出-財政收入)/該地區當期GDP。Size為公司規模,定義為公司總資產取對數;Long為長期資本收益率,定義為(凈利潤+所得稅費用+財務費用)/長期資本額;Capital為資本積累率,定義為(所有者權益合計本期期末值-所有者權益合計本期期初值)/所有者權益合計本期期初值);BIr為營業收入增長率;Sustain為可持續增長率,定義為凈資產收益率·收益留存率/(1-凈資產收益率·收益留存率);FA為固定資產占比;IA為無形資產占比;LEV為財務杠桿。
為了進一步檢驗假設H2,在模型(2)的基礎上將生態問責分政治壓力與環境規制執法力度進行檢驗,構建模型(3)如下:
EAs表示生態問責細分指標集合,其中包括政治壓力EAnum為被問責官員數量,由i企業所在地區p被問責總人數取對數;EApunish為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入駐到反饋結果期間的立案處罰案件數,由i企業所在地區p環保督察期間立案處罰數取對數。
在考慮政府補助細分性質后構建模型(4)對H3進行檢驗,具體采用兩種劃分方式:一是借鑒步丹璐和王曉艷[40]將政府補助按照約束性強弱手工整理為硬約束類(Hard,指國家制訂了法律法規明確補助條件、補助目的的政府補助)和軟約束類(Soft,約束性較弱的補助,國家沒有明確補助條件與補助目的);二是依據上市公司年度報表附注中披露的政府補助項目明細、發放原因、發放主體判斷補助目的,將用于環保、減排、節能、清潔生產、能源再生、生態修復、技術改造等相關的政府補助進行手工整理劃分為環保創新類(GT),其余劃分為其他用途補助(Other)。SUBs表示以上政府補助分類變量集合,如下:
2.2?研究樣本與數據
采用2015—2018年4期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并依據證監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結果與生態環境部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名錄綜合考慮剔除文化傳媒、服務業、金融業等,得到會產生污染的行業樣本,剔除數據缺失值后追蹤樣本為9 035個,樣本分布在除香港、澳門、臺灣以外的31個省區市。時間窗口選擇2015—2018年的原因在于我國自2015年起開始逐步搭建生態問責法治框架,中央環保督查組陸續進駐各省區市,于2018年年初結束31個省區市首輪巡視并反饋結果。涉及的公司財務報表數據以及非財務數據由CSMAR數據庫、RESSET數據庫收集。生態問責相關數據由生態環境部網站收集手工整理。相關區域經濟數據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整理收集,相關環境數據通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整理收集。
3?實證檢驗分析
3.1?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檢驗
首先依據生態問責中各省區市所受的政治壓力與環境規制執法力度繪制政府補助趨勢圖。如圖1所示,上半圖中生態問責后被問責官員數量越多,即政治壓力越大的地區,所發放的政府補助均值越低;下半圖中生態問責后被立案處罰數越多,即環境規制執法力度越大的地區,所發放的政府補助均值越低。生態問責后政府補助均值線性趨勢隨著政治壓力與環境規制執法力度的增大而降低。
根據地區在一個時期是否受到生態問責,表1中的Panel A將地區內的公司分為被問責區組和未被問責區組進行組間差異檢驗。結果顯示均值檢驗中未被問責當期省區市公司的政府補助(Subsidy)高于受到生態問責當期省區市的公司,均值在5%的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Panel B列出了生態問責相關指標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均值均略高于中位數樣本輕微右偏,并且被問責人數最多的省區市有1 613人,而最少的只有40人,可見各省區市受到的生態問責壓力差距較大。此外,在Pearson相關分析中當地是否受到生態問責(EcoAcc)與企業當期獲得的政府補助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版面所限此處相關系數分析結果不予列示。以上結果初步判斷被問責區組的政商關系弱于未被問責區組,但仍然存在眾多可能的影響因素,需要在回歸分析中進一步討論。
3.2?基本分析
3.2.1?生態問責對政商關系的主要影響
根據H1的基本假設,按照模型(1)設定對政府補助和生態問責進行了面板數據多期雙重差分的固定效應模型檢驗,表2中Panel A第(1)列列示了具體檢驗結果。變量EcoAcc·T的系數-0.102在1%水平顯著,即地區受到中央巡視生態問責的影響后當地公司獲得的政府補助會減少,表明政商關系一定程度上被生態問責所削弱。地方政府在中央環保督察組巡視后,總體上在給予企業補貼政策時表現得更加謹慎,如果地方存在不合理補助則意味著生態問責能夠對當地政企合謀傾向起到抑制作用。
3.2.2?生態問責中政治壓力與環境規制的效力差異
對生態問責細分特征的進一步檢驗結果如表2中Panel B所示。第(2)列列示了生態問責中的政治壓力影響,被問責官員數量EAnum·T的系數為-0.019,在1%水平顯著,表明中央生態問責給地方帶來的政治壓力越強,企業得到的財政補貼越少。第(3)列則列示了生態問責規制強度對政府補助影響的回歸結果,立案處罰數EApunish·T的系數為-0.014在1%水平顯著,表明中央環保督察組入駐期間對環保問題的執法力度與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在生態問責下對生態問題的處罰力度越強,對環保要求越嚴格的地區,越不容易產生政企間的環保政策套利。比較發現,政治壓力對政府補助的影響較強于環境規制的影響,支持了H2假設,表明適當輔以政治壓力更有助于讓地方政府推行環保措施。
3.2.3?不同性質類別政府補助影響研究
對政府補助進行分類檢驗后結果如表2中Panel C所示。從補助約束性強弱的劃分來看,第(4)列結果表明生態問責對硬約束類補助(Hard)并沒有顯著影響,而第(5)列EcoAcc·T系數為-0.124在1%的水平顯著,即在受到生態問責影響后的地區企業獲得的軟性政府補助(Soft)顯著減少,說明地方政府在接受中央環保督察組巡視后對自身的任意性行為進行了約束,支持了H3a假設。Panel C還列示了生態問責對政府補助中不同用途的環保創新類補助(GT)與其他補助(Other)的影響檢驗結果。第(6)列結果表明用于支持環保創新的政府補助并沒有發生顯著改變,第(7)列EcoAcc·T系數為-0.141通過了1%的顯著水平檢驗,即其他用途的政府補助顯著減少。結果沒有支持H3b假設,地方政府在生態問責后對其他類型的企業財政補貼發放更加謹慎,但并沒有顯著增加也沒有顯著減少對環保創新發展的扶持,在總體更少發放補助的情況下還是保持住了對企業環保創新發展的補貼。
3.3?穩健性檢驗
3.3.1?考慮地區與個體樣本選擇偏差:地區環境質量與公司研發基礎
地區受到的問責處罰壓力大也可能是由于該地區原本環境質量就差,因此樣本的初始值可能存在偏差。為了消除各省區市環境質量差異帶來的影響,引入地區空氣污染Air(煙、粉塵排放量/t)與廢水量Water(廢水排放總量/萬t)來控制各地區的環境質量基礎,相關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由于當期問責處罰取決于過去的環境表現,因此將污染數據進行滯后一期處理。表3第(1)(2)列結果顯示,在分別控制了地區環境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后,EcoAcc·T檢驗系數依然顯著,地區環境質量偏差并不影響生態問責對政府補助的影響。
此外,現有研究集中于驗證政府補助促進企業創新 [24],或通過緩解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等作用以實現創新可持續性[47],卻忽略了企業自身追求創新的積極程度與潛力同樣會影響政府補助的獲得。在生態問責的背景下,政府亟須調整產業戰略,重污染與落后產能企業面臨巨大壓力亟須轉型,這意味著積極進行技術升級的企業更容易獲得財政補貼支持。因此設定企業研發投入金額取對數為Create變量進一步控制公司個體不同研發基礎產生的影響。表3第(3)列結果顯示有著良好研發基礎的公司的確能夠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但控制公司研發基礎后生態問責效力的實證結果依然穩健。
3.3.2?基于生態問責數據期間的擴展檢驗
我國自2015年開始逐步建立生態問責法治體系,但直至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組才得以成立并首次進駐河北省(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2月4日對河北省開展了環境保護督察,并形成督察反饋意見),實質巡視督查主要集中在2016年之后。因此河北省的被問責時間也可以選擇2016年作為起點,為保證結果穩健,以2016年后開始標記為不同時期被問責省份,2016年之前都標記為未被問責地區,進行檢驗后實證結果見表4第(1)列,結論依然存在。為避免因年度數據較短和樣本缺失帶來的偏差,自2015年向前補充1年至2014年和向前補充2年至2013年進行檢驗,結果分別列示在表4第(2)列和第(3)列,實證結果依然存在。
3.3.3?對稅收返還與減免的考慮
雖然上文采用政府補助來反映政商關系,但企業的稅收政策依然能夠體現一定的政企聯系,以往也有學者在研究政府補助時對部分稅收返還進行了考慮[21]。因此在綜合了稅收返還與減免后對政府補助進行了調整形成變量Subsidy_T,如表4第(4)列所示,EcoAcc·T檢驗系數為-0.105,在1%的水平顯著,表明實證結果依然存在。
3.3.4?關于政府補助變量的替換檢驗
借鑒方穎和郭俊杰[48]的研究,在反映政商關系時使用政府補助與營業收入的比值取對數形成變量Subsidy_re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第(5)列,EcoAcc·T檢驗系數為-0.125,在1%的水平顯著,結論依然穩健。
3.3.5?對政治壓力指標不同度量方法的檢驗
在中央環保督察組進行巡視的過程中,先進行官員的約談,而后對部分官員進行問責。因此除了以被問責人數衡量中央督察組巡視施加的政治壓力,還可以約談人數進行替代解釋,實證結果依然存在。EAsummon為被約談官員數量,由地區p被約談總人數取對數,約談官員數EAsummon 描述統計已列示在表1Planel B中。表4第(6)列結果顯示EAsummon·T回歸系數為-0.016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雖然約談對于官員的政治壓力不如直接問責大,但依然略強于環境規制的作用。
3.4?進一步分析
3.4.1?政治聯系的源生基礎:產權背景
根據以往的文獻,民營、國有企業的政治關聯對企業所獲得的政府補助影響顯著不同[28]。在考慮政治壓力和違規成本時,企業不同的產權性質決定了不同政商關系的天然基礎,其面對財政補貼時則具備不同的待遇與抗風險能力。我們將樣本按照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為兩組,進一步研究初始政治聯系不同的企業在生態問責下受到的影響差異。如表5所示,第(1)列至第(3)列的國有企業組均不顯著,表明生態問責并不會使其政府補助顯著減少;若進一步將企業產權性質中的國有企業分為央企和地方國企,結果并無顯著變化,此處檢驗結果不進行列示。而非國有企業組生態問責相關變量均顯著負相關,EcoAcc·T系數為-0.103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EAnum·T變量系數為-0.019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EApunish·T系數為-0.013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非國有企業在地區受到生態問責期間得到的政府補助顯著下降。由此可見,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具有天然政治基礎,同時主要為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企業,大多能夠得到優先保障與扶持,能夠抵御生態問責對政商關系的沖擊,不會顯著影響所享受的補助政策。
3.4.2?主動建立政治聯系:高管政治背景
除了企業自身產權性質有所影響外,企業也可選擇聘用具備政治聯系的高管以增強政商關系。因此為了進一步驗證高管政治背景是否可能會對生態問責效力產生影響,設定高管政治背景Poli變量,并加入高管政治背景與生態問責變量的交乘項構成多期三重差分模型,詳見模型(5)。Poli變量定義為公司高管曾任或現任政府官員或黨員干部則取1,否則取0,高管當期建立的政治聯系很可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為公司財政補貼帶來好處,因此選擇滯后一期的政治背景數據。具體回歸結果見表6 。
由表6第(1)列可見,在沒有聘用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公司(Poli=0),生態問責與政府補助的回歸系數為-0.084,該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聘請了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公司(Poli=1)與沒有聘請的公司斜率差異為-0.091,即交叉變量EcoAcc_Poli的回歸系數,并且通過了10%水平顯著性檢驗。對聘請了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公司(Poli=1)在地方被生態問責以后(EcoAcc=1)其回歸系數為-0.175(-0.084-0.091)。這說明在生態問責下聘請了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公司獲得的政府補助反而降低更多。同理細分到政治壓力與執法強度上,表6第(2)列和第(3)列交叉變量EAnum_Poli、EApunish_Poli回歸系數也在10%水平顯著,也說明聘請了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公司面對生態問責下的高政治壓力和執法強度,獲得的政府補助相比于沒有聘請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公司減少的更多。以上結果表明,企業通過建立政治聯系而獲得的財政補貼在生態問責中更容易失去,這也提供了政商關系在生態問責中被削弱的經驗證據。
3.4.3?企業議價與談判能力:地方財稅依賴度
地方政府競爭的道路選擇在生態文明建設下面臨多重博弈。生態問責中的政治壓力使得地方政府需要與企業保持距離并嚴格執法,但官員政績競爭使得政府對大型企業尤為倚重。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干預企業的政府補助時也必然受制于地方財政狀況[28]。大企業能夠更好地貢獻地方財政收入、解決就業問題,從而需要主動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并給予政策支持為企業提供發展空間。因此利用公司繳納的所得稅費用/當地GDP衡量地方政府對公司的財政依賴度,并將樣本劃分為高依賴組和低依賴組進行調節作用檢驗。如果財政依賴度超過樣本年度中位數則定義為高財政依賴,否則定義為低財政依賴。具體結果見表7。
從公司對當地財政的貢獻上看,低依賴組的政府補助與EcoAcc·T、EAnum·T、EApunish·T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高依賴組除去政治壓力(EAnum)外其他結果并不顯著,表明低財政貢獻的企業會受到生態問責對政商關系的影響,而納稅大戶形成的政企財政聯系在生態問責中能夠避免被削弱。高依賴組EAnum·T系數為-0.016在5%水平顯著,表明在面對中央政治壓力時企業的地方財政貢獻度高并不能抵消生態問責的影響。
3.4.4?地區污染治理投資結構的影響
政府補助資源配置的優劣取決于當地政府的投資能力,理論上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越高、投資結構越好的地區企業獲得更多政府補助的可能越大。如果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不足則說明該地的環保投資結構不合理,地方政府也可能會為了多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項目而擠占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為此,需要檢驗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結構對生態問責與政府補助關系的調節作用,設定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與地方GDP的比值取對數表示地區污染治理投資結構,如果高于年度地區中位數則認為具備好的污染治理投資結構,否則為非優污染治理投資結構。具體回歸結果見表8。在污染治理投資結構好的地區,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在生態問責之后并沒有顯著變化;在污染治理投資結構非優的地區政府補助與EcoAcc·T、EAnum·T、EApunish·T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生態問責使得污染治理投資結構較為不好的地區對地方政府資源配置做出了調整,其政商關系在生態問責之后受到顯著影響。
4?研究結論與啟示
生態問責制度在黨的十八大后得到系統性建設,在中央環保督查首輪巡視中大量違規企業受到處罰與關停,大量官員被問責,生態問責嵌入了嚴厲的政治壓力,不可避免地影響地方政商關系。以2015—2018年中央環保督察組設立并陸續進駐各省區市之后的年度為研究期間,將生態問責相關變量作為研究對象,檢驗其對企業以獲得政府補助為代表的政商關系的影響,可融合探索行政問責與環境規制的影響效應。以往的問責文獻主要關注宏觀的行政問責制度路徑設計或政府責任審計[49-50],而環境規制文獻則分別討論企業創新[51]、績效[52]、環保投資[53]、違法成本[54]以及外部約束[55]等變量。近年來生態問責開始引起各界關注,但只有少數研究對生態問責進行了制度討論[56]。區別于以往研究,上文除了檢驗生態問責總體影響,還同時比較討論了環保督查中政治壓力與執法強度的影響,具體研究結果如下。
(1) 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后,當地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顯著減少,這意味著生態問責會削弱地方以往建立的政商關系,地方政府在發放政府補助時會更加謹慎。在生態問責的細分特征上,生態問責為地方政府帶來的政治壓力對企業獲得政府補助的影響要強于生態問責中環保執法強度的影響。而具體到政府補助的細分性質,生態問責會使地方政府發放的軟約束類的補助顯著減少,對硬約束類的補助沒有顯著影響;同時對減少除環保創新用途以外的補助作用顯著。表明生態問責并非絕對地抑制財政補貼、削弱政商關系,而是僅減少軟約束補助的任意發放,并沒有降低對企業環保創新的扶持。給出了我國政治體系能夠自我約束、改善治理能力的新證據。
(2) 企業政治聯系中由產權性質帶來的源生政治基礎會影響生態問責效力,國有企業能夠避免生態問責對政府補助的影響,而非國有企業則不能。企業在生態問責中更容易失去因聘用具備政治背景的高管而建立政治聯系所獲得的財政補貼。
(3) 地方政府對企業的財稅依賴度高,企業便能抵消生態問責對政商關系的削弱,而財稅貢獻小的企業則不能,但在政治壓力下企業的高財稅貢獻并不能完全避免生態問責影響。
(4) 地區污染治理投資結構的好壞也影響著生態問責對政商關系的作用,對污染治理投資結構相對非優的地區政商關系受到影響較大,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顯著減少,對政府資源的調整能夠緩解工業污染治理投資被擠占的現象,體現了生態問責提升政府補助使用效率,矯正地方資源配置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投資能力。
研究的政策建議與現實意義是:①近年來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與生態問責制度的完善實施密切相關。問責中政治壓力的效力大于環境規制執法強度,表明環保政策由上到下的實施需要對地方政府施以必要的政治壓力才能提高政策執行效率,這也符合Fahlquist[6]責任歸于政府提升效率的研究觀點。地方政府在經歷生態問責后審批發放政府補助時會更加謹慎,有利于減少不合理政府補助,避免政企合謀,并不斷優化自身的污染治理投資結構,提升投資能力。②國有企業與聘請具有政治背景高管的企業要完善自我監管,避免政治聯系濫用。③企業要積極研發創新,努力減少對生態環境產生的負外部性,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避免受到政治不穩定而帶來的風險,更避免因污染與產能落后淘汰而失利。④通過生態問責對政府補助影響的研究,探索了生態問責微觀落實的基礎。追責官員、處罰企業為已產生的嚴重污染付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生態問責更核心的作用在于推進國家宏觀制度與企業微觀運作的連接,從而規范未來政府與企業的行為。生態問責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制度探索,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流向,引導未來企業發展方向,使政治治理與環境治理耦合從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
(編輯:李?琪)
參考文獻
[1]梁平漢, 高楠. 人事變更、法制環境和地方環境污染[J]. 管理世界, 2014(6): 65-78.
[2]袁凱華, 李后建. 政企合謀下的策略減排困境——來自工業廢氣層面的度量考察[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 25(1): 134-141.
[3]聶輝華, 李金波. 政企合謀與經濟發展[J]. 經濟學(季刊), 2007, 6(1): 75-90.
[4]LOPEZ R, MITRA S. Corruption, pollution, and the Kuznets Environment Curv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0, 40(2): 137-150.
[5]LO K. How authoritarian is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5,54: 152-159.
[6]FAHLQUIST J N.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al?[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9, 22(2): 109-124.
[7]LIU L, ZHANG B, BI J. Reforming China's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11th Five-year Pla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2 ,21: 106-111.
[8]LY H,MA Z M,ZHANG L W. Redlines for the greening of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3,33: 346-353.
[9]傅強, 馬青, BAYANJARGAL S. 地方政府競爭與環境規制:基于區域開放的異質性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 26(3): 69-75.
[10]NUTLEY S, LEVITT R, SOLESBURY W, et al. Scrutinizing performance: how assessors reach judgements about public servic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2, 90(4): 869-885.
[11]STROM K. 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0, 37(3): 261-289.
[12]FOX J, SHOTTS K W. Delegates or trustees? a theory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9, 71(4): 1225-1237.
[13]ROMZEK B S, DUBNICK M J.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7, 47(3): 227-238.
[14]MULGAN R. ‘Accountability: an ever-expanding concep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 78: 555-573.
[15]解冰, 康均心. 反腐敗刑事制度的科學構建[J]. 管理世界, 2011(3): 170-171.
[16]陳勝藍, 馬慧. 反腐敗與審計定價[J]. 會計研究, 2018 (6): 12-18.
[17]萬廣華, 吳一平. 制度建設與反腐敗成效:基于跨期腐敗程度變化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4): 60-69.
[18]SINDEN A. In defense of absolutes: combating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nvironmental law[J]. Iowa law review, 2005, 90(4): 1405-1511.
[19]DAMANIA R, FREDRIKSSON P G, LIST J A. Trade liberalization, corru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form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6(3): 490-512.
[20]侯方宇, 楊瑞龍. 新型政商關系、產業政策與投資“潮涌現象”治理[J]. 中國工業經濟, 2018(5): 63-80.
[21]余明桂, 回雅甫, 潘紅波. 政治聯系、尋租與地方政府財政補貼有效性[J]. 經濟研究, 2010(3): 65-77.
[22]步丹璐, 張晨宇, 王曉艷. 補助初衷與配置效率[J]. 會計研究, 2019(7): 68-74.
[23]饒靜, 萬良勇. 政府補助、異質性與僵尸企業形成——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會計研究, 2018(3): 3-11.
[24]蘇昕, 周升師. 雙重環境規制、政府補助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及調節[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9, 29(3): 33-41.
[25]王克敏, 劉靜, 李曉溪. 產業政策、政府支持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3): 113-124, 145.
[26]王克敏, 楊國超, 劉靜, 等. IPO資源爭奪、政府補助與公司業績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9): 147-157.
[27]HELLMAN J S, JONES G, KAUFMANN D.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3, 31(4): 751-773.
[28]潘越, 戴亦一, 李財喜. 政治關聯與財務困境公司的政府補助——來自中國ST公司的經驗證據[J]. 南開管理評論, 2009, 12(5): 6-17.
[29]BENHABIB J, PRZEWORSKI A. Economic growth under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0, 6(1): 77-95.
[30]ECKARDT S.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fiscal condi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cross-section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28(1): 1-17.
[31]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張峰. 生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階段的發展[J]. 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2(5): 97-104.
[32]劉偉. 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結合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J]. 經濟研究, 2016(5): 4-13.
[33]張凌云, 齊曄, 毛顯強, 等. 從量考到質考:政府環保考核轉型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8, 28(10): 108-114.
[34]BANSAL P, ROTH K. Why companies go green: a model of ecological responsive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4): 717-736.
[35]GRAY R, BEBBINGTON J.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managerialism and sustainability : is the planet safe in the hands of business and accounting?[J].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2000(1): 1-44.
[36]DEY P K, PETRIDIS N E, PETRIDIS K, et 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195: 687-702.
[37]XU C.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4): 1076-1151.
[38]周黎安. 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 經濟研究, 2007(7): 36-50.
[39]步丹璐, 黃杰. 企業尋租與政府的利益輸送——基于京東的案例分析[J]. 中國工業經濟, 2013(6): 135-147.
[40]步丹璐, 王曉艷. 政府補助、軟約束與薪酬差距[J]. 南開管理評論, 2014, 17(2): 23-33.
[41]倪星, 王銳. 權責分立與基層避責:一種理論解釋[J]. 中國社會科學, 2018, 269(5): 117-136,207-208.
[42]金宇超, 靳慶魯, 宣揚. “不作為”或“急于表現”:企業投資中的政治動機[J]. 經濟研究, 2016(10): 126-139.
[43]CHEN Y, JIN G Z , KUMAR N, et al. The promise of Beijing: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2008 olympic games on air qualit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3, 66(3): 424-443.
[44]GHANEM D, ZHANG J. ‘Effortless perfection : do Chinese cities manipulate air pollution dat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4, 68(2): 203-225.
[45]沈洪濤, 周艷坤. 環境執法監督與企業環境績效:來自環保約談的準自然實驗證據[J]. 南開管理評論, 2017, 20(6): 73-82.
[46]BECK T, LEVKOV R L.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1637-1667.
[47]李健, 楊蓓蓓, 潘鎮. 政府補助、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創新可持續性[J]. 中國軟科學, 2016(6): 180-192.
[48]方穎, 郭俊杰. 中國環境信息披露政策是否有效:基于資本市場反應的研究[J]. 經濟研究, 2018, 53(10): 160-176.
[49]李兆東. 環境機會主義、問責需求和環境審計[J]. 審計與經濟研究, 2015, 30(2): 33-42.
[50]馬志娟, 韋小泉. 生態文明背景下政府環境責任審計與問責路徑研究[J]. 審計研究, 2014(6): 16-22.
[51]JAFFE A B, PALMER 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97, 79(4): 610-619.
[52]CLARKSON P M, RICHARDSON G D. The market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capital expenditures by pulp and paper companies[J]. Accounting review, 2004, 79(2): 329-353.
[53]唐國平, 李龍會, 吳德軍. 環境管制、行業屬性與企業環保投資[J]. 會計研究, 2013(6): 83-89.
[54]龍小寧, 萬威. 環境規制、企業利潤率與合規成本規模異質性[J]. 中國工業經濟, 2017(6): 155-174.
[55]馬紅, 侯貴生. 環保投入、融資約束與企業技術創新——基于長短期異質性影響的研究視角[J]. 證券市場導報, 2018(8): 14-21.
[56]余敏江. 論生態治理中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利益協調[J]. 社會科學, 2011(9): 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