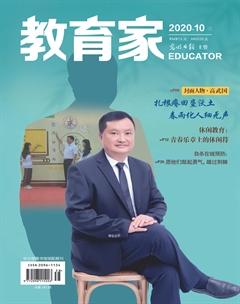自殺在線預防:愿他們鼓起勇氣,踏過荊棘
王夢茜


近年來,自殺越來越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公共衛生問題。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每年有超過80萬人死于自殺,而每例自殺死亡背后有超過20次的自殺嘗試。自殺是15~29歲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而自殺是可以預防的,2020年世界預防自殺日的主題是“共同努力,預防自殺”。作為一名自殺預防的實踐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朱廷劭和他的團隊,正在進行自殺在線預防模式的探索,他們通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在微博上主動尋找自殺傾向人群,向他們傳達幫助與支持。
在網上發表自殺言論,不只是說說而已
2012年3月18號,有一位叫“走飯”的微博用戶發表了一條微博:“我有抑郁癥,所以就去死一死,沒有什么重要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第二天,這名90后女大學生被證實已自殺死亡。在她的最后一條微博下已有超過一百萬條評論,并且每個月還在增加,這里儼然成了心理危機者的“樹洞”。朱廷劭團隊初期的研究就是從對這條微博留言內容的文本分析開始的。“雖然很多自殺行為的實施非常突然,但在那之前,我們其實可以捕捉到很多信號。”
2013年,朱廷劭開始做網絡心理的研究,主要是通過用戶的網絡行為去了解他們的心理特征和心理變化,包括潛在的自殺行為和自殺風險。有的人認為,在網上講自殺的人,只是為了博取別人的關注,并不會真的采取行為。朱廷劭通過研究發現,其實并不是這樣。“在網絡上表達自殺意念的人,有一半以上,真的會去嘗試自殺。這就提醒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的每一條跟自殺有關的表達,背后有可能就是一個自殺死亡的真實案例。”
“目前自殺干預的主要困境是主動求助率很低。但其實很多人選擇自殺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求助。”據朱廷劭統計,只有約20%的人明確表示不愿意接受干預,剩下80%的人則是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邁出主動求助的那一步,如不想麻煩他人、對獲得幫助沒信心、顧慮他人看法、不知道從何獲得幫助、擔心費用等。“有些人會產生病恥感,擔心別人看輕他們,尤其像之前網上有人宣告自殺卻遭受網絡暴力……公眾對自殺的污名化態度,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自殺者的求助意愿。”
在這種情況下,朱廷劭希望能夠去幫助這群人。他發現,在自殺人群中年輕人占首位,同時他們也是互聯網用戶的主力軍,這兩大人群有非常大的重合。這令他萌生了一個想法:或許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主動找到那些有自殺傾向的人,并向他們提供幫助。
借助人工智能,讓自殺預防從被動變主動
每天約有數千條微博在釋放自殺信號,如何找到網線那端或許已在絕望邊緣徘徊的人?
朱廷劭做了一個極端情況下的研究——將已確認自殺死亡的微博用戶數據與一般用戶進行比較。他發現,前者的微博互動更少,更加關注自我,有很多負性消極的表達,并且在夜間更加活躍;表述內容中與死亡相關的詞更多一些,與工作相關的詞更少一些;表述方式上會更加頻繁地使用序列、連接、解釋、詳述等修辭關系……這說明,自殺死亡用戶和一般用戶在網絡表達內容和方式上都有區別,通過計算機找到有自殺意念人群的方法是有可行性的。
基于上述區別特征,朱廷劭團隊做了一個自殺在線主動預防模型。首先利用網絡爬蟲自動下載網上的微博內容,作為原始數據;其次利用機器學習的模型,即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對每一條微博給出一個預測標注,自動去標注這條微博是否有自殺意念,并按嚴重程度劃分為有自殺意念、有自殺計劃、有自殺嘗試三個等級;計算機完成初篩后,會由志愿者做第二輪人工的核查,確認這條微博確實有自殺意念后,再做出干預行為。朱廷劭強調,自殺死亡用戶與一般用戶的表現差異不能單獨拎出來一條就當作是自殺高風險的標記物,判斷是否有自殺風險需要綜合多種因素。于是,他們利用多種機器學習算法優化這一模型,不斷提升機器學習的性能,提取更多特征,加入新的語料,從而提高識別的精度(目前,這一預測模型精度可達到80%)。在微博平臺識別出有自殺意念人群后,他們會主動發送私信,提供幫助信息。
“‘主動是在線自殺預防的核心意義。”朱廷劭強調。過往的自殺預防較為被動,以自殺預防熱線為例,只能等待求助者打電話過去,如果對方不主動打電話,干預就無法實施,而現實中有自殺意念人群的主動求助率并不高。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在自殺預防中能夠快速處理大量信息,并及時做出反饋。這一方面使干預方能夠主動找到被干預對象,另一方面也讓干預盡量前置,當人們剛剛產生與自殺有關的意念或情緒波動時就介入干預。
“你拍拍我的肩膀,讓我挺起胸膛”
在線自殺預防工作正式開始前,朱廷劭認為需要明確有自殺意念人群最真實的需求——他們最需要什么樣的支持?什么信息對他們而言比較重要?什么樣的方式能夠幫助到他們?2016年暑假期間,朱廷劭及其團隊邀請了兩批有過自殺意念的用戶,做了兩次焦點小組訪談。2016年11月,他們開展了一個更大規模的用戶實驗,分兩次向4222名微博用戶發送了私信。這4222名用戶,是他們在半年期間,用人工方法確認發表過有自殺意念微博的用戶。
一開始,朱廷劭非常忐忑,所幸反饋結果比較正向,700多人表示愿意參與實驗,300多人直接回復了私信。有人說:“謝謝您,你是第一個這么問我的人。”也有人說:“謝謝在我深陷泥潭之時拉我一把。”……根據實驗反饋,有自殺意念的人最需要的幫助,一是想知道自己該怎么辦,需要一些應對心理危機的具體可行的建議,二是想了解自己現在到底怎么樣,需要有更科學的心理測評來明確自己的現狀。基于這些內容,朱廷劭對私信做了進一步的改進:“第一會交代我們從哪兒來、干什么,是在哪看到其信息的,同時后面會附上三種干預資源——科學的心理測評量表、全國自殺干預熱線匯總以及在線值班的志愿者。在線值班時間寫的是晚上6點到10點,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會一直工作到深夜12點。”
在這些基礎上,朱廷劭團隊正式啟動在線自殺預防工作,2017年4月開始對系統進行測試部署,2017年7月正式上線值班。這一系統到目前為止還一直在運行。目前,他們的私信設置是最多發五次,每一次都會在內容上稍做變化。“我們希望通過多次私信溝通,傳達出我們沒有放棄的訊息,希望他們也不要放棄。不管通過什么方式,只要能夠激活他們跟外界交流的意念,跟外界保持溝通,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好的起點。”
朱廷劭提及一位微博用戶,“前兩次私信他都沒有回復,第三次他回復了,認為我們是真的想幫他。后來他一邊接受心理咨詢,一邊學習如何做咨詢,現在已經走出了自己的困境,并開始幫助別人。”
許多人在自殺前會經歷一個漫長、復雜的心理活動過程,在生與死的抉擇前徘徊許久。在這個過程中,若他們及時接受干預,感受到社會力量的支持,或許能夠鼓起勇氣,挺過那一關。有一名網友這樣評論朱廷劭及其團隊所做的在線自殺預防工作:“你拍拍我的肩膀,讓我挺起胸膛。”而朱廷劭坦言:“我們無法杜絕自殺,也解決不了所有人的問題。幾乎沒有任何人會活得好好的,突然想跳樓自殺。他們肯定遭遇了一些常人難以想象的困境。我們力所能及的就是向那些有自殺意念的人提供一種新的思路或方法,讓他們重新去看待自己的問題,用科學的方法去面對,或許會有好的結果。”
自殺預防,不是只靠心理學就可以解決
近年來,青少年自殺事件屢見報端,引發社會熱議。前段時間,朱廷劭對有自殺意愿的微博用戶數據做了一個統計分析,從中也發現有自殺意愿的人群低齡化傾向很嚴重。在他們的樣本中,高中生較多,初中生也有,甚至還有小學生。其中有一半人從來沒有向他人求助過,在有求助經驗的人中,對家人求助的概率甚至低于陌生網友。
“很多時候孩子跟父母的關系反而成為他們自殺的一個動因。”朱廷劭認為,在自殺預防過程中,家長需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讓孩子感受到愛和支持,而不是指責、誤解和忽視。他建議家長先傾聽孩子的想法,了解孩子所面臨的問題,然后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讓孩子獲得解決問題的勇氣和方法。“有的時候,很多孩子其實并沒有意識到自殺的行為會帶來自殺的后果,他們可能是為了逃避或者發泄,就走了極端。若能提前發現苗頭,在早期提供一些專業的建議,去幫助他們克服問題,激發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可能比單純的自殺干預更好一些。”
“自殺往往是各類社會問題的最終表現形式。”朱廷劭呼吁人們關注自殺的根源,而不是自殺這一行為本身。他告訴記者,與國外90%自殺是長期精神疾病導致的情況不同,在中國這個比例可能不到一半,也就是說接近一半的自殺者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他們可能因為學習、工作、婚戀、經濟等各個方面的問題而自殺。朱廷劭曾考慮過與一些社工組織合作,他們負責線上,社工組織負責線下。但他坦言,這種體系的建設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針對自殺的干預,也不是只靠心理學就可以解決的。在我國,自殺預防工作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政府和社會方方面面的理解與重視。”
志愿者的話
劉明明:我們雖然不能保證把那些有自殺意愿的人徹底拉回來,但是也經歷過許多次,當他們在死亡邊緣搖擺的時候,幫他們往生的方向推了一把。
李婷:學習心理學已經有6年了,這可以說是第一次接觸高危人群。他們像受了傷的小駱駝,雖然脆弱,但也拼命抓住韁繩,愿意相信我們,在心理學方法的指導下去努力生活。
申兆慧:他們有很多痛苦是正常人想象不到的,我們需要針對每位用戶的情況多加了解,給予他們關心與幫助。
王堃:抑郁、焦慮、自殺,其實就在我們身邊。每個人都可以被溫柔以待,每顆心都可以感受到溫暖。
丁曉南:在交流的過程當中,很多人充滿了防備與敵意,但是我們的工作也讓很多人感受到被看見、被關注、被傾聽。
李季:我們每一周的約定、每一次聊天,都可以成為讓他們留下來的一絲希望。
丁瑞峰:每當有人因為我們的存在而點燃一線內心的希望,都感覺內心無比安慰。希望我們的存在,能夠為更多暫時失去方向的人,帶去希望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