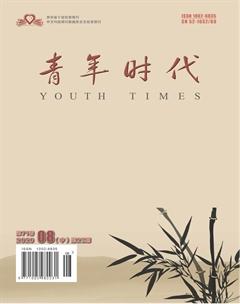行政訴訟調解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思考
摘 要: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行政訴訟領域立案制度的改革,大量新型行政案件涌入法院。以往較為單一的行政糾紛解決方式難以適應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現實需求,探索新的行政糾紛解決方式勢在必行。在和諧社會背景下,行政糾紛更多以協商的方式解決,這一點與行政訴訟調解不謀而合。因此,本文將從行政訴訟調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調解存在的問題及建議展開論述。
關鍵詞:行政訴訟調解;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行政訴訟;必要性;可行性
一、引言
行政訴訟調解,指在行政訴訟過程中,發生行政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和協調下,以行政法上的權利和義務為內容進行協商,達成和議而解決行政糾紛的活動。行政訴訟調解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調解是在行政訴訟程序中進行的;第二,調解以該被訴行政行為合法為前提;第三,行政訴訟調解堅持自愿原則;第四,調解是針對訴訟標的而言的。
對于行政糾紛是否適用調解這一問題,學界歷來存在爭論。我國立法基本采用傳統行政法理論中公權力不可處分原則,認為行政糾紛因涉及對行政權的處分而不適用調解。以往的行政法立法中以單獨條款明確了行政法不可以調解,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除了重申這一原則外,增加了行政賠償、行政補償以及行政自由裁量類案件作為例外規定。而現實中,法院以變通適用調解即“協調和解”方式解決行政糾紛的做法屢見不鮮。可見,《行政訴訟法》并非絕對不適用調解。而且,隨著新類型行政案件的增多,調解適用的案件種類也會越來越多,以往關于行政訴訟調解的理論就需要重新審視。
二、行政訴訟適用調解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一)行政訴訟適用調解的必然性
隨著社會發展,新類型的行政案件數量持續增加,加之2015年修訂的《行政訴訟法》進行立案制度改革,立案登記制的確立降低了行政案件的準入門檻,有限的司法資源很難在有限時間內處理眾多的新類型行政案件。所以,拓展新的行政糾紛解決方式對降低法院壓力和緩解社會矛盾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政府的職能也在發生轉變。政府不僅是以往的行政命令的發布者、監督者、管理者,而且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目前,群眾參與社會管理成為流行趨勢。政府和公民由過去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更多地轉變為“契約”或者是合作關系[1]。在這種社會治理模式下,選擇較為緩和的糾紛解決方式對行政管理和政策推行具有深遠意義。而行政訴訟調解作為一種妥協而非對抗性的糾紛解決方式,不會因為糾紛徹底破壞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
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原則與司法解釋中有限適用調解的規定存在矛盾。在行政糾紛處理中,行政訴訟案件以“協調和解”方式結案或者經法院勸說當事人撤訴的案件占比很大,這其實就是對行政訴訟調解的變通適用[2]。出于司法實踐的需要,我國應當重新審視行政訴訟調解并合理制定適用規則。
(二)行政訴訟調解的可行性
部分學者認為,行政訴訟不適合調解,這主要受公權力不可處分理論的影響。但行政行為種類眾多,越來越多的行政行為表現出自由裁量的特點,行政訴訟是否適用調解已經不能一概而論。判斷行政糾紛是否適用調解主要看該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行為主體是否具有處分權以及是否危害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如果行政糾紛中提到的行政行為不涉及合法性判斷,沒有超出處分權的范圍并且不會危害第三人,原則上是可以適用調解的。
三、行政訴訟調解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其一,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法律依據相對薄弱。盡管我國《行政訴訟法》在2015年已經列舉了適用行政訴訟調解的三種例外情形,但也重申了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這一原則。因此,從立法原則的角度看,很難將該條款作為行政訴訟調解制度有效建立的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發展緩慢,對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里的調解制度,更加凸顯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缺漏。雖然行政訴訟有其特殊性,但是并不能構成其不適用調解的理由。
其二,關于調解的適用范圍的列舉方法不合理。《行政訴訟法》中提到的適用調解的三種例外情形之間存在重合。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但是,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關于調解的適用范圍,該規定采用了行政行為理論類型和行政行為種類的雙重標準,而在行政賠償案件和行政補償案件中,行為主體亦有自由裁量權。但將所有自由裁量類案件包括在內也過于寬泛。
其三,行政訴訟調解制度會對行政訴訟制度造成沖擊的認識不合理。現代社會,行政糾紛涉及的領域更為寬廣,表現形式更為多元,以往較為單一的行政糾紛解決方式不再能適應司法實踐的需求。因此,近些年多提倡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但有學者擔心,行政訴訟調解是否會對行政訴訟制度造成沖擊,是否會降低法院的公信力。
四、完善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建議
(一)加強立法,完善行政訴訟調解的法律依據
如前文所述,出于現實的需要,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以“協調和解”為名的變相的調解制度,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據以及調解程序等相關制度保證,很難有良好的實施效果。理論發展總是為實踐發展服務的,既然行政訴訟調解是出于現實需要,以法定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就是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對行政訴訟調解適用范圍界定方法的建議
部分學者主張采用列舉的方式,但列舉方式功能有限且過于僵化,無論采用肯定式列舉還是否定式列舉都容易遺漏。適用調解的核心是自由裁量權,不如描述為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因裁量權幅度提起的訴訟。
(三)對于行政訴訟調解和行政訴訟之間關系的處理
第一,調解并非前置程序,是否適用調解取決于當事人的選擇。行政訴訟調解遵循自愿原則,調解的適用取決于糾紛雙方當事人的合意。行政訴訟調解是在行政訴訟程序下進行的,因此行政糾紛雙方當事人得以暫時擺脫行政關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作為原告和被告這樣的平等法律主體而進行協商。調解是以行政糾紛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妥協和讓步來完成的,其中典型的表現為行政機關為達成調解協議而讓渡其特殊地位,以解決事實上地位不平等的問題。因此,不必擔心調解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受威脅而被迫達成調解的情況。調解因在法院的主持下進行,更具權威性和正當性[3]。并且,調解的適用不會影響訴權的行使,如果調解失敗或者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協議,相對人仍然可以啟動訴訟程序。
第二,調解的適用范圍較小,僅適用于部分自由裁量類案件。在行政糾紛中,我國嚴格適用有限調解原則。因此,并非所有行政案件都適用調解,行政訴訟在解決行政糾紛中的主體地位不會受調解影響。調解可以在訴訟前或者訴訟中的任何一階段進行,調解可以是一審調解也可以是再審調解,貫穿行政訴訟程序始終。行政訴訟程序是一個獨立的程序,其主持法官和審判人員不同,適用的程序也就不同。
第三,因達成調解協議產生的證據,不能作為行政訴訟證據使用。經過調解程序,調解失敗又轉入訴訟程序的,調解過程中產生的對當事人不利的證據不能作為證據在行政訴訟程序中使用。為解決糾紛,在達成調解協議的過程中,當事人可能會作出妥協和讓步,這種讓步勢必會損害自己的利益,但其目的是達成調解協議獲得利益置換,如果調解失敗,這種妥協賴以存在的基礎已經不存在,繼續采用在此種情形下達成的內容,勢必會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五、結語
總之,行政訴訟調解對于拓寬行政糾紛解決方式以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加強對行政訴訟調解方面的理論研究符合司法實踐的發展需求,也符合和諧社會推行的需求。對于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無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司法實踐層面,國外都有先進經驗可借鑒。所以,我國未來在行政訴訟相關立法修改時,也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完善行政訴訟調解制度。
參考文獻:
[1]喻文光.行政訴訟調解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建構[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1):8.
[2]鄒榮,賈茵.論我國行政訴訟調解的正當性構建[J].行政法學研究,2012(2):26.
[3]梁秋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的行政調解研究[J].學術論壇,2015(2):148.
作者簡介:李閃閃(1992—),女,漢族,河南新鄉人,碩士,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