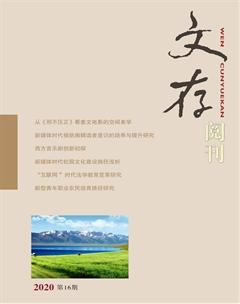俄漢語言中俄女性詞匯的對比
摘要:不論在俄語還是漢語中,都存在一些表示女性的名詞,俄語中以陰性名詞來代表女性,漢語中則使用“女”字旁來表示。俄漢兩種語言中代表女性的名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俄兩國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及中俄兩國對女性的看法。本文將以俄漢語中表示女性的詞匯、熟語等為例,簡要闡述女性在中俄兩國的地位的異同。
關鍵詞:俄漢對比;女性詞匯;陰性名詞;文化
俄漢語言中都有許多關于女性的詞匯或漢字,以俄語中的陰性名詞和漢語中的女字旁漢字為例,這些詞匯的日常使用及其衍生出來的熟語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俄兩國女性的社會地位,本文將通過對俄漢語中的女性詞匯以其衍生出來的一些熟語等日常用語的對比,淺析俄漢語言中女性詞匯的異同。
一、俄語中代表女性的詞匯,熟語及其意義
俄語通過名詞的詞尾來判斷陰性名詞和陽性名詞,陰性名詞代表女性,而陽性名詞則代表男性。除了一些表示客觀的性別的單詞,如:мама(媽媽;陰性)、 папа(爸爸;陽性)、 мужчина(男人;陽性)、 женьщина(女人;陰性)之外,還有一些表示職業、動物的名詞也區分為陰性和陽性兩種,如:表示職業的:учитель(教師;陽性)учительница(女教師;陰性); артист(男演員;陽性)-артистка(女演員;陰性); граф(伯爵;陽性)-графиня(女伯爵、伯爵夫人;陰性); коммунист(共產黨員;陽性)-коммунистка(女共產黨員;陰性);Студент(學生;陽性)-стутентка(女學生;陰性)等。可以見得,這些表示職業的陰性名詞最初是不存在的,它們是由陽性名詞派生出來的,無非是在這些表示職業的陽性名詞后面加上了-ка; -ня; -ница等后綴,就以此產生了表示女性的陰性名詞,由此可見,這些陰性名詞屬于從屬、次要的地位。在封建俄國,盛行著“上帝主宰世界,沙皇主宰國家,男人主宰家庭”的原則,家長對婦女,兒童和全家老少擁有不受限制的統治權,俄國婦女的對家長處于絕對服從的地位。父權制度不僅在經濟地位上貶低壓制婦女,還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婦女的社會角色范圍,并有意識的降低了對婦女知識、技能和職業的要求,同時在道德上對女人的要求比對男人更加苛刻。因此,上述的表示職業的陰性名詞是派生自陽性名詞的,由此可見,在社會上,陽性名詞也就是男性,占據著主導地位,而陰性名詞也就是女性,還是被視作男性的附屬品。
除此之外,語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俄羅斯女性的社會地位也可以從一些熟語中反映出來,如:Бабъя дорога-отпечи допорога(婆娘只在灶臺到門檻內重要). Курица-не птица,баба-не человек(母雞不是禽類,婆娘不是人). Коли муж не бьет-значит не любит(男人不打你,就是不愛你)。這些熟語充分體現了在俄羅斯女性地位的低下,且在這些熟語中,提到女人是所用的詞匯是баба,這個詞準確的翻譯過來是“婆娘”的意思,可以見得,是帶有一些貶義色彩的。在俄羅斯歷史發展長河中,女性一直被看作男人的“私有財產”,被當作實現經濟和政治野心的手段。除以上提到的熟語中的女性形象外,俄語中還存在一些詞是沒有陰性形式的,比如:бедокур(淘氣生事者)、бражник(游手好閑的人)、буян(尋釁鬧事者),這些詞沒有陰性名詞是因為,雖然俄羅斯女性地位低下,但是社會對女性的品德要求卻比對男人的要求要嚴苛,男人可以淘氣生事、游手好閑、尋釁鬧事,而女性卻不可以。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俄羅斯社會女性的地位是比較低下,且對女性的要求嚴格的。
除了以上提到過的熟語和一些沒有陰性名詞的現象外,俄語中的粗話也可以反映女性在俄羅斯的地位。俄語中常見的粗話多數都是陰性名詞,如:сука(母狗,婊子)、блядь(妓女,婊子)、скадина(畜生),這些粗話也多是陰性名詞。在一些表示動物的名詞中,如:狗(собака )、豬(свинья )、雞(курица )、鴨子(утка )等在俄語中也都是陰性名詞。俄羅斯女性的社會地位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俄語中的河流、祖國等詞也都是陰性名詞,俄羅斯人稱伏爾加河為母親河、稱祖國為祖國母親等,由此可見,俄羅斯人認為女性是偉大的,是能夠孕育生命的。在著名長詩《伊戈爾遠征記》中,多次提到水、草、烏云等自然元素,而這些詞匯都是陰性名詞,伊戈爾出征前,烏云密布,仿佛是在提醒他此次出征兇多吉少,而伊戈爾大軍戰敗被俘,正是烏云暴雨掩護伊戈爾大軍連夜逃走,而這些詞都是陰性名詞,象征著女性的慈悲與寬容。
二、漢語中表示女性的漢字,詞匯,熟語及其意義
與俄語不一樣的是,漢語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因此我們需要通過漢字的結構來進行分析。在漢字中帶有女字旁的漢字非常多,我們將挑選一些具有代表意義的漢字進行分析。中文里除了“媽媽”“姐姐”“ 奶奶”等女性親屬稱呼的此之外還有許多以“女”為偏旁的漢字,詞匯,如;“奴”“奸”“妓”“婢”“妒”“妾”等,我們一一來進行分析:首先“奴”字是一只手抓住了女子,表示被掠俘虜和被剝奪人身自由的人,這里形容女子是沒有是人身自由的,女子是男性的附屬品;“奸”字表示“奸人”“奸臣”,都是貶義,可借此表達女性地位的低下;“妓”指“娼妓”,娼妓在古代是供男人玩樂的一群女性,她們沒有人身自由,只能依靠出賣身體來生活;“妒”指“嫉妒”這是大眾認為女性常有的一種心態,女人善妒,因此也是貶義。形容詞有“妖嬈”“婀娜”“姍姍”“嬌媚”“嫵媚”“嫻靜”“溫婉”等,這些詞匯都帶有女字旁,它們也多用來形容女子,代表來對女子性格等的美好祝愿,只是,這些帶有欣賞含義的詞匯都是從男人的角度出發的,我國古代就有女子需要三從四德的思想,何謂三從四德?三從指的是:婦女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指的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女的品德、辭令、儀態、女紅)。由此可見,以上提到的形容女性的形容詞皆是從男性的角度出發,希望婦女嫻靜溫婉、婀娜多姿等,而“妖嬈”“嫵媚”等詞匯在古代是帶有一些貶義的含義的,說明作為女子要賢良淑德,妖嬈嫵媚則是不守婦道。
除了上述的一些漢字和詞匯以外,中文里還有一些熟語或成語,這些熟語或成語一樣體現了女性的地位,如:“最毒婦人心”“婦人之仁”“雞多不生蛋,女人多了瞎搗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嫁乞隨乞,嫁餿隨餿”“打老婆,罵老婆,手里無錢賣老婆”“紅顏禍水”等,這些熟語或成語多反映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像“最毒婦人心”“婦人之仁”一說是指女性的貶義含義,而“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嫁乞隨乞,嫁餿隨餿”則是指女人沒有自主的權利,只能是男人的附屬品。當然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女性的地位不再像從前那樣低下,但也只是在文明相對發達的地區,在一些落后地區有些熟語和成語以及它們的觀點還在被使用,比如一些農村地區常使用“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嫁乞隨乞,嫁餿隨餿”“女兒是賠錢貨”“女子無才便是德”等,這就證明在一些較為落后的地區,女性仍是廉價的、不被尊重的。
除了一些熟語,近現代的一些詞匯也能體現出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在一些精神文明程度較為發達的地區,也存在一些詞匯,如“女司機”“女強人”“老處女”“大齡剩女”“女博士”等。“女司機”一詞是近幾年產生的,代表了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大眾普遍認為,女性不能很好的駕駛汽車,操縱一些重型機械等,這是一種對女性的偏見,一般在路上發生交通事故,如果駕駛人是女性,路人便會調侃一句“又是女司機”,盡管也許這位女司機是擁有多年駕齡的司機。但如果司機是男性,卻很少有人說“害,又是個男司機”這樣的言論。而“老處女”“大齡剩女”等詞更是頻頻出現,這是調侃到了一定年紀卻沒有結婚的女性,但是到了一定年紀卻還沒有成家立業的男性卻沒有人調侃他們為“老處男”“大齡剩男”等,這也體現了社會認為女性到了一定年紀就應該要嫁人,相夫教子的偏見。近些年“女強人”一詞多用于事業成功的女性身上,但是這一詞背后的含義卻是指對女性雖然事業上成功,但是家庭生活卻空虛的惋惜。“女博士”一詞也是近年來使用率較高的一個詞,但多數用來調侃,社會多數人認為女博士難嫁,讀死書,形象木訥,很顯然這是一種刻板印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社會多數人秉持“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觀念,只是,這里的“無才”不再是指從前的大字不識一個,而是指學歷不用太高,學歷太高會難嫁。
中文也和大多數語言一樣,包含粗話,而這些粗話也多是包含女性含義的,如:“去他娘的”“去他媽的”“婊子”等,這些現象都可以視為一種潛在的性別歧視的表現。
除以上的一些對女性的偏見之外,中文里也有許多詞匯,如“祖國母親”“大地母親”“母親河”等,都體現了中國人對母親這一稱呼的神圣性的認可,我們認為母親是偉大的,是寬容博愛的。
三、俄漢語言中表示女性含義詞匯的異同
經過前面的一些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俄漢語言中帶有女性含義的詞匯的異同之處。
1.相異之處:(1)俄語中有許多表示動物的名詞都是陰性形式,如:豬、狗、雞、鴨子等,但是在漢語中表示動物的詞匯多用反犬旁,幾乎沒有使用女字旁的漢字;(2)在職業詞匯方面,多有從陽性名詞派生出的陰性名詞來代表女性從事相同的職業,而在漢語中這種派生出來的詞匯很少,我們在介紹以為女性的職業時,很少說女教師、女學生、女教授這樣的詞匯,只是在個別詞,如上文提到的“女司機”上含有一些偏見;(3)漢語中有較多關于女子婚戀的熟語,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等,而俄語中卻比較少談及女子的適婚年齡。
2.相同之處:(1)俄漢兩種語言中,在熟語中都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低下,沒有自主權;(2)俄漢兩種語言中的粗話都大多包含帶有女性含義的詞匯或字眼;(3)俄漢兩種語言中都稱祖國、大地、河流為母親,表示俄漢兩種語言都認為母親是神圣,寬容博愛的。
結語
綜上所述,俄漢兩種語言中,在詞匯、熟語、漢字等方面有許多都包含女性含義,而在這些代表女性的詞匯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那就是俄漢兩種文化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本文通過詞匯、熟語兩個大方面的列舉,對俄漢兩種語言中代表女性含義的詞匯及其蘊含的深層意義進行了對比分析。可以得出,在俄漢兩種語言中代表女性的詞匯和其意義是大同小異的。
參考文獻:
[1]潘凡.漢語語言中的性別歧視現象[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5(10):78-79.
[2]何玉婷.淺談漢語中的性別歧視[J].語文學刊,2016(01):37-38.
[3]張潔.淺議漢語中的性別歧視[J].學語文,2018(06):94-96.
[4]孫慧潔.俄漢語言性別歧視現象探究[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2(04):271-272.
[5]陳春紅.俄語稱呼語中的性別歧視研究[J].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4(01):32-37.
[6]李琳.論俄語中的性別歧視現象[J].中國俄語教學,2000(01):59-64.
作者簡介:
劉可染(1997年—),女,漢族,延邊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語言文學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語語言文學。